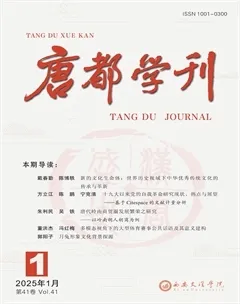月兔形象文化背景探源
摘"要:月亮與兔的形象結合,長期流傳于我國古代神話體系之中。就中國古代月與兔如何產生聯系這一問題,可以從早期女性生殖崇拜、月中陰影說、陰陽五行說和長壽升仙四個方面作初步的探索與闡述。從歷史學、人類學、文字學、哲學思想等多個角度對兔月之間關系的產生進行剖析,可以厘清、證實上述四個方面在其特定的時期,對兔月之間聯系的產生起到了促進、推動的作用。兔、月關系的產生,是我國古代早期與秦漢時期思想文化合力的結果,該討論對研究思想文化中構建神話形象、月兔形象和早期思想及秦漢思想有著積極的拾遺補缺作用。
關鍵詞:兔;月崇拜;月兔;秦漢思想;早期文化
中圖分類號:K203"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0300(2025)01-0107-08
收稿日期:2024-10-18
作者簡介:郭陽子,女,陜西西安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生,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
兔是我國自古以來就有記載的本土動物,是我國古代“五牲”和“六首”之一。在距今5 3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M10出土了目前所見最早的兔形文物。《詩經·周南·兔罝》中的“肅肅兔罝,椓之丁丁”[1],就描繪了捕捉兔、放置捉兔網的場面。《孟子》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住焉,與民同之也”[2]中提到的“雉兔”就是指代獵戶、打獵之意,也側面反映了兔是狩獵對象。這些兔形象,向我們證實了兔在中國歷史的早期,就已經進入中華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兔在古代的意義絕不僅僅止步于世俗社會的食物鏈。
漢代兔就已經被普遍賦予了月亮象征這一文化含義。漢代早期的壁畫、畫像石中常常見到月中奔兔的畫面,到了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兔的形象也更加豐富,有的肩生雙翼,有的手持臼杵,從月中奔跑的兔影到生有翅膀的搗藥月兔,但兔與月亮總是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3]中提到的“詹兔”本意是蟾蜍與兔,但是在這里將其合稱時指代的是月亮。在與蟾蜍合稱之外,兔也可以單獨作為月亮的代名詞,如成語“墜兔收光”就是將月亮稱為兔,意為月亮落下……
月與兔這對組合歷經千年文化變遷,時至今日仍然深入人心。月與兔是因何走到一起,二者之間又因為什么產生了關聯?這些奔跑于林間草木的小動物,是如何從田野之中升入月宮,成為月亮重要的代表形象?月宮灑下的清輝,又為偏偏何落在了兔的身上?
一、女性生殖崇拜的體現
在古代,日與月都被賦予了很強的性別屬性。《禮記·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孔穎達注疏道:“君立于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方以象月。”[4]660人們以陰陽分日月,將人間的男女婚配應用于日月運轉中,認為日月為夫妻之象,太陽代表男性,而月亮則代表女性并具有女性的特征。
月亮所表現的女性生殖特征,源于月亮的晦朔變化。我國早期的生殖崇拜多體現在對生殖能力的崇拜上,《王國維文集·生霸死霸考》中認為月亮的由虧到盈,再由圓到缺,使女性先民聯想到自己懷胎后日漸膨起分娩后重新平復的肚子。月亮每月自虧至盈,而后又缺,這樣的變化規律正如懷胎孕育,生子后再孕。[5]另外,月亮朔望變化的周期在28天,與女性的月經周期基本吻合,由此“月經”“月水”“月事”等別稱都與月相關,月經與生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月亮也被賦予了與生殖有關的重要意義。
《淮南子·精神訓》云:“日中有踆烏。”[6]508郭沫若先生認為日中的鳥由男性生殖器而來的,他曾針對日中鳥這一問題說:“無論是鳳或燕子,我相信這傳說是生殖器的象征,鳥直到現在都是生殖器的別名,卵是睪丸的別名。”[7]趙國華在其《生殖崇拜文化略論》中也提到三足烏負日花紋應該是男性生殖器的一種表達。[8]另外,月亮中的蟾蜍也因為其形似女性生殖器,鼓起的腹部似孕育中的女性以及多子等被學者廣泛認為是女性生殖崇拜的一種象征。筆者認為,兔與上述提到的金烏、蟾蜍類似,都是古代對生殖崇拜的體現,也因此兔與月產生了聯系。
有關古人對兔繁殖方式的記載,陸佃《埤雅》引《會稽志》云:“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9]提出兔口有缺口,是通過口中吐子繁衍后代。《論衡·奇怪》又曰:“兔舐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10]159即認為兔通過舔舐雄兔的毛發受孕,從而生子,并且是通過從口中吐出小兔的方式完成生產。
顯然,古人對兔的生理認識不足,對兔究竟如何繁育還沒有一個確切的認識。加之兔的性別特征并不明顯,雄兔雌兔在外觀上又很難辨認,且兔生育較為頻繁,甚至會有假孕的現象——即腹部變大,造窩準備生產等一系列類似懷孕的行為,而實際上母兔并未受孕。[11]兔的生理特性導致兔的生育過程在古人眼中變得更加神秘。當時人們對兔的生理認識的局限性,使得其想象空間有所擴張。杭世駿《訂訛類編》云:“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成孕。”[12]又有清代周亮工《書影》云:“常獵者言中秋無月,則是年兔必少。世傳兔望月而孕……;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以獵者言觀之,實有此理。”[13]我們可以看出古代人們普遍認為兔的繁育與月亮有著密切的關系。尹榮方在其《月中兔探源》中對月兔關系問題,指出兔的繁育周期大致在28天左右,與月的晦朔周期一致,并且母兔在當月產子過后,下一月便可繼續受孕生子,周而復始,如月亮相位每月規律變化一般。[14]“月光何德,死則又育?”正是人們對月亮死而復生、周而復始生命力的一種肯定。兔不僅僅在產子的規律上與月的周期相聯系,不斷新生的小兔,也是一種循環往復生命力旺盛的象征。另外,兔作為家畜中生殖能力非常強的一種動物,一胎大致可以生6至8只小兔,多者10只以上,且幼崽的存活率較高,成長速度快,大約3個月后就可以性成熟繼續生育。[15]因為兔擁有強大的生殖能力,而早期的生殖崇拜正是體現在對女性生育能力的崇拜上,
參見傅道彬《中國生殖崇拜文化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頁。加之兔的很多生理特征與月亮周期相似,人們對生殖的崇拜也逐漸發展成為兔與月的密切關系。
除了從兔的生理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出兔與生殖崇拜的關系外,在文字學的角度我們同樣可以找到兔與生殖之間的關系。《說文·兔部》:“婏,兔子也。婏,疾也。從女、兔。”許慎在兔部中提到的“婏”,原意為兔生子,后來衍生出“疾速”“快速”的意思。段玉裁注“婏”曰:“釋獸曰‘兔子婏’。本或作嬔。按女部曰嬔,生子齊均也。此云婏、兔子也。則二字義別矣。郭云。俗呼曰□。婏、疾也。”[16]段玉裁針對婏字又作補充“婏”與“嬔”同,指生子整齊均一,意為兔多生且生子順利。《類篇》云:“芳萬切,說文兔子也,婏疾也。又無販切,媚也,又美辨切,婉婏順也,文一,重音二。”[17]這里提出“婏”又聲為miǎn,婉婏為順的意思。《中華大字典·女部》:“娩,美辯切音免銑韻。婉,順也。同□,《說文·子部》□,生子免身也。”[18]可以看出婏、娩、嬔、□都為同一字,婏、嬔、□都為娩的異體字。從漢字字義的演變和延申來看,婏字本義僅僅是兔生子這一動詞義,但是因兔生子較多且較為順利,以及字音字形的變化,婏衍生出了與娩字同義即婦女分娩生育這一意義。古人通過漢字的發展將兔繁衍與人類繁衍聯系起來,體現了兔在古人生殖觀念中的重要作用。
另一佐證兔與生殖有關的觀點來自《本草綱目·獸部》:“兔……。血:涼血活血,解胎中熱毒。催生易產。催生丹治產難。臘月兔血,以蒸餅染之,紙裹陰干為末。每服二錢,乳香湯下。……催生散用臘月兔腦髓一個,攤紙上夾勻,……設茶果,齋戒焚香,望北拜告曰:大道弟子某,修合救世上難生婦人藥,愿降威靈,佑助此藥,速令生產。”[19]這記載了古代醫學認為兔血和兔腦都有為產婦催生的功效,并且在制藥之后,還會用藥丸向掌生育的神靈祈禱,兔不僅僅在藥物中起到了催產的作用,也在與生育神的溝通中起到了媒介作用。
兔在古代文化中多是乖順的形象,正符合古代對女性的期望,兔在生理上與月相變化的吻合,更為人們對兔的生殖展開了想象。兔所具備的強大生殖能力,獲得了古人對其生殖能力的崇拜。生殖崇拜作為早期人類重要的精神文化現象,在眾多神話傳說、巫術、禮儀等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生殖崇拜的影子。在這一文化影響下,月—女性—兔三者之間,就形成了一個閉環,將女性的色彩賦予月亮與兔,月亮與兔也承載了古人對女性的期許。月與兔也因為生殖崇拜而被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二、“月中陰影說”的合理性
屈原《天問》謂:“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20]502這里的“菟”通兔,即指月兔。屈原早在2 000余年前,就對月中兔提出了疑問,即月亮表面的陰影是否是與月中的兔有關?千年之后,唐代柳宗元作《天對》回答了他的疑問:“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21]柳宗元認為月亮本身自有圓缺,月亮上的陰影僅僅是像兔形,并非真的月中有兔。柳宗元的回答雖并未真正解釋月中陰影到底是何物,但也指出了不過是人們將月中陰影看作兔影罷了。
這就是古代將兔與月聯系起來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月中陰影說”。尹榮方在其《月中兔探源》一文中對這一說法持否定態度,認為此說并無根據,根本無法通過觀察月中陰影形狀而推測出兔形。而筆者認為,“月中陰影說”并非毫無根據可言,其背后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我們可以先運用視覺暫留現象解釋這一問題,人眼在觀察景物時,光信號傳入大腦神經,需經過一段短暫的時間,光的作用結束后,視覺形象并不立即消失,這種殘留的視覺被稱為“后像”,視覺的這一現象則被稱為“視覺暫留”。兔為夜間動物,且兔出現的地點多為郊野這類較為空曠的場所,為視覺暫留提供了環境與可能性。如果夜間行走于鄉野小路,周圍多為靜景,而兔作為動景更容易被注意,夜晚行動中的兔可以讓觀察者在視覺上短暫獲得一只兔的輪廓形狀,盡管兔的形象已經從眼前消失,但是人眼仍然會短暫保留一段視覺效果,若此時再仰頭望月,人眼很容易將保留的視覺與月中的陰影重疊,繼而產生了月中陰影為兔的說法。
但是產生視覺暫留現象的一個重要限定詞是“暫”,即短暫時間內產生的現象,那就對觀察者獲得兔、月兩種視覺的時間范圍要求得非常嚴格,倘若沒有在兔之后立馬望月,就不能滿足視覺暫留的先行條件,那也就無法產生這一現象。所以并不是每次月中陰影似兔都可以用視覺暫留現象來解釋。這里又要提到另一心理學的理論——接近聯想。接近聯想是指當一個人同時或者先后經歷兩件事情,所經歷的這兩件事情會在人的心里互相聯系、互相結合。由于兩種事物在位置上、或在空間距離上、或在時間上比較接近,所以認知到第一種事物時候,很容易聯想到另一種事物。[22]運用這一理論解釋“月中陰影說”,對觀察兔月的時間限制放寬,在夜間室外光線能夠滿足視覺捕捉動兔的條件下,必定需要足夠光源,那么就意味著當晚的月亮要較為明亮和圓滿,觀察動兔的前提也就意味著可以觀察月亮,兩種因素出現在同一條件下,使觀察者在一段較為接近的時間或空間中,先后獲得兔、月形象的可能性增加,也更合理地解釋了將月影聯想作兔狀并非一種主觀的臆想。
月中陰影為兔的說法在古代較為普遍,《開元占經》引《河圖·帝覽嬉》曰:“月中無兔、蟾蜍,天下無官。”又引《荊州占》曰:“月中兔、蟾蜍不見,天下失女主,一曰宮女不安。”[23]這記載了古人觀月時月兔影不見的罕見月相,可見在古代,月中的兔影不僅僅被普遍認作一種可觀察到的月相,同時也可以將觀察到的月兔影作為觀天占卜的依據。而這一長期為古人所認可的觀點,絕不是空穴來風毫無憑據的猜測臆想,在其背后一定有著一套可以推動其流傳發展的邏輯。
在古人眼中,將月亮中的陰影看作兔,是他們對月亮最樸素的認識與思考,也是早期人類對月球陰影最原始的一種探索。在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觀的背景下,古人將天空與地面緊密聯系,認為天空是對地面的反映,而在這樣的認知下,也隨之將地面奔跑的兔與當空的明月相聯系。在眾多漢代畫像石、壁畫和帛畫上,我們都能看到兔的圖像,大致在東漢以前這些月兔圖像中有很大部分作奔跑狀,
參見劉惠萍《漢畫像中的玉兔搗藥——兼論神話傳說的“借代”現象》,載于《中國俗文化研究》2009年第10期,第208頁。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早期的月中兔更多的是對兔形態的一種形象描寫,這也說明了早期月中兔的來源更多地應該是來自古人對現實兔的觀察與摹寫。兔作為夜行動物,其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相對于其他動物形象來說,更容易在夜間月明時刻被人們捕捉到,且因為前文所提的視覺暫留與聯想等行為,加之古人天文知識與動物知識的局限性,就漸漸形成了“月中陰影”這一月中兔來源的說法。
早期奔兔的圖像,不僅僅是將地面的兔描繪于月中,有時還會將天空地面中其他的元素與其相結合,如山東梁山后銀山東漢墓墓室墓頂的壁畫,就描繪了月中兔、日中金烏和流云。也有像是河南南陽阮堂畫像石中描繪的,將月中奔兔與星宿結合。古人將月亮連同月中如兔的陰影,與當時天空中一同出現的太陽、流云、星斗共同繪制于一幅畫面中。“月中陰影說”為我們了解當時漢人構建出的一套較為完整的宇宙體系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也向我們展示了當時人們對星空本質的追尋,這一說法是古人在其特有知識體系中對星空日月的認識與探索,我們可以認為“月中陰影說”是在視覺效果和聯想現象共同作用下,受到天人合一思想影響的條件下,古人對月中陰影的追問與思考,這一說法也成為古代天文學、宇宙觀及其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陰陽五行學說的滲透
《禮記·祭義》云:“日出于東,月出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4]1217《周易·系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24]。在陰陽五行學說之中,月與日通常相對,日代表陽,月代表陰。月亮作為陰之所宗,是極陰的象征。
王充在《論衡·說日》中引張衡《靈憲》中的觀點闡釋了月中兔的來源:“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10]502即月亮乃陰之所宗,其日積月累產生的陰精,累積成獸形,形狀似兔,屬陰。那么王充對于兔與月關系的理解,就是認為兔是由月亮陰精匯聚而成的獸類。又引《博物志》曰:“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10]159舊時人們認為兔在夜間活動時仰頭望月,即可有孕,兔的出生繁衍與月的晦朔息息相關。另外,何薳的《春渚紀聞》中也引道:“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而孕。”[25]說明古代人們認為兔的繁殖并不是雌雄交合,而是通過與月亮建立聯系而進行的,因此在一年月最圓最亮最大的中秋,即月之陰精最為旺盛之時,望月而生的兔數量會因此增加。以上材料都可以證明古人認為:兔的數量多少是與月亮陰盛陽衰的變化有著密切關系的。
《晉書》中記載了晉時一次黑兔獻瑞的故事:“石勒時,茌。平令師歡獲黑兔,獻之于勒,或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于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殿下宜速應天人之望也。’于是大赦,改咸和三年曰大和。”[26]這一記載表明,當時受陰陽五行學說中五德始終說的影響,將捉住的黑兔以為祥瑞,黑兔為玄,而玄又為水色,而晉在五德始終說中為金德,金生水故出現代表水的瑞獸即為代晉的祥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陰陽五行說的流行下,黑兔因為其毛色被看作是具有水行的動物。《論衡·說日》中:“夫月者,水也。”[10]502就指出月在古代也被認為是具有水行的象征,因此從五行類別的角度來說,兔與月都屬水行,故二者之間由此產生聯系。但是因這里的兔是較少見的黑色皮毛,相比常見的棕色野兔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除開具有特殊性的兔外,普遍的兔形象和月也與陰陽學說有著密切的聯系。王充《論衡·說日》說:“日月毀于天,螺蚌汨(泊)于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10]503《論衡·偶會》:“月毀于天,螺消于淵。”[10]102《論衡·順鼓》:“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于天,螺、蚄舀缺,同類明矣。”[10]685是諸書并以月蚌同陰,氣類相感,與此文語意并同,是其證。闡明了月亮與水同一,而水又與蚌蛤的生長關系密切,二者均是屬陰之物,因此月亮的陰晴與蚌蛤的多少關系密切。這與上文提及的兔數量多少與月關系類似,而且在月與蚌屬性關系論述中,也提到了兔與二者是氣類相同者——即皆為屬陰之物。《厚生訓纂》曰:“兔八月、十一月可食,多食損陽。”[27]從中國傳統醫學的角度側面說明了作為食物的兔,同樣具有至陰的屬性,過多食用會損害陽氣。更加明確地佐證這一論點,可以在《論衡·順鼓》中的另外一句話中看出:“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被(破)螺、蚄,為得其實。”[10]685這句話更是直接標明兔為屬陰之物,在當時民間霏雨不停的時候,人們希望通過抓捕一些陰屬的動物來解決雨患,這就更加明確了兔與月都為屬陰之物。
《初學記》引漢劉向《五經通義》中針對兔的陰陽屬性出現了這樣的觀點:“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并明,陰系陽也。”[28]10類似的論述在《初學記》引《春秋元命苞》中也有提及:“月之為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28]9陰陽五行講究萬事皆分陰陽,通常兩兩相對又互有聯系,這里提到蟾蜍屬陽而兔屬陰,二者一同在月中,起到為月亮衡制陰陽的作用,這一較為特別的觀點同樣體現了古人將陰陽學說的理論運用到兔月關系上。只是這里的兔不再作為月的象征,而是跳脫出了月的屬性,在與月的關系中獨立出來不再與月成依附關系,兔開始在月中擁有自己的職能,在兔月關系中發揮著自身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說法在現有文獻中提及較少,也為我們提供了陰陽五行觀視角下的另一種兔月關系,繼續深入此觀點仍然需要更多的文獻作支撐。而在古代主流觀點中,兔多是因為與月屬性相同而與月產生聯系,兔的屬性明顯弱于月,在兔月關系中兔更像是月的附屬。但是不論二者在兔月關系中扮演著何種角色,都不可否認地體現出了陰陽五行學說對兔月關系的滲透,可以說陰陽五行學說為兔月關系的產生與維持提供了較為完善的一套理論體系,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思想依據,古人在其自己的世界觀內長期將兔月視為重要的一個整體。
總之,月與兔在中國古代五行學說的思想背景下,都被看作水行的象征,而陰陽觀念中的月更是陰之所宗的極陰的象征。我們從古人關于兔的產生、兔與其他屬陰物的同一性、以及對兔直接的記載都可看出,兔同樣具有屬陰的特性,由此中國古代通過陰陽五行將兔與月亮聯系起來,且正如陰陽五行中相生相克那般,古人眼中兔與月并不是單方面受到陰陽的影響,兔的多寡與月的圓缺同樣都可以作用于調節陰陽。
四、長壽不死信仰的影響
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西周頌鼎上金文祈愿道:“頌其萬壽眉”,同屬于西周時期的靜叔鼎、小克鼎、沈子它簋蓋等青銅器物上都刻有與長壽有關的祝辭。可見長壽的觀念在西周時期就已經非常流行,郭沫若在《周彝中之傳統思想考》一文中道:“凡彝銘多于祖若考蘄求延年益壽,貽孫翼子之事。”[29]指出在西周時期,人們通過銘文向祖先祈求長壽的這一行為是較為常見的。
在與月亮有關的神話中,月亮也常常被賦予長壽永生的特點。首先,月亮本身就被看作是不老的仙都。嫦娥奔月的故事原型《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也。‘奔月’或作‘坌肉’,藥坌肉以為死畜之藥,復可生也。”[6]501其次,在討論關于月中蟾蜍的話題中,也有提到蟾蜍是長壽的動物。《類說》載:“王興為蒲江主簿,罷官,隱于秋長山。山下洞穴有千歲金蟾,見者當得道。”[30]當時人們認為蟾蜍也是一種長壽可活千歲的動物,在遇到蟾蜍之后還可以獲得得道升仙的機會。另外有關月中金桂的傳說。《太平御覽》引《淮南子》“月中有桂樹”,又引《安天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后生焉”[31],都描述了月中栽有桂樹的情況。《藝文類聚》曰:“范蠡好食桂,飲水討藥,人世世見之。”另引《說文》:“桂,江南木,百藥之長。”又曰:“彭祖者,……歷夏至殷末,八百余歲,常食桂芝。”[32]即桂樹被當作長生不死的仙藥,桂樹在藥材之中也是有著延年益壽的作用。
以上可以看出,許多與月有關的神話傳說和月中的相關元素,都與長壽有關。加之月亮盈虧變化,也象征著死而復生、周而復始、自我更新、永不消逝,使得人們將長壽永生這一愿望融合到了月亮崇拜之中。
兔在古代,同樣是人們眼中長壽的象征。葛洪《抱樸子·內篇·對俗》曰:“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33],說兔可以活至千歲,到了五百歲之后,毛色變白。同樣在梁簡文帝《上白兔表》“千歲采變”[34],此句也指出了兔作為一種長壽的動物,在壽命千歲以上之后,身上的顏色會發生變化。《日下舊聞考·風俗卷》記載:“重陽前后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兔,謂之迎霜兔”[35],說明在古代還有在重陽節吃迎霜兔以祈長生的習俗。在當時,人們認為兔是一種長壽的動物,甚至可活至千歲,加之上文提到過,古人認為兔的生命是具有周而復始、生生不息之特點的,人們也因此認為兔就是一種長壽不死乃至可以復生、往復的動物,由此兔也像上文中桂樹、蟾蜍一般,升入不死仙都,兔與月亮也因為長壽這一認知而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在人們祈求長壽的過程中,長壽這一思想逐漸衍生出了新的概念——升仙。大約在東周時期,升仙概念漸漸出現,這一時期的銘文內容從“長壽”更多地變為了“難老”和“毋死”這樣的祈愿。也就是在這一長生不朽觀念的指引下,“升仙”觀念發展起來。李豐楙在《不死的探求——從變化神話到神仙變化傳說》中說道:“‘變化’是仙道傳說的重要律則,也是道教修煉成仙說的中心思想。”[36]弗雷澤(Sir Frazer)《永生的信仰和對死者的崇拜》(The Belief of Immortality)中將死亡起源的神話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就提到了“月亮圓缺”(Waxing and Waning Moon)的類型,在論述此類型神話中,弗雷澤列舉了包括非洲、大洋洲、亞洲多個國家的月亮與死亡的傳說,并認為人們在思考月球盈虧的過程中,會將人類的永恒與月亮聯系起來。[37]由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古代中國在建構升仙觀念的過程中,人們的思想從肉身永恒逐漸轉移到升仙得道,這一變化的思想靈感來源,應該就是人們通過觀察月亮盈虧找到的有關長生的突破點——肉身的變化和靈魂的不死同樣意味著永生,通過變化成仙從而達到長生不死的愿望。
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新店鄉熊營村漢墓出土的西王母東王公畫像石刻中,在西王母與東王公座位之下繪有一只肩生雙翼的兔。帶有雙翼的兔形象在其他壁畫中也有發現,如河南省偃師縣辛村新莽時期漢墓壁畫中,同樣出現了生有雙翼的兔。這種帶有雙翼的兔形象,是兔與鳥崇拜的結合。類似的結合還有羽人形象,西漢劉向輯《楚辭·遠游》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東漢王逸注解道:“人得道,身生毛羽也”,宋洪興祖補注曰:“羽人,飛仙也”[20]697。可見在古代,身著雙翼是一種神力的象征,代表著得道飛仙的成功,正如蘇軾《赤壁賦》中所謂“羽化而登仙”一般,兔這一肩生雙翼的變化也意味著完成了升仙,肉身生長出翅膀就代表著完成了精神靈魂意義上的永生,兔通過一種特別的變幻完成了生命的永恒,在各路仙助冥贊下抵達更高于人間的彼端——仙界,并且通過升仙在仙界系統中獲得了長久永生的幸福。這種通過飛仙完成的生與死存在空間轉化,就像月亮的圓缺一般在變化之中獲得了生命的不滅與連續。
有關得道升仙的方法,《史記·封禪書》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38]。我們了解到,古人眼中的升仙與不死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等同的,服用不死之藥即可成為仙人。館藏于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新莽時期銅鏡上有銘文作:“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非(徘)回(徊)名山采草,浮由(游)天下敖四海,壽如今(金)石得天道,子孫長相保兮。”也提到了不死仙人日常需要采集仙草食用,可見在古代,不死仙草是飛仙的環節之一。關于不死藥來源的記載中,《淮南子·覽冥訓》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6]501。《后漢書》引劉向《列仙傳》曰:“至昆侖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39]講述了神農時期雨師赤松子去昆侖山尋找西王母的住處,并且向她取得求仙之法的過程。我們可以得知,在古人眼中,西王母掌管升仙的途徑與方法。出土于河南省偃師縣辛村新莽時期漢墓壁畫又將西王母與兔聯系到了一起,這幅壁畫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將西王母與兔結合的壁畫,此后又大量出土了西王母與兔結合的畫面,甚至李凇在《論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中提出:“在一幅表現西王母的圖像中,如果其中圖像的組合減至最低因素,那么就是西王母配玉兔搗藥;如果再減掉玉兔圖像,則西王母的可識別性受損。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認為,搗藥兔是西王母的標志。”[40]李凇提到的搗藥兔,成為辨識西王母的標志性元素,這就充分說明了搗藥兔與西王母的聯系非常密切。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兔是西王母身邊重要的標志,主要肩負著制作升仙不死藥的搗藥職責,那么除開與兔的關系,西王母與月亮也同樣關系非常密切。
在仝濤、鄒芙都《西王母龍虎座造型源于西方考》一文中,就提出了對西王母的崇拜應當與西方女神的崇拜有著直接關系。[41]西王母在古代被看作是源于西方、居于西方的西方女神。而月亮同樣來自于西方,郭璞《山海經圖贊》:“昆侖月精,水之靈府。”[42]郭璞指出昆侖山為月精所在,因此西王母在我國古代也常被認為是月神。《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載:“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月,名曰西王母。”[43]可以看出在古代祭祀中,月與西王母的關系非常密切,祭祀月亮就是祭祀西王母。西王母作為居于西方的月神在很多場合是可以作為月的化身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兔、西王母、月三者關系非常密切,且都受到了升仙思想的影響而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在古代,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升仙鏈,從掌管升仙的女神,到制作不死藥的搗藥兔,到最終飛入的不死仙都,西王母、兔與月亮三者在神話體系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飛仙這一過程中缺一不可的。
可見,兔與月在升仙思想從萌芽到成熟的過程中,都與升仙觀念有著緊密的聯系。對生命的渴求、對長壽的祈愿,是我國先民最古老世俗愿望參見余英時《東漢生死觀》,侯旭東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22-23頁。
的體現,在追求生命不朽的過程中,人們從月亮盈缺中受到啟發,將“變化”納入不死的范疇,在靈魂不滅凡胎變化飛仙的條件下,升仙這一新的觀念漸漸代替了長壽這一思想,并且這一思想也被應用到了兔形象的演變之中,生有雙翼的兔更是成為得道修仙成功的標志。飛仙永生的兔擺脫了人間普遍世俗意義中的兔形象,位列仙道的同時也被賦予了制作不死之藥的神仙職能。到了漢代,隨著黃老之學的興盛,修仙得道更是流行開來,并且向世俗化轉變,有關月與兔得道修仙的神話體系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完善并流傳下來。在這一過程中,兔月之間產生了更為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兔月之間的密切關系,受到了長壽與升仙思想的深遠影響。
五、結論
總之,月兔這一神話形象的構建,經過了漫長的文化整合。早期的月亮與兔形象,被先民賦予了女性生殖力量的內涵,在女性生殖崇拜文化背景下,二者逐漸產生了聯系。在望月過程中,隨著人類對月球陰影的追問與探索,人們將月中的陰影看作兔形,這就漸漸推動了“月中陰影說”的形成,而這一說法是視覺現象、心理學聯想和天人合一多重背景因素合力產生的。而后隨著陰陽五行學說的興起,月亮和兔在此文化體系中,常常被認為具有同一屬性,因而月亮與兔的聯系更加緊密。直至漢代,道家思想中的長壽升仙思想流行開來,月亮與兔因為各自的特點常被認為具有長生不死的能力——例如月亮被認作不死的仙宮,兔也被看作為制造不死藥的神獸,也是在漢代,月兔形象基本固定并流傳下來,月亮與兔這對不可分割的組合長期存在于中國神話體系當中,其形象的產生與發展,可以說在不同時期受到了上述四點的深切影響。
參考文獻:
[1]"周振甫.詩經譯注(精裝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9:50.
[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214.
[3]"郭茂倩.樂府詩集[M].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9:347.
[4]"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5]"王國維.王國維手定觀堂集林[M].黃愛梅,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1-5.
[6]"何寧.淮南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8.
[7]"郭沫若全集編輯出版委員會.郭沫若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9.
[8]"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略論[J].中國社會科學,1988(1):131.
[9]"陸佃.埤雅[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37.
[10]黃暉.論衡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1]李斌.母兔假孕發生的原因及防治[J].農業知識,2002(8):31.
[12]杭世駿.訂訛類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6:226.
[13]周亮工.書影[M].北京:中華書局,1958:7.
[14]尹榮方.月中兔探源[J].民間文學論壇,1988(3):29.
[15]秦川.中華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實驗動物學[M].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8:57.
[16]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72.
[17]司馬光.類篇[M].北京:中華書局,1984:357.
[18]陸費逵,等.中華大字典[M].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7:486.
[19]王慶國.本草綱目(金陵本)新校注:下[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1511-1513.
[20]金開誠,董洪利,等.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6.
[2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919.
[22]林崇德.心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14.
[23]雒啟坤,張彥修,主編.開元占經節選[M]//中華百科經典全書.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5187.
[24]朱熹.周易本義[M].北京:中華書局,2009:230.
[25]何薳.春渚紀聞[M].北京:中華書局,1983:112.
[26]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743.
[27]周臣.厚生訓纂[M].張孫彪,校注.2016:19.
[28]徐堅,等.初學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4.
[29]郭沫若.金文叢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8A.
[30]王汝濤,等.類說校注: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81.
[31]李昉,等.太平御覽[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0.
[32]歐陽詢.藝文類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2-29.
[33]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5:47.
[34]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58:3003a.
[35]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2364.
[36]李豐楙.不死的探求:從變化神話到神仙變化傳說[M]//馬昌儀.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下編.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389.
[37]弗雷澤.永生的信仰和對死者的崇拜[M].李新萍,等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28-37.
[38]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462.
[39]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1030.
[40]李凇.論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89-39.
[41]仝濤,鄒芙都.西王母龍虎座造型源于西方考[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3):36.
[42]郝懿行.山海經箋疏[M]//郝懿行集.濟南:齊魯書社,2010:5000.
[責任編輯"唐健君]
Explor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Moon Rabbit Image
GUO Yangzi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moon and the rabbits has long been a part of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To explore how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on and the rabbit originated in ancient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four aspects: the early worship of female reproduction, the theory of “shadows on the moon”, th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and the concepts of longevity and immortalit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bbit and the mo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anthropology, philology,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can clarify and confirm the roles of these four aspects in promot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abbit and the moon during their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The emergence of the rabbit-moon relationship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early thought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culture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is discussion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studies on how mythological images are constructed, the moon-rabbit image, and the early thought,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Key words: "rabbit; moon worship; the Moon Rabbit; philosophical idea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arly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