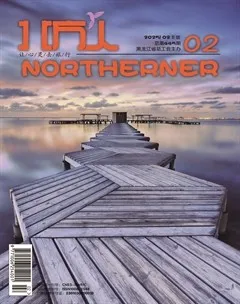生活的恩賜

剛從青海回來(lái)的那年,一次出完差,在回京的飛機(jī)上,我和一位主持人前輩坐在了一起,和她天南海北地聊,聊到了眼下的生活狀態(tài)。她說(shuō)她忙得根本沒(méi)有自己的生活,一場(chǎng)接著一場(chǎng)的錄像,一臺(tái)連著一臺(tái)的晚會(huì),一趟跟著一趟的出差,累得她每天回到家倒頭就睡。聽(tīng)完有些害怕,盡管當(dāng)時(shí)我面臨的問(wèn)題是沒(méi)活兒可干,但不知哪來(lái)的底氣,開(kāi)始在心里勸誡自己:將來(lái)我可千萬(wàn)不能活成這樣。我可以努力工作,但工作除了要?jiǎng)?chuàng)造價(jià)值,更是為了好好生活。
這么多年過(guò)去,和她的對(duì)話,以及我內(nèi)心的旁白,至今記憶猶新。想來(lái)我是在不斷提醒自己,別為了工作迷失自我,要珍惜平凡生活。因此,這些年來(lái),所有工作的日子,我都盡全力;所有不工作的日子,我也不敢怠慢——認(rèn)真做一頓飯,從備料到擺盤,從上菜順序到餐桌布置;用心做一籃面包,感受面團(tuán)發(fā)酵的神奇;認(rèn)識(shí)每一種香料,學(xué)會(huì)屬于它們的魔法;在菜市場(chǎng)挑出最新鮮的番茄,在超市里一排排地認(rèn)識(shí)每一種食材。我熱愛(ài)美食,盡管它們最后會(huì)變成腰間和臉頰上的贅肉,讓我在每年春節(jié)前都付出巨大代價(jià)和耐力讓它們消失,但卻從未動(dòng)搖我對(duì)它們的愛(ài)。
我想這和我的名字有一絲奇妙的聯(lián)系。
“尼格買提”的意思是恩賜。恩賜的是什么?按照維吾爾族人對(duì)食物非同尋常的尊重,我想,我名字的完整含義應(yīng)該是:感謝賜予我們美食,以滿足我們生存的需要,以及豐富了我們對(duì)人生的理解,并激勵(lì)我們向往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于是我果真成了一個(gè)被生活賜予了好運(yùn)和美食的人,而我還以生活的,是對(duì)美食的頂禮膜拜。
我首先膜拜的應(yīng)該是高高放在洗衣機(jī)上的層層糕吧。沒(méi)錯(cuò),鑒于20世紀(jì)90年代初我家的居住環(huán)境還很局促,媽媽在廚房里做好了蛋糕就把它們放在洗衣機(jī)頂上冷卻。媽媽通常會(huì)汗流浹背地在一個(gè)由陽(yáng)臺(tái)改建成的廚房里,搗騰她托人從蘇聯(lián)運(yùn)回來(lái)的巨型烤箱。那大概是我遇見(jiàn)的第一臺(tái)烤箱,那時(shí)候的我不會(huì)預(yù)料到未來(lái)的自己會(huì)為一臺(tái)臺(tái)不同型號(hào)的烤箱著迷和心動(dòng)。
我依然記得這臺(tái)烤箱的每一處細(xì)節(jié)。金屬材質(zhì),通體漆上了白色,高約一米,頂部是邊長(zhǎng)約六十厘米的正方形灶臺(tái),有四個(gè)煤氣灶眼,完美而強(qiáng)迫癥似的排列整齊。光是這四個(gè)灶眼就已經(jīng)讓它在那個(gè)時(shí)代脫穎而出了,更別提它最洋氣的部分:下方的大烤箱。和如今的電烤箱不太一樣,或者說(shuō)有點(diǎn)麻煩的是,使用這臺(tái)烤箱需要點(diǎn)火。右手劃著一根火柴,同時(shí)左手迅速扔下火柴盒,摸到烤箱對(duì)應(yīng)的旋鈕,在火柴靠近烤箱內(nèi)部下方的一個(gè)小洞的同時(shí),扭動(dòng)旋鈕打開(kāi)煤氣,“轟”的一下,著了。說(shuō)得容易,但每回都要經(jīng)過(guò)五六次的失敗才能成功那么一次。之后關(guān)上烤箱門,開(kāi)始預(yù)熱。
我從小到大都覺(jué)得沒(méi)什么是媽媽不會(huì)的,也堅(jiān)定地認(rèn)為她做的甜品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無(wú)人能比。我愛(ài)扒著櫥柜看她一遍遍地加料、攪拌。媽媽會(huì)去爸爸書(shū)桌上抽出幾張稿紙,那是新疆人民出版社白底綠道的稿紙,她小心翼翼地折出印,裁好邊,放進(jìn)那個(gè)時(shí)代最常見(jiàn)的長(zhǎng)方形鋁制飯盒里,在里面均勻地刷上油,這就是烤盤了。飯盒大小的烤盤做巴哈力很對(duì)口,做出的巴哈力的大小和形狀頗似我們現(xiàn)在常說(shuō)的“磅蛋糕”。
層層糕就需要大一點(diǎn)的烤盤了。一層一層的蛋糕坯需單獨(dú)烤出來(lái)。同時(shí),用一只小鐵鍋把牛奶和糖熬成焦糖色的煉乳——這也是我的最愛(ài),每次媽媽做蛋糕用剩了,我都會(huì)拿一把勺,把那只香甜的小鐵鍋刮個(gè)干凈,再把勺子舔個(gè)遍,滿心的甜蜜感。煉乳需要在每一層的蛋糕之間均勻涂抹,好讓它們牢牢粘在一起。
媽媽將粘好煉乳的層層糕放在洗衣機(jī)上,在表面撒滿核桃碎。接著,她又去爸爸的書(shū)架上拿下一本《辭海》,壓在層層糕上——那是我見(jiàn)過(guò)最厚的書(shū),兩手拿不動(dòng),每次想看時(shí),就把它放在腿上一頁(yè)頁(yè)地翻,沉著呢。我也喜歡快速?gòu)念^撥到尾,聞一聞那書(shū)里油墨的奇香,這味道讓人上癮。一本《辭海》的重量剛剛好,不會(huì)破壞蛋糕的形狀,但也足夠把它壓瓷實(shí)了。
到第二天層層糕才算是做好了。媽媽切下邊上的一角,喂給我吃。那香甜柔軟的口感,好得恰如其分,至今回味無(wú)窮。至于為什么只給我切四邊和四角吃,我當(dāng)然明白:中間的、完美的部分,會(huì)留給媽媽的宴客餐桌。
后來(lái),在我有了自己的家,擁有了較為獨(dú)立的生活之后,我買了第一臺(tái)烤箱,以及平底鍋,還有全套刀具,當(dāng)然還少不了紅酒杯。等這些常用的物件都備齊了,才覺(jué)得終于像個(gè)家了。
我完美地遺傳了媽媽的基因,成為一個(gè)不折不扣的“強(qiáng)迫癥患者”。在第一個(gè)客人按響門鈴之前,我可能還在調(diào)整刀叉與餐盤的距離,仔細(xì)計(jì)算桌上的一切布置到底是軸對(duì)稱比較好看還是對(duì)角對(duì)稱比較舒服。即便身心疲累,但追求享受食物的儀式感,以及用自己最大的期待放大食物之美,已經(jīng)深深融入我的靈魂。也許,我費(fèi)盡心力做的一切,僅僅是為了滿足我自己對(duì)于“美好”這事兒的欲望。
(摘自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一夜長(zhǎng)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