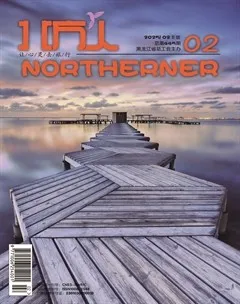一個字帶來的麻煩
“她”這個字我們天天用,但出現時間只有百年,是五四白話文運動時期才被造出來的。
在古漢語中,只要是指一個別的東西,不管指人指物,都可以用“他”來表達。比如我們熟悉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我并無他意”“我們他日再戰”。
但是近代以來,國門初開,西方文化來了。西方語言中,比如英語,第三人稱的男女是分開的。按說,語言不一樣,他們用他們的,我們用我們的,井水不犯河水不就行了嗎?可當時西方文化很強勢,我們翻譯他們的書和文章時,他們的文字中第三人稱既然分男女,那在漢語中對應地該怎么寫這兩個字呢?
男性的人稱代詞沿用古漢語中的“他”就行了,但女性的怎么辦呢?當時有很多討論。我們先聚焦在三個人身上:魯迅、周作人和劉半農。在用什么漢字來指代女性的第三人稱這個問題上,三人的主張不一樣,拿出的方案也不一樣。
先說魯迅,他剛開始的主張是用“伊”字,“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伊”。這個字在古漢語中也是人稱代詞,但不分男女。古漢語中有這個字,而且和“他”在字形、讀音上都不一樣,那就借來用下。語言就是這樣,遇到了新的意思,不主張新造一個字,而是看看在傳統資源中有什么可以借用。所以,魯迅有一段時間的文章中,指代第三人稱女性的字就成了“伊”。
但是,這個方案一旦用起來就會發現有問題。我們在口語中說“tā”,寫到紙上為什么就變成“伊”了呢?到底念成什么,難道要我們改口語嗎?這是一個創新,但是推廣成本太高了。事實上,魯迅自己最后也放棄了這個用法。
再來看第二個人,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他覺得,不如在“他”的右下角寫上一個小小的“女”字,一眼可見,也沒有語言和書面文字不合拍的問題。但這個方案也只有周作人用了一段時間,沒有推廣開,因為印刷起來太麻煩,而且在視覺效果上也不好看。
提出最終解決方案的是劉半農,就是他造出了我們今天常用的“她”字。不過嚴格地說,也不能說這個字是他造的,因為古漢語里有這個女字旁的“她”,不過意思與讀音不一樣,古漢語中“她”指姐姐,讀音為jiě。當然,這個字很早就作為生僻字不用了,劉半農也不知道自己其實造了個舊字,這實在是“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這個字一造出來,馬上就流行開來。結果證明,作為一個方案,它是最好的,避開了前兩種方案的毛病。但在當時,這是一個被罵得很慘的方案,因為里面有男女歧視問題。
有人就說,表示男性的“他”是單人旁,表示女性的“她”就是女字旁,女性難道不是人嗎?這可不是個別激進分子的少數意見,朱自清就遭到過這樣的反對。
朱自清在學校教書時,給學生發的講義里用到“她”字,很多女學生收到講義后都修改為單人旁的“他”。還有人認為,既然女性的人稱代詞用女字旁,男性的為何不用男字旁呢?這才男女平等。
那這段文字公案帶給我的啟發是什么呢?就是外來者對我們的影響。
過去,我們看見外來者,通常反應是先判斷對方是善意還是惡意的,對我是否有好處、是否有用,以此決定我是接納還是拒絕,是戰還是逃。但是,通過這個例子,我們知道現實情況沒有那么簡單。因為外來者對我們最大的影響方式,不是要對我們干什么,而是只要在那里,我們原先的世界就已經改變了。
比如,你可以想象一個生活場景。兩個閨蜜正在餐館吃飯,突然隔壁桌來了個大帥哥獨自吃飯。男生跟她們沒有任何交流,僅僅在旁邊存在了那么一會兒,是典型的生命中的過客。但如果你有生活經驗,就知道這兩個正在吃飯的女孩,無論是心思還是交談的話題,都可能發生某種微妙的變化。外來的存在不必介入,就會在你們的內部產生新問題。
這就牽涉到我們對當下這個時代的理解了。有人說,這個時代對我們個人的命運影響太大。時代在變,我們就得跟著變。有人說,是環境太險惡,有人對我們缺乏善意,所以我們活得不容易。這種思路都是在說,環境因素在主動介入你、影響你。但是,我們可能把這個事情想淺了。
這個時代的最大特征,是我們的生活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相鄰關系。我們的命運不得不和一些陌生的東西在一起,僅僅是在一起。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里,各種各樣的人、機構、話題、觀念成為我們生命中的過客,成為我們的他者。他們沒打算搭理我們,也不打算介入我們,甚至談不上什么影響,但只要他們在我們的生命中存在過,我們的命運、狀態等就有可能被徹底改變。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那些他者、過客對我們無恩無怨,談不上好也談不上壞,但是,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產生的,解決的責任也是我們自己的。這才是一個變化時代的真正含義。
這就是我從一個字引發的小感想。
(摘自文匯出版社《羅輯思維:人文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