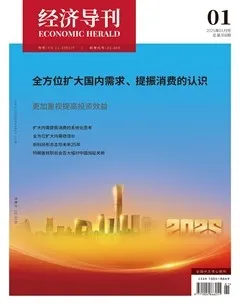中信基金會:一個扎根于民族沃土的國家高端智庫
留美經歷:呼喚中國智庫
大約在1996年,我在美國留學,博士資格考試結束已兩年了,時間稍感寬裕。走在大街上的時候,我常常會停下來,向路邊的無人報亭口塞上一元硬幣,取出一份《紐約時報》或《華爾街日報》,邊走邊讀。
這類報刊頭版文章的用詞,尤其是第一段及第二段的文字,高選謹慎,用義深涵,生僻大詞常在。我去美國留學之前,對《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時代》周刊等名報名刊充滿了崇拜,認為它是先進、發達、民主和自由理念之地的“傳信者”。可是,在美國念書六年期間,我才發現這些靠近美國決策層的“語料”,只要涉及社會主義制度、涉及中國、涉及中華文化及歷史評價,用詞的導向都是貶義的,在隨后幾個月時間內我也“頓悟”了。
改革開放后,我們國家的報刊,不僅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央電視臺等大報、大刊、大臺,而且在我們學校的課堂上,出版物及各類宣傳品中,多是以贊美詞語報道、宣傳美國及西方的經濟、技術、文化、制度、歷史及文化。那個時期,《新概念英語》《靈格風》之類英語教材,英語教學課、英語課外補習班等,都在直接間接地傳播著美國制度的優越。中美之間,中國一方“理念+貿易大入超-產品貿易大出超”與美國“理念+貿易大出超-產品貿易大入超”超級不平衡!而美國報刊報道中國幾乎都是延續了冷戰時期的口徑,變化不大。
我出生在中國經濟省份的第三梯隊——陜西省;在這個第三梯隊的省份里又處在縣級經濟體的第三梯隊——富平縣;我們村的經濟在縣里還排不在前列。也就是說,我所生活的環境是中國社會中的貧困底部。但在我們村里,人們的意識行為、人們之間的相互交往,人們的理念信仰,絕不像美國報刊所詆毀描述的那樣,是一個無助的令人詛咒的社會。那里人間真情在,生活同樣是生機勃勃。我親身的生活經歷告訴我,美國的輿論及輿論對應的社會看錯了中國。

我把這些觀點和想法告訴身邊很多的同學,不管是中國的、美國的,還是南美、歐洲的。但在20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的學生、日本人后裔福山寫了《文明的終結》一書,斷稱人類的歷史就終結在美國現世的社會形態上,山巔之國,燈塔明亮,美國當之無愧。顯然我的解釋訴說無效,那是一個輿論導向蔑視美國西方之外的國家民族與文明歷史的時代。
2000年,我從美國回到北京,體驗到二十多年間,我們國家經濟在大踏步前進之時,我們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有所缺失。雖然中國經濟超常規增長,商品出口貿易大幅增長,但在理念信仰領域卻出現缺失,與西方同類軟實力產品在“中間層”和“基礎層”部位競爭處在弱勢,經常顯現西方理念“大入超”的影響力。海外讀書及生活經驗告訴我,一種能夠校正上述國家間互動“入超-出超”不平衡的理念的公共品——國家智庫——在中國亟待構建出并健康成長。
初識中信基金會:一批獻身中國道路學者的理念影響力
這個機會終于到來了。2014年,在人民大學的一個會議室里,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簡稱中信基金會)會與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聯合舉辦一個國際經濟形勢研討會議,邀請我參會發言。我的發言是中規中矩的。但是,在那前后一段時間,我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國建置經濟的歷史傳承與當代競爭》(2004)中得出了中國復興和崛起的概念,隨后幾年,我對上述問題又進行了深入探討及挖掘,使我對中國經濟、中國道路、中國制度自信滿滿。但當時國內外學術領域的爭論非常激烈,也令我深知中國經濟發展是個超大體系的復雜演進過程,爬山過坎具有艱難性和長期性。記得在會議上,一位著名大學老師在談到中美經濟發展趨勢的時候,認為美國經濟將在3-5年時間內必然全面崩潰,這顯然過了頭。我當即插話表示不同意見。事實也是如此。我當時的觀點是,中國經濟制度有自己的增長韌性。
1840年以后,中國一代代人奮斗不息,迎來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較為全面的工業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后追趕西方鋪墊了二次成長的前提。中國經濟超高速發展,出現了國際格局東升西降的趨勢。但是,在給定制度集合、給定技術及市場規模條件下,說美國經濟在3-5年將全面崩潰,并不符合實際。作為大尺度產業全覆蓋經濟體,美國經濟體有自己的制度韌性。在這次會議上,我認識了中信基金會的理事長孔丹同志,我還見到了多年的老朋友季紅社長,我們認識十幾年了。2000年,我擔任北大經濟學院副院長,當時她是《經濟導刊》總編輯,曾在導刊編發我的文章,后來我到云南大學任副校長,她又向我約稿。這次見面不久后,季紅邀請我參加中信基金會,她向我詳細介紹了孔丹理事長發起構建的這個平臺凝聚健康學術力量的使命和努力,她所介紹的中信基金會的宗旨和學術上的努力方向深深吸引了我,我希望和他們這批具有家國情懷和為踐行中國道路獻身的學者共同努力,我也融入了這個平臺,成為中信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中信基金會里有一批著名的跨領域學者,他們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人生歷練,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在中信基金會參加各種會議和討論,以及承擔一些課題,讓我拓寬經濟學視野,接觸到國際關系、政府管理、公共事務、地緣政治、歷史甚至科技發展等領域的多方面重大前沿問題。
孔丹理事長有一次在會上說,危難險重問題是中信基金會選題中的首選系列,這對我來說非常新穎。智庫作為國家的思維智力單元,在國家面臨突發性國內外危機事件,艱難的權衡得失選擇,顛覆性風險事件取舍,中長期重大戰略謀劃,往往需要短時間內承擔超大思維智力的抉擇和對策性研究,智庫正是儲備和提供這種智力支出的樞紐單元,完成這些任務的基本能力是國家智庫的看家本領。美國斯坦福大學的食品研究所、麻省的經濟研究局、華盛頓的企業研究所,俄羅斯的瓦爾代中心、國際關系中心等等都表現出了這種智力儲備和應對突發事件的智庫能力。
中央在2013年前后推動我國構建國家高端智庫,這也是對當時國際國內大變局的一種主動應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拿出真見解”的“三真”研究學風。孔丹理事長之后還加上了一真,“真解決問題”。讓中央對智庫的要求在中信基金會運行方面自行加碼,承擔國家決策的“偏師”和國家建設的助手,參與重大問題的研究及對策討論,在力所能及的基礎上,自覺輔佐補正一些理論研究的偏向和短板。經過十年的努力,中信基金會團結了一大批熱愛黨和國家、自覺獻身于為中華崛起奮斗的學者。很多人自覺地把中信基金會作為自己的科研之家。
中信基金會的國際戰略研究:俄羅斯調研
在團結一大批科研同事的基礎上,中信基金會不僅研究國內問題,也介入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在基金會中,堅持民族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中,大家有了主心骨。我從自己參加基金會的中俄調研活動中舉例說明自己的心路成長歷程。
2018年5 月,我隨中信基金會小組去俄羅斯國家智庫及幾個政府部門進行調研,我個人對中俄關系更深一層認識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調研期間,小組的幾個同志去列寧墓瞻仰遺容。我當時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列寧墓坐落在紅場靠近克里姆林宮一邊的正中央。莫斯科的五月仍在早春尾巴,宮前草坪上的紫丁香和白丁香花枝交纏在一起,向護城河對面的旅人送上陣陣濃香。汩汩河水,綠草高樹;宮殿巍峨,朗日晴空。好一派北國風光!在我心底,紅場是一個傳心之地。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紅場世事有滄海桑田之大變,但紅場并不紅,它和故宮城墻、承德喇嘛廟、青海塔爾寺、布達拉宮山墻的顏色一樣,都是收斂色。文明有自己均衡收斂路徑的外觀痕跡。規模宏大,地面用燧石色腳掌大的石頭鋪成,有作坊手工的粗糙美感。”
“紅場上還彌漫著5月9日勝利日閱兵的搭建物,令我肅然起敬。列寧墓呈深棕色,長長的宮墻與花圃形成的墓前道,讓我有入陵稟令之覺。俄建筑師們確有過人之處。鐫刻著俄羅斯英雄的銘牌在宮墻一側導引行人向陵口走去。非常驚訝,我竟然發現了朱可夫的標牌,早年我參軍入伍,此后四十年間,朱可夫的回憶錄一再教導我:一個弱小子,在國家處于危難時刻應當挺身而出,他是我的偶像。進入陵門,深色墓道引我向列寧身旁。透明的水晶棺穹下,列寧的身材瘦小,你是用何等的力量造就了一個為未來而設計的國家實體?克里姆林宮青草、近勝春,更無一點風色。墨鑒紅田十萬頃,著我列兵一單。朗日分輝,午云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會,此處難與君說。
兩世人的靈魂師學,50年學有俄族和世界各族的諸多碎片知識,瞬間在我的腦海里聚攏,化為一個有序畫卷:在20世紀初,當列強諸惡用叢林法則撕分世界時,列寧讓馬恩理論——科學社會主義——從思想實驗室走向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從列寧墓出來,靜靜地坐在克里姆林宮的草坪上。列寧當時在克宮辦公的時候,望著那個大炮,會作何感想呢?這時,克宮總統大樓穹上紅藍白三色旗高懸,普京正在樓內辦公,他在沉思嗎?

晚間聚會討論的時候,我意外地得知帶隊開會的大樓里,那個曾經被用作美國大使館的建筑,竟然是孔丹理事長父親孔原早年在共產國際工作時的大樓。那個時代稍早的中國,清廷坍塌,國家被軍閥列強割租為47片。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中國先賢,在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許多第一代共產黨人到蘇聯來如饑似渴地學習,孔丹的父親是中共早年的奮斗者之一。他是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下來到蘇聯的。這些學成歸國的學子們,很快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骨干,在破碎山河中,由學生、工人和農民等組成的愛國志士發動組織起來。冥冥之中,歷史在用它獨特的方式,讓后輩們來到父輩奮斗過的地方,教誨后輩在新時代繼承列寧的精神,讓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學派,進行社會主義制度的薪火傳承。懷著這樣的心路成長歷程,中國共產黨早一輩人在蘇聯留學,近一輩人在俄羅斯考察與交流。中俄兩代人的成長是互相借鑒的。果然,在五年后的俄烏沖突中,這一次交流成了我,也成了小組同仁對中俄關系及全球關系把握的理念基礎。
中信基金會成長十年,在我的切身經歷中,中信基金會經歷了創生、起步期運行、重大事件決策參與,日益管理規范,成為扎根國家文化歷史沃土,又具有國際視野的國家智庫。
(編輯 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