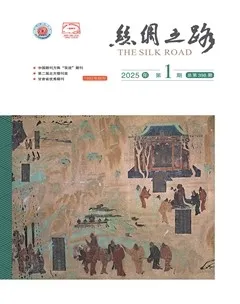試析甘肅武威慕容智墓出土半身俑









[摘要] 甘肅武威天祝縣祁連鎮岔山村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出土兩件木質半身俑,造型較為特殊。通過對唐長安、洛陽為代表的兩京地區,甘肅及西部的新疆地區出土的同類半身俑進行梳理和對比,對半身俑的流行地域、出現時間、制作特征等做進一步分析發現:兩京地區、河西地區和新疆地區出土的半身俑在時代、材質、制作工藝上有所差別,甘新地區出土的木質半身俑的年代普遍早于兩京地區出土的陶質半身俑,但所雕刻技藝和造型又和唐代中原地區的其他人物陶俑相似,和甘新地區傳統的相對粗獷的雕刻技法相異。由此推測甘新地區半身俑可能是在初唐時期吸收了中原地區雕刻技藝和藝術造型,結合地方自身的木雕傳統創造出來的,至玄宗時期又傳入中原地區,流行于晚唐墓葬之中。
[關鍵詞] 慕容智墓;半身俑;兩京地區;甘新地區
[中圖分類號] K878.5"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1005-3115(2025)01-0151-09
201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搶救發掘了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1],該墓位于武威天祝縣祁連鎮岔山村,為一座長斜坡墓道單室磚室墓,墓內隨葬品數量大、種類多。在墓室東北部帷榻上散布有數件著衣木俑,其中有2件呈有頭胸部的半身形象[2]。根據簡報描述如下:半身男俑 L:86,頭戴黑色幞頭,面龐豐滿,濃眉,細眼,圓鼻,丹唇下撇,細頸,高12.6厘米;半身高髻女俑 L:88,頭束高髻,面容豐腴,粗眉,細目,小鼻,小嘴,頰飾圓靨,頭側以金、白色顏料繪出發飾,下部連接方形木桿,高17.5厘米(圖1)。
慕容智墓出土此類半身俑又叫胸像俑、胸俑,是指只做出人物胸部以上部位的隨葬俑,在眾多類型的人物俑中這樣的半身俑卻顯得較為特殊。眾所周知,事死如事生的傳統喪葬觀念使得古人將生人世界的物象也一并葬入地下的冥界,為了代替活人殉葬而產生的人物俑即是冥器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春秋戰國時期,代替人殉舊俗的隨葬俑興盛起來。秦漢大一統王朝時期陶俑的使用數量龐大、氣勢恢弘,如秦始皇陵東側陪葬的兵馬俑群,漢景帝陽陵陪葬坑的兵馬俑群。唐代更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又一個高峰,唐代墓葬中隨葬的人物俑造型多樣、十分生動,而這類半身俑絕大多數就出土于唐代墓葬中。
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有唐長安、洛陽為代表的兩京地區,甘肅河西走廊及西部的新疆地區。長安地區發現的這類俑均為陶質,通常下部中空,可能下接木身或木架,也可能以泥塑其下身。甘肅新疆地區出土此類俑,材質多為木質。
一、唐兩京地區出土半身俑概況
(一)長安地區出土半身俑概況
長安地區出土半身俑的墓葬主要集中在唐長安城周圍,且出土的半身俑均為陶質。從已刊布的考古資料來看,此類俑多在等級較高的墓葬中使用。楊思勖墓內半身女俑是陶俑中數量最多的,也是長安地區出土半身俑墓葬年代最早的一座。完整者10件,頭部殘缺僅有發髻殘片但可確定為半身女俑的多件,因此推測半身女俑應在百件以上[3]。西郊陜棉十廠唐墓M7出土半身俑12件,男俑2件,女俑10件[4]。西安紫薇田園都市工地唐墓出土6件,男俑5件,女俑1件[5]。唐代杜江墓出土2件,男女俑各1件[6]。大理正荀曾墓出土半身男俑1件[7]。南郊馬騰空唐墓群出土17件,男俑4件,女俑13件[8]。李良墓出土7件,男俑3件,女俑4件[9]。柳昱墓和朱庭玘墓也有出土(圖2)。
(二)洛陽地區出土半身俑概況
據刊布資料,目前洛陽地區出土半身俑的唐代墓葬僅有元和九年(814)鄭紹方墓一例,該墓為單室土洞墓,隨葬的7件陶俑均為半身俑。其中男俑3件,頭戴幞頭,制作粗糙,通高9厘米。女侍俑4件,高發髻偏向左側,通高8.7厘米[10]。另有偃師市杏園村墓(M2503)、宋祜墓、鄭夫人墓[11],鞏義市芝田唐墓[12],三門峽市張弘慶墓[13]等出土有半身人物俑。其特征與長安地區較為一致,皆為陶制,據明確紀年墓葬來看,流行時段在中晚唐。
(三)兩京地區出土半身俑的特征
因洛陽地區所發現半身俑材料較少,洛陽之外幾個地區的半身俑特征與長安地區較為一致,故一并歸入兩京地區半身俑特征總結如下:
從年代上來看,兩京地區出土的半身俑的墓葬較早為玄宗時期,晚唐墓中多有流行。
從材質和制作上來看,兩京地區目前所發現的半身胸像俑皆為泥質紅陶,制作工藝大多是合模制作,為前后合模。多數報告提及了半身俑身部僅做出胸部以上部分,底部有孔,“原可能配有其他材料的俑身”[4],俞偉超先生在《西安白鹿原墓葬發掘報告》中提到半身女俑“只做出胸以上的部分,下部中空,并曾于期間發現木灰”,并推測“是在下面支一木身或木架,外披羅繡”[9]70。結合發掘出土的遺物和發掘報告來考察,以上學者所提觀點值得采納和借鑒。半身俑在當時并不是以現在出土的形態使用的,其下部中空應該是和其他部位進行組合使用的,由于材料限制及地下埋藏環境的變化導致現在已經難以看見了。施彩,一般是通體涂刷粉白打底,頭發涂黑彩,面部可見墨線描眉的痕跡,嘴唇涂朱。
從造型和尺寸來看,該類俑普遍偏小,尺寸和造型的關系很大。目前收集到的資料中,半身男俑皆為半身幞頭俑,高度7.3-8.6厘米;半身女俑的造型差別主要是發髻的多樣,根據發髻可分為鬧掃髻、蟬髻、墮馬髻、雙髻等,尺寸變化主要根據發髻的高低,高度6.8-12.2厘米。
從人物性質來看,半身男俑均為半身幞頭俑,半身女俑發髻多樣。俞偉超先生在《西安白鹿原墓葬發掘報告》直接將半身俑寫作“半身男侍俑”和半身女侍俑”,根據半身俑的發髻和面部特征來看,該類俑的身份可能為男侍或女侍。但也不排除其他性質的可能。
二、甘肅、新疆地區出土的半身俑概況
甘肅地區出土的半身俑主要為木質,也有極個別為陶質或三彩。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半身俑皆為木質。
(一)甘肅地區出土半身俑概況
甘肅武威地區出土半身俑的數量不在少數,除祁連鎮岔山村大可汗陵區的慕容智墓出土并刊布的這兩件外,位于青嘴喇嘛灣陽暉谷陵區的M3出土7件:4件為半身男侍俑,通高14厘米。3件為半身女侍俑,均殘,其中半月形高發髻半身女俑,高15厘米;雙高髻,呈“十”字形,高12厘米;扇形發髻女俑,面部殘,高13厘米。M4出土半身童俑2件,男女各一,通高11厘米。M5(弘化公主墓)出土半身高髻女俑7件,2件面部殘,高8-10厘米[14]。位于武威高壩鎮的翟舍集及其夫人安氏墓出土7件半身女俑,通高11厘米,較為特殊的是這批俑皆為三彩器[15](圖3)。
夏鼐先生1944年發掘敦煌老爺廟古墓,其中老爺廟1號墓出土3件半身女俑,“小女俑都只有上半身,至胸部為止,下端制造時卻加削平,露一管狀空穴。原初當另有絹帛做成衣服套在外面,也許還有一木桿插入空狀穴中做支柱。但是這些木材和絹帛都已腐朽不留痕跡”[16]。
1、2.青嘴喇嘛灣M3出土半身俑" "3、4.翟舍集墓出土半身俑 5、6.慕容智墓出土半身俑
(二)新疆地區出土半身俑概況
新疆地區出土的半身俑皆為木質。為分段雕刻,施彩。
1973年發掘的阿斯塔那M206為張雄夫婦合葬墓,出土大量木俑。張雄死于貞觀七年(633),其妻麹氏死于垂拱四年(688),前后相距55年,因此墓中有前后兩次的隨葬品。張雄入葬時隨葬木俑多是儀仗人馬,共19件,男俑17件,女俑2件,簡單雕刻出身體。夫人麹氏入葬時隨葬的木俑數量和種類較多,出土了多件絹衣木俑,男絹衣木俑7件,2件完整。僅雕出胸部及其以上,膠合于長方形木柱上,著黃色花綾袍、黑腰帶。女半身俑同樣是分段雕刻,再膠合成形,上施彩。M224出土同樣女半身俑1件[17]。
阿斯塔那72TAM188為男女合葬墓,出土墓志一方,載昭武校尉沙洲子亭鎮將張公夫人麹娘(麹仙妃)死于開元三年(715)十月,同年十一月入葬。同墓男尸入葬時間較晚,無墓志可查,但文書中出有開元四年(716)勘安西坊玄覺寺牒,說明男尸入葬較晚[18]。出土木雕半身女俑僅雕出上半身,胳膊部位有洞。阿斯塔那M214出土1件木雕半身女俑上身部分和M188出土的構造極為相似(圖4)。
(三)甘肅、新疆地區唐代墓葬出土的半身俑特征
從年代來看,甘新地區出土半身俑的墓葬年代在初唐和盛唐時期。
從材質和制作來看,以木質為主流,胸部以下為實芯的木柱,與上半身分段雕刻并膠合。
從性質來看,半身俑的形象皆為侍者形象。樊國君在文章中將武威喇嘛灣陽暉谷陵區的M3出土的半身男侍俑稱為胡人俑。阿斯塔那M206出土半身男俑《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簡報》將其稱為宦官俑,但金維諾、李遇春二位先生結合史料和墓葬內出土的木構建筑殘塊等認為應該為傀儡戲俑[20]。
三、唐墓出土半身俑的綜合認識
以考古發現的半身俑為基礎,將兩京地區和甘新地區出土的半身俑進行對比分析,在時代、材質、制作工藝和性質上存在異同。年代上河西地區和新疆地區要早于兩京地區。兩京地區均為陶質,甘肅和新疆地區出土的半身俑主要為木質。兩京地區半身俑的制作大多合模制作,為前后合模,在下部留出圓孔,安插在下部支具上,推測為木質材料,無法保存下來。甘肅、新疆地區的半身俑胸部以下為實芯的木柱,與上半身分段雕刻再膠合或者用木釘接合。從性質上講半身俑應當皆為侍者。
至于隨葬人物俑質地的不同,則在兩京地區與甘新地區葬俗傳統中久已有之。新疆地區史前墓葬如吐魯番地區鄯善洋海墓地、托克遜恰克古墓;羅布泊古墓溝墓地、小河墓地、樓蘭LQ墓地;東天山地區的焉不拉克墓地、五堡墓地、艾斯克霞兒南墓地等都出土有木質人物俑。這些木俑大小尺寸不一,除個別木俑一體雕刻出比例失調的手臂外,大多數木俑分開制作肢體部分,再拼接而成,且四肢缺失較嚴重。另外一個特征即人物原先都應穿著衣物。以孔雀河古墓溝墓葬出土木質人物俑為例,人物為女性半身形象,頭戴圓頂帽或尖頂帽,腦后刻有發辮,胸前刻出雙乳,未見四肢部分[21]。焉不拉克墓地出土一類人物俑全身包裹服飾,上身外裹毛皮,下身著平紋毛織長褲或平紋毛織長裙,腳著皮靴[22]。歷史時期出土木質人物俑較為重要的發現有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等。甘肅地區在漢唐時期由于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管控空前加強、溝通頻繁,河西走廊的重要地理區位尤為突出,因而文化一度繁盛。該時段出土人物俑的墓葬有敦煌老爺廟、張掖黑水國、高臺駱駝城、威武磨咀子等。其中木質俑為大宗,雕刻較為簡略,較小木俑雕刻出整體形象,較大木俑則分開雕刻再進行拼接,往往以墨線勾勒五官及衣飾。而中原地區戰國楚地墓葬常采用木俑,西漢高等級墓葬陶俑常制作木質手臂,在肩頭預留圓孔進行拼裝,其余地區和時代,尤其秦漢以來人物俑基本為陶質,無論模制或捏塑,普遍為人物整體形象。可見喪葬明器中人物俑材質的不同是不同地域根據自然資源情況所采取的不同做法,即因地制宜的結果。
兩京地區與甘新地區半身俑的年代差異,有兩方面的可能性:第一,兩京地區在初唐已制作陶質半身俑,只是目前暫未經考古發現;第二,盛唐至晚唐兩京地區制作半身俑受到初唐至盛唐時期甘新地區的影響而產生。從文中統計的半身俑自身特征來看顯然是存在著相互聯系和影響,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下文列舉幾例淺析。
吐魯番阿斯塔那張雄夫婦墓出土的木俑存在明顯的差異。張雄夫婦入葬時間相距55年,經歷了整個初唐早中期,兩次隨葬的木俑差異明顯。屬墓主張雄的隨葬木俑雕刻較為簡單,只用半圓木條簡單雕刻出頭部和身軀,通體施彩。而第二次入葬的夫人麹氏的隨葬木俑造型和技藝水平相對較高,為分段制作和彩繪,其中有一種半身俑胳膊部位有洞(圖5)。據載,張懷寂9歲隨高昌王麹智進京,可以相信其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很明顯在為其母親安排葬禮過程中,遵從一定的唐制。這可能是該墓兩次入葬木俑差異的一方面原因,也反映了這一時期新疆地區木俑制作對長安地區陶俑的仿作和改造。
結合甘肅秦安唐墓出土的一類結構較為特殊的陶俑,可能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半身俑有所啟示。秦安唐墓M1為方形磚室墓,年代根據墓中出土的文字磚殘存的字跡推測應為唐景龍三年(709)或唐神龍三年(707)。又根據三彩俑的造型手法和藝術形象,推測為景龍三年的可能性最大。M1出土立俑17件,分三彩和陶質兩種。三彩俑高32.5厘米。男俑戴幞頭,著翻領長袍,雙手抄攏,穿靴,立方托板上;女俑螺髻,披巾,束裙曳地成喇筒狀,一手貼胸,一手下垂或雙手抄攏。陶俑似用高嶺土制成,高33.5厘米。發分單髻或雙髻高聳,面部用朱、墨等彩繪。俑身系用刀削成喇叭筒狀,從造型看,應為另著手臂和服飾,但是沒有發現衣飾殘跡[23](圖6)。從圖中可以看出,M1出土的立俑胸部及以上部位和長安地區出土的半身陶俑十分相似,但其下制成喇叭筒狀的支撐,制作較為粗略,保留明顯的刮削痕跡。而胸部以上制作較為細致,兩兩相似,為模制無疑。其制作應為上下兩部分分開制作,再拼接完成。因而,推測長安地區的半身俑應該也以同樣的方法制作,只是可能以木材做為下部支撐,無法存留至今。因而此墓半身俑可作為陶質半身俑對木質半身俑仿作的一個例證。
1、2.第一次葬入木俑[20]45 3、4.第二次葬入木俑
武威高壩鎮翟舍集墓出土三彩半身俑也十分罕見。翟舍集夫婦入葬先后相隔26年,兩次隨葬俑存在差異。夫人安氏葬于唐開元十四年(726),隨葬大量的三彩俑,工藝水平較高,是河西地區僅見的三彩明器。時逢盛唐正是兩京地區三彩明器盛行時期,推測此墓三彩俑應制作于長安地區。再結合敦煌老爺廟1號墓出土陶質半身俑,足見盛唐時期兩京地區陶質等半身俑已形成了典型風格,并且對甘新地區木質半身俑在材質、制作、造型等方面已產生一定影響。
四、結語
綜上,在以武威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出土半身俑為基礎,對此類俑在更廣大的地域上做以對比分析,發現甘新地區出土的木質半身俑的年代普遍早于兩京地區出土的陶質半身俑,但所雕刻技藝和造型又和唐代中原地區的人物陶俑相似,與甘新地區傳統的相對粗獷的木質人俑雕刻技法存在差別。因此,推測甘新地區半身俑這一類特殊人俑的出現可能是在初唐時期吸收了兩京地區的陶俑制作技藝和藝術造型,并且結合地方自身的木雕傳統創造出來的,至玄宗時期又傳入兩京地區,只是材質上發生了變化,陶塑和模制取代了木刻,造型上更加飽滿和細致,并且反過來又影響到甘新地區(圖7)。陶質半身俑在長安地區一直流行至晚唐墓葬之中,雖然中晚唐墓葬隨葬陶俑呈衰落趨勢,題材、種類和數量明顯減少,但根據長安地區一些墓葬的發掘報告顯示,半身俑在人物俑的占比卻有所增加。
據慕容智墓志載慕容智葬于天授二年(691),“王以龜組榮班,魚軒懿戚。出總戎律,敷德化以調人;入奉皇猷,耿忠貞而事主”。表明慕容智本人曾居長安、入侍宮廷[24]。其墓葬形制與長安地區較一致,且符合他三品官階的身份等級。因而該墓出土的半身俑正是初唐時期河西地區木俑對兩京地區陶俑仿作的一個最佳例證。
考古學界對半身俑的研究不在少數,但主要是對某一座墓葬中的半身俑根據發飾進行類型學分析。以長安地區的半身俑研究為例,程義在《關中唐代墓葬初步研究》中根據發型分為五式[25];段敏鴿在《唐代長安地區小型墓葬研究》中同樣是根據發髻將半身俑進行了類型學分析[26];肖健一在《西安市南郊馬騰空墓》一文中指出半身俑“有明確的時代依據,可以作為判斷年代的參照標準,故具有較高的學術及藝術鑒賞價值”[8]。本文的梳理對此類俑有一個略微宏觀的視角,對以上學者的研究和認識有所補充,關于該類俑更為具體的使用、性質、造型等方面的分析將另文討論。鑒于材料有限、認識鄙陋,難免管中窺豹,僅期望對后期的深入研究有所增益。
[參考文獻]
[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武周時期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21,(02):15-38.
[2]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縣博物館.甘肅武威市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J].考古,2022,(10):29-47.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唐長安城郊隋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80.
[4]馬志軍,張建林.西安西郊陜棉十廠唐壁畫墓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2002,(01):16-37.
[5]劉呆運,李明.西安紫薇田園都市工地唐墓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2006,(01):17-24.
[6]張小麗,朱連華,趙晶,等.唐代杜江及夫人翟氏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6,(04):10-18.
[7] 張小麗,趙晶,朱連華,等.唐代大理正荀曾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5,(01):14-19.
[8]肖健一,王育龍.西安市南郊馬騰空唐墓發掘簡報[J].江漢考古,2006,(03):37-49.
[9]俞偉超.西安白鹿原墓葬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56,(03):33-75.
[10]徐殿魁.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六座紀年唐墓[J].考古,1986,(05):429-457.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杏園唐墓[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12]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鞏義芝田晉唐墓葬[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13]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市兩座唐墓發掘簡報[J].華夏考古,1989,(03):97-112.
[14]黎大祥.武威青嘴喇嘛灣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J].隴右文博,1996,(01):74-89.
[15]黎大祥.武威大唐上柱國翟公墓清理簡報[J].隴右文博,1998,(01):3-9.
[16]夏鼐.《敦煌考古漫記(二)》[J].考古通訊,1955,(02):24-31.
[17]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西北大學歷史系.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簡報[J].文物,1975,(07):8-18.
[18]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疆考古三十年[M].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107.
[19]葉爾米拉、雷歡.傾國傾城之桃花玉面——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仕女俑鑒賞[J].文物鑒定與鑒賞,2014,(12):26-29.
[20]金維諾,李遇春.張雄夫婦墓俑與初唐傀儡戲[J].文物,1976,(12):44-50.
[21]王炳華.孔雀河古墓溝發掘及其初步研究[J].新疆社會科學,1983,(01):117-127.
[22]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干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地[J].考古學報,1989,(03):325-362.
[23]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秦安縣唐墓清理簡報[J].文物,1975,(04):74-77.
[24]劉兵兵,陳國科,沙琛喬.唐《慕容智墓志》考釋[J].考古與文物,2021,(02):87-93.
[25]程義.關中唐代墓葬初步研究[D].西北大學,2007.
[26]段敏鴿.唐代長安地區小型墓葬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18.
[作者簡介]" "黃飛翔(1988-),男,漢族,陜西西安人,碩士,助理館員。研究方向:游牧考古、美術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