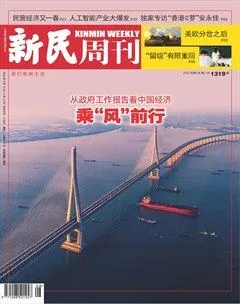“館閣體”束縛個性

明代翰林侍講學士沈度,能寫一筆雅潔靈秀、結體緊密的小楷字,被明成祖朱棣譽為“我朝王羲之”,擢為翰林修撰等。有皇上的加持,沈度身價陡升,亦被稱為“館閣體第一人”,效仿其書風者不計其數,此即為“臺閣體”之濫觴期。
廟堂喜歡這樣的書風,當然是可以理解的,那溫潤嫻雅、圓融秀擢的美感,不正是世道太平、管理有序和物阜民豐的體現嗎?拿畫類比,清初個性鮮明的“四僧”,受歡迎程度自然要遠遜于四平八穩的“四王”,也是同理。館閣體作為科舉考試的通用字體,以“烏、方、光”為書寫要素,表面上看,形成一套合乎規范的樣式。“烏”就是字要黑,最好黑得發亮,不能淡而無神。所謂“墨分五色”和“雅淡”之趣,看來只適用于繪畫而與館閣體“不搭”;“方”即字體要方正,且大小一致、格式統一,像“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記得過去練小楷時,用的也是密密麻麻的小方格紙或者等距離直線無格紙,否則很難保證字距、字行的整齊劃一;“光”自然指紙面和用筆的光潔流利,什么枯干虬曲、古拙雄強都與館閣體的趣味大相徑庭。好比要求一個人,不能太棱角分明、情緒波動或者“妄炫己意”,舉手投足須按既定的一套招式來,想想也累!
館閣體之所以被視為泯滅個性且差點斷了書法的“慧命”,是因為它的束縛性太強,無法體現書寫的暢神和情感的律動,實可謂“千人一面”。不妨對“烏、方、光”再作解讀:“烏”者,虛實、濃淡就不見了;“方”者,疏密參差、大小對比隨即遁形;“光”者,與厚拙的碑體書風難以兼容,甚至水火不容。我在想那些力倡碑學后又考上進士者,想必在考場內也不得不“屈從”于館閣體吧?為求取功名,那些很有審美能力的讀書人,或許都曾有過一番內心的糾結,可一旦面對現實,就不能不有所割舍,不能不練就兩套家伙事:一套“繡花針”;一套“自家拳”,前者為應試,后者成為信札、詩文的日常書寫中隨手拈來的筆體。
不能說“館閣體”一無是處,作為精美的小楷,其嚴謹規范的一面,對于初學者仍值得借鑒。說實在沒有楷書功底和多年的苦練,也很難把它寫好。但總的來說,館閣體畢竟不能以書法的高端形態視之。作為一種通用字體或考試字體,其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書寫樣式,實與“文人性情”和“個性化”的審美追求格格不入,與書法境界的超拔也相去甚遠。它最大的弊端或曰不足在于,每個字都像是固化的模式,很少有新奇跌宕的美感。當你知道它的書寫內容時,便能想見通篇會是什么樣子了,不會為你帶來別致的審美愉悅。好比一臺機器,它能制造出來的產品,從一開始就已經定型,這難道不是藝術創作的大忌嗎?
信息
游刃乾坤——近現代海派篆刻的崛起
近日,“游刃乾坤——近現代海派篆刻的崛起暨來楚生 陳巨來 葉潞淵篆刻學術特展”在程十發美術館舉辦。此次大展是上海中國畫院近年來舉辦的首個篆刻專題展,呈現“頡頏吳齊”“第一希有”“潞璋瓊淵”“西泠風來”“誰主沉浮”五個單元共計264件(組)篆刻、書畫作品及文獻。展覽在回望來楚生、陳巨來、葉潞淵三大海派篆刻名家異彩紛呈的藝術歷程之外,還呈現中國近現代篆刻藝術流變中海上印壇先驅們的熠熠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