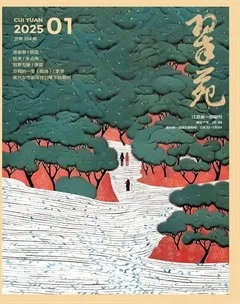包羅萬象
漿皮包子
《紅樓夢》,借賈寶玉之口,提到了晴雯愛吃的豆腐皮包子。這包子什么形制?書中未有交待。但我覺得,這種包子與吾鄉漿皮包子可能是同一種食物。
漿皮是豆腐皮的別稱。黃豆磨成漿,加水煮開,豆漿的蛋白質和脂肪與空氣接觸后,表面會凝結一層黃白色的油膜。因是豆漿之皮,故名漿皮。磨豆腐者通常用木條將之挑出,晾干后拿到集市上出售。頭層漿皮好比牛初乳,營養最豐富,故價值要高些。
漿皮原先非主流吃食,有坐月子婦女的家庭方會購買,用之做成漿皮蛋湯,有催奶之效。大批量購買漿皮的往往是素菜館或寺廟,多是用來制作素鴨。吾鄉功德林素菜館的素鴨深得居士信眾所愛,層層包裹的漿皮以菌菇汁鹵制,夾層之間放有冬筍、芝麻、木耳,口感軟嫩油潤,仿若葷物。
在漿皮包子出現后,漿皮的用武之地得到了拓展。切成小片的漿皮與筍丁、松茸菌末配蔥花、姜米入油鍋煸炒,入熬煮的醬油、白糖、精鹽、高湯燜煮,收汁后澆上麻油攪拌,若以這樣的餡心作為小菜,吃著米飯,喝著燒酒,哪怕置身寒夜,都不會覺得飲食單調,時光乏味。
對堿、搓條、摘劑、搟壓、包捏……漿皮包子名中有“漿”,但制作面皮時不能搭漿,該有的步驟不能省卻。包好的漿皮包子上籠蒸煮,一只只蒸籠下水火交融,無需多久,香味隨著煙霧揮散開來,熱騰騰地端上桌,夾一只放到碟子里,湊上去咬開,開口處的面皮向內壓擠,又迅即張開,被“關押”好幾分鐘的熱香這時一個勁地噴發到臉上。吹上幾口氣再咬,咸甜味交融在一起,綿韌糾結在一處,在和諧與沖突中搖擺不定之時,口味由清淡漸轉至濃烈,熱燙的鹵香汁在舌面上翻滾而過,像歲月里出現的炙熱愛情,讓人沉迷卻又易被傷害。故吃漿皮包子要慢品慢食,情感的恒溫才能維系長久。
相較其他漿皮食物,漿皮包子有了含蓄之美,在牙齒打開它的“世界”后,一段舌尖的美妙之旅就開始了,由漿皮,或許能想到它的“近親”豆腐;由松茸,或許能踏足到它的產地彩云之南;由筍,或許能想到喜食它的國寶熊貓。這都是舌尖旅程中的花絮,它們入口入心,精彩地綻放在生命的每一個角落。
漿皮分三六九等,一籠的漿皮包子亦有等級之分。蒸籠周邊的包子一定比蒸籠中間的包子好吃,因為蒸籠底部的松針墊在編織時,收口往往在中間,蒸煮時,水蒸氣往往透不過來,味道自然就打了折扣,當然蒸其他包子也是這么個理。
牛肉包子
受《水滸傳》影響,我原以為宋朝吃牛肉很普及,后來了解牛肉在宋朝很金貴,非普通人能享用。我印象中,牛肉壓根就沒便宜過,價格是豬肉雞肉的幾倍。
百姓人家,過日子總要精打細算,三天兩頭吃牛肉的家庭很少。以前我母親只在節慶時才會買牛肉,以牛肉搭配白菜或青菜或豆腐燒了吃。本地菜場所賣的主要是汆熟的牛肉,切片用醬油醋辣椒汁蘸食,是很下酒的硬核菜。本地一些茶館從牛肉里看到了商機,化整為零,做成一個個價廉物美的包子,換得了不少民眾的鈔票。
牛肉包子,餡心以牛肉丁為主,佐以筍丁,當然也有茶館出于成本考慮,把筍丁換作土豆丁,這樣的包子味雖不賴,但看上去黏黏糊糊,不太清爽,美食之色亦不可忽視。我喜歡的還是牛肉筍丁餡包子,口感厚實,味道清新,像年少時笨拙的初吻,無技巧可言,卻勝似千言萬語。
牛肉包子表皮鮮亮白潤,餡心綿韌濕潤。“潤”在牛肉包子上有著不同釋義,外表的“潤”是光度,內里的“潤”是油分。牛肉包子和很多包子外觀相同,頂端一圈褶紋圍繞著“鯽魚口”,忽略了顏色的話,其形類似于蒲公英花,在“花”之上,似乎能看到陽光雨露生成出的暖意,以及月色中的清澈光華。
熱吃牛肉包子最好以盤子承接,端起盤子,夾起包子湊嘴邊開一口子,能看到飽含汁水的肉餡在晃蕩,把畫面放腦海里洗禮,感覺就是微縮版的肚皮舞女郎在表演。此時對著包子開口處輕輕吮吸,中間不要停頓,以免鹵汁滴落盤中,造成浪費。吃牛肉包子時可以佐湯面餛飩,或以茶水配之,但要以西湖龍井一類清淡綠茶為宜,這樣不會沖淡牛肉的本味。
擺放冷了的牛肉包子可放鍋里煎,趁煎得滋滋作響時,撒一把芝麻,扔一撮蔥花,在熱油的“鼓勵”下,餡心恢復了多汁的本性,外皮有了黃金般的色澤,特別是近油最多的包子底板,“純度”似乎更高,嚼入口中酥松香脆。連皮帶餡咬一口,根本無法甄別混在一起的厚重香味,油香聯合麥香、肉香、蔥香、芝麻香在舌尖上演繹一段“五味進行曲”。
吾鄉牛肉包子所用牛肉,多取自北鄉散養的水牛。它們會吃帶有露珠的青草,會跑到池塘里“泡澡”。內外得到浸潤的水牛肉質鮮嫩,帶有韌性,吃時生纏綿,吃后有回旋,連續幾天不吃就產出念想。這似乎也是牛肉包子面市多年,一直未曾被淘汰的主因。
龍蝦包子
好多年前,吃龍蝦的人很少,那時飯店的菜單里是沒龍蝦菜的。而現在,每家飯店至少都要有三四種龍蝦菜,龍蝦成了我們飲食里的常客。我們這邊甚至有幾家餐館只在龍蝦上市時營業,其中一家餐館老板還靠賣龍蝦買了別墅購了車,最近又移民了澳洲。
龍蝦爆紅后,野外的龍蝦不夠人們消耗了,養殖龍蝦的就多了起來。吃龍蝦不一定要追求自然生長的,養殖的反而要干凈。因為龍蝦適應力強,在臭水河陰溝里都能很好地活下來。雖說“英雄不問出處”,但要是知道吃的是這樣的龍蝦,食客估計腸子都會悔青了。
現在夏天聚餐時要是沒了龍蝦,酒喝起來定是寡淡無比,飯吃起來必是枯燥無味。但古語云“病從口入”,故吃龍蝦一定要吃得明白,吃得放心。我熟悉的一家飯店,他們包括龍蝦在內的所有食材都是精挑細選,這么說也許有打廣告的嫌疑,但我吃了覺得味道新鮮,重點是人家老板拖家帶口一日三餐都是在店里解決,這是實打實的“真金不怕火煉”啊。
近來這家飯店又在早晨供應起了龍蝦包子。剝好的蝦仁,剔取的蝦黃,放豬肉糜里,添些蔥姜,加點料酒,攪拌成餡心。特別要注意的是,剔取蝦仁時,要抽掉蝦背上的黑腸線。因去了黑腸線的蝦仁肉質易松散,故在剝取蝦仁前,可將龍蝦先下鍋過油,這樣能維持蝦仁滑彈的口感。
有了肉餡打底后,蝦仁突顯出滑嫩,蝦黃漫溢出鮮爽,它們蒸制的過程中,或嵌入肉餡,或融入肉餡,肥瘦合宜的肉糜由此生成出金黃的油汁,從內部滲透到松軟的包子皮上。等到出鍋后,能看到包子頂端的“鯽魚口”里,都有了一汪油汁。
咬開龍蝦包子的面皮餡料后,油汁隨即濡潤了牙關和舌面,一嚼一咽間,豬肉的厚重葷香中冷不丁地冒出龍蝦的清甜和鮮美,隨著一浪高過一浪的食欲,層次豐沛的滋味滲透到味蕾世界里,拼接出一片充盈著清新氣息的魚米之鄉,幻境中的田園更可能是理想中的家園,形似燈籠的龍蝦包子照亮了內心深處的歸途。
拿演藝圈來形容的話,龍蝦在我們飲食生活當中,已從“跑龍套”的角色成為一線主演,而龍蝦包子的開發,似乎標志著它又向樂壇等領域進軍了。但無論怎樣發展,受益的永遠是我們這幫“吃貨”群眾。
雪菜包子
冷冬之季,常見雪天。雪是自然景色,亦是天然養料。雪蓋田野之際,一蓬一蓬的雪里蕻趁勢生長,在白茫茫大地中顯示出一抹綠意,因之為秋播冬收,故又有冬菜一名。
收獲后的雪里蕻,被農人運到市集上出售。雪里蕻價低廉,買家通常都是幾十斤上百斤的買。雪里蕻有澀感,極少有人直接拿來入菜,一般都要進行腌制。雪里蕻葉多梗細,腌后,味道比“高腳白”腌菜好。買回來的雪里蕻洗凈后,掛陽臺的晾衣繩上,讓它吸收陽光的撫照,接受風霜的洗禮。歷經考驗的雪里蕻可經久貯藏。
等在外擱上多天的雪里蕻萎縮了身形后,就將它用鹽揉搓,一層層地碼到腌菜缸內,壓瓷實了,再擺一塊頗有分量的石頭壓上。這種石頭有個專業名稱叫做“壓菜石”,以前沒有專門賣“壓菜石”的商店,人們都是東尋西覓,也許在荒墳扒一塊殘碑斷碣就用上了。收舊貨的小畯曾以“三文不值二文”的價格從鄉間買過一塊“壓菜石”,這石頭大有來歷,是我們這邊宋代城墻的匾額。
腌菜缸里的雪里蕻,在鹽的刺激和石頭的擠壓下,不斷地滲出汁水。個把月后,搬開石頭,缸內的雪里蕻已變成了黃綠色。這時取出來切成小段,和肉絲一起燒,配雜魚一起煮,與豆腐一起燉,即使只配幾個紅辣椒單炒,亦是下酒又下飯的家常小鮮。若把雪菜煸炒為餡,做成雪菜包子,也必是甚得人心的美食。
吾地很多早餐店都有雪菜包子賣。當然煸炒的雪菜包子餡里,不僅有雪里蕻,還有五花肉丁和筍末,葷素兩食材再加上蔥姜等佐料的幫扶,極大地豐富了雪里蕻的色香味體系。當雪菜包子連蒸籠一起端上桌時,從氤氳的熱香氣中,能看到白亮的包子有序地擺放在松針墊上。因個頭不小,一籠里面也就放了七八個雪菜包子。但個頭不小不代表食客對它有開發難度,飯量大者吃五只雪菜包子不在話下。
歷經煸炒、蒸煮的雪菜餡,由面皮包裝后,美妙得難以言喻。入口時,牙齒穿過綿軟的包子皮后,能聽到輕微的嘎嘣脆聲響,接著咸鮮和鮮甜先后在嘴里橫沖直撞,隨著咀嚼的深入,油滋滋的肉丁和脆生生的筍末也混跡到其中,似乎是環肥燕瘦兩類型的美人在嘴中較著勁,同臺比美間演繹了至鮮之味。
我原先上班要經過一家早餐店,常能聞到一股雪菜包子的香味。雪菜包子的氣息在包子里面具有個性。調整辦公地點后,我還時常想念起這味道。時間寬裕時,我會繞道走這家早餐店門口過一下,或點幾只雪菜包子吃吃,或聞聞雪菜包子的香味。美食,有時體悟體悟就過癮了。
我認識的一位“老吃刮”,他到早餐店用餐時,會點一碗陽春面,一只雪菜包子。他吃雪菜包子時,先吃包子皮,最后把餡料放面條上作澆頭,這樣一碗雪菜肉面就有了。陽春面和雪菜包子加一起,比單點雪菜肉絲面還要便宜上幾元。遇上這樣的吃家,店方真是拿他沒轍。
白菜包子
浙江是省名,也是人名——明末清初有畫僧浙江,擅山水,所作刪繁就簡,清冷秀逸。我臨習過他的作品,只得皮毛,意境相差十萬八千里。想來畫畫不只是靠筆墨線條,重要的還有繪者人生之得失。
吾觀浙江的畫風,疏淡有味,與白菜之味仿佛。白菜雖是尋常蔬菜,但不可輕易忽略其價值。寄萍老人喜作白菜,常題“咬得菜根,百事做得”。這是至理名言,遠比當下畫家單一地題寫“百財”要高明許多。
白菜常在餐桌上與我們相逢。它的至美時刻當在秋末,經過秋霜“腌漬”的白菜,被稱作“晚菘”。“菘”似乎表明白菜有著松樹一樣的傲骨,寒冷是天降大任,只有歷經磨難,才會淬煉出更好的自己。
白菜性平,葷素皆可與之搭配。雪天里,剁一棵白菜,配上魚肚、魚丸、肉圓、粉絲及各式菌菇燉一鍋“全家福”,品食者可按喜好,夾取可口的食物,舀取味美的濃湯。水霧氤氳中,一片歡聲笑語。這安詳之景是和諧社會基石上的美麗紋路。
提及白菜,我還會想到白菜包子,這是秋冬時的大眾早點。吾鄉有一家小茶館,開在一古剎對面,其只售賣素湯面及素包子,所做的白菜包子堪稱一絕。我和茶館里的老板聊過,他們每天要賣到七八百只白菜包子。
這家茶館環境頗顯陳舊,梁架結構的房子,地面鋪的是方方正正的羅底磚,擺著十多張老式的四仙桌,搭配油漆斑駁的學士椅或高矮不一的條凳,有些影視劇里晚清食肆的感覺。初一月半的時候,茶館的生意會特別火爆,周邊的信眾去古剎燒香時,會順便來吃個早餐。
我去過這家茶館不下百次,常點兩只白菜包子,要一碗免費的蠶豆瓣熬制的素湯。要是招待朋友,就會點上一籠白菜包子,再下幾碗素湯面。因個頭大,臉盆大的蒸籠里只放置了八個白菜包子,籠底是一層松針墊,蒸煮時,能將草木芬芳融入到包子里。
白菜包子的品鑒黃金期當在出籠后的五分鐘內,此時香味尤盛,會隨熱氣滾滾而來。白菜包子外體飽滿,腹體寬敞,形如康熙名瓷太白尊,其是由摹仿李太白的酒壇而得名,這么一比喻,白菜包子似乎也沾光有了詩文才氣。
一道籬笆三個樁。白菜包子餡料里,不只有白菜,還有茶干丁、香菇末,它們齊心協力,讓美味的“籬笆”更加牢固。
白菜包子的口感初是平淡,咀嚼數下后,卻又有一種說不來的濃郁。表面看,它內陷的汁水不如肉包豐盈,但卻能在口舌運動中陣陣地漫溢出來。整個品嘗過程帶有一種天然的節奏感,食完整個包子,嘴中周邊還彌漫著鮮味,讓人深刻理會到“意猶未盡”的含義。
曾文正公云,鴨湯煮蘿卜白菜,遠勝滿漢筵席二十四味。白菜包子里也用高湯調配,至于用了什么食材煲湯,每次問茶館的老板,他都避而不答。這畢竟屬商業機密,說穿了就不值錢了。
青菜包子
我們的餐桌四季常青,而“青”多半來自青菜。飲食里若缺了青菜,就像生命褪去了本色,行走世間難免底氣不足,就像老輩人所言的“三日不吃青,走路不正經”。作家陸文夫寫一朋友千方百計從北京調回來工作,不為別的,其中一原因竟是為了吃青菜。
鄉人對青菜同樣充滿迷戀,因多用以燒湯,故青菜在故鄉被稱作“湯菜”。適合做湯的葷素食材頗多,但唯獨青菜有此頭銜。在夏至祭祖時,鄉人還會拿青菜配豆腐白燒,供奉先人后再食用,據說能保平安。青菜在鄉人心目中分量著實不輕,它蘊含精神的價值。
青菜有多面性,能入菜,能制餡包面點。這是食物的情趣。當然是建立在前人創造力之上,麥餅、包子、燒賣、餛飩皆是代代相傳的經典。我接觸最多的青菜面點,是青菜包子。吾鄉只要做早市的飯店茶館,都有的賣。煙霧繚繞間,咬開一只剛出籠的青菜包子,映入眼簾的菜餡像一團綠藻,明晃晃地躍動著,觀之滿心歡喜。喜悅之悅,也可是躍動之躍。
有成語以“面有菜色”形容饑民,換到青菜包子這里,面有菜色是對它的褒獎。蒸煮的過程中,經素油調合的菜餡滲出汁水,在包子表面形成翠綠的斑點,清鮮感直面而來。鄉間有一老飯店名曰“翠綠”,店名相傳就是從中得來。而隔宿或復蒸的菜包,餡心極易泛黃,時間不僅是殺豬刀,也許還是剁菜刀,讓菜餡從青春少女變成黃臉老婦,這樣的包子色感不佳,口感也好不到哪里。
新鮮的青菜包子宛如兩幅畫,外觀是雪景山水,內里青綠山水,冬去春來,全靠牙齒轉換。若是要給其精確定義的話,應是民國江南畫家袁培基的風格。食物里微縮了天地的精華,它的味道可以膚淺,可以透徹,除了口舌滋味,還有深入心靈的品味。“品”由三口組成,這樣的味道注定復雜,味外之味只能意會,無可言傳。
冬天的青菜包子口味更為絕妙,霜打的青菜周身布滿甜糯之味。這種甜糯像少女奉上的初吻,笨拙、生澀、稚嫩,少了風韻,也沒了套路,一切新奇甜蜜,似毛茸茸的羽毛撩撥人心。食就是色,色就是食,人的一生,會不斷地往欲望的洞口里投放食色,減少投放,或能超出塵世。
一只青菜包子、一碗稀粥、一碟蘿卜干,這是我一位僧人朋友的早餐,他幾乎天天這么吃,從未吃膩過。這讓我想到車前子所說的“美食更是一份心境……有了這一份心境,也是美食:寧靜、清淡、虔敬”。此話信然。
作者簡介:
李晉,筆名李敬白,80后,江蘇泰州人,文字散見于海內外報刊。著有《人間滋味,溫暖可期》《節氣之美·食事:美人纖手炙魚頭》《紙面留鴻》《寸紙小鮮,煙火滋味》等,獲冰心散文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