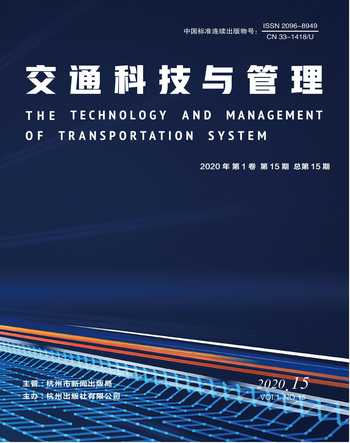回彈法檢測混凝土強度的準確性研究
蘇漢飛 汪清河 夏信友

摘 要:為確保結構施工質量,首先要做好結構的檢驗工作。在結構檢驗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混凝土強度檢測。在混凝土強度的檢測方法中,由于回彈法具有操作簡單便捷、評定速度快等優點,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本文將對回彈法和回彈儀進行簡單的介紹,并對其檢測混凝土強度的準確性進行分析研究。
關鍵詞:回彈法;混凝土強度;檢測;準確性
中圖分類號:TV544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混凝土由于會受到構成原材料、外加劑、制造工藝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其強度和性能都會有所不同;而混凝土的強度是混凝土結構中最重要的評價指標,目前常用的檢驗混凝土強度的方法有立方體抗壓強度試驗法、鉆芯法、回彈法等。
立方體抗壓強度試驗法是將邊長制作成150 mm新拌混凝土的立方體試件養護到指定的齡期后,利用壓力試驗機進行強度測試。這種測試方式雖然結果準確度高,數據直觀可視,但是容易受到施工條件或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且無法完全反映出工程實體的強度,通常用于仲裁測試或工程驗收。
鉆芯法是在混凝土結構物上鉆取圓柱體芯樣,經過篩選加工后再放到壓力試驗機上做抗壓測試。這種方式雖然可以對工程中混凝土的實際強度進行精確的檢測,但是實際操作中會對混凝土結構或構件造成損壞,使建筑物的原始受力情況遭到破壞,因此很少在實際中進行使用。
回彈法測量混凝土強度主要是在混凝土表面進行的無損檢測,以不損壞混凝土結構為基礎,對其硬化后的強度進行測評。相對于前面介紹過的兩種方法而言,回彈法具有很多優點,例如:操作簡單便捷,使用靈活性強,經濟性高等。基于這些優點,目前我國工程質量控制大多會選擇使用回彈法進行測評。但是由于回彈法測量混凝土強度時容易受到原材料、外加劑、建造工藝等因素的影響,測量的精確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分析,目前回彈法測得的數據也僅用作參考,而無法用作評判混凝土是否合格的標準。
1 回彈儀工作原理
回彈法是通過測量混凝土的硬度進而推求混凝土的抗壓強度,由于混凝土的抗壓強度與其表面的硬度存在相關性,所以在應用回彈法檢測混凝土強度前,應先確保結構構件外表層干凈,避免浮漿等問題影響檢測結果;除此之外,還應確保混凝土表面的干燥,如果混凝土外表有潮濕現象應先進行干燥處理,以免對外層混凝土造成灼傷,也避免混凝土含水量的變化對混凝土外表硬度造成影響。
回彈儀是在重錘中利用彈簧對其進行加力,當彈簧松開時,沖擊桿會產生一種恒定的力量并向測試表面進行樁基。二擋重錘被撞擊產生回彈時,滑塊的會談將達到峰值,此時使用標尺記錄下重錘反彈的間距。反彈間距和彈簧原長度之比為回彈值,通過測量回彈值的大小即可間接推斷出混凝土的強度。例如,混凝土的強度較低,則受到彈擊能量時就會吸收更多能力,反彈力就變小,故而回彈值就小,反之同理。上述原理即可得出混凝土強度大小與回彈值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成正比關系。
回彈儀的彈擊能量計算方法如下:
式中:A1為使混凝土產生塑性變形的功;A2為使彈擊錘、彈擊桿及混凝土產生彈性變形的功;A3為彈擊錘和指針工作中因摩擦損耗的功;A4為彈擊錘和指針工作中克服空氣阻力的功;A5為混凝土產生塑性變形時增加自由表面所損耗的功;A6為混凝土構件的顫動和彈擊桿與混凝土表面移動而損耗的功。在試驗過程中,如果混凝土構件剛度足夠大,在回彈過程中回彈儀可保持與混凝土表面緊貼時,所產生的功的損耗對于回彈值的影響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如果混凝土構件無法與回彈儀保持緊貼時,由所產生的功的損耗不可以忽略不計。
在測量過程中,回彈儀的準確度會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響,例如由于混凝土的骨架結構中充滿不同的原材料,當強度較大的原材料剛好出現在測量點時,回彈儀測得的數據值會偏大,反之同理。除此之外溫濕度等因素也會對回彈儀測得的硬度值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故而回彈儀的測量結果是具有不穩定性的。
2 試驗材料及方法
本文將依據相關規程中的立方體試塊抗壓強度的測量方法,以及其中的回彈法測量方法,對某項目的混凝土進行對比測量,測試組與對比組所取用的樣品均為同一批次所制作的混凝土。
3 分析研究混凝土回彈法測定強度的準確性
3.1 預加應力對試驗的影響
根據回彈法的具體工作原理可知,我們將應力預加到標準試塊后再進行試驗,防止出現誤差較大的現象發生而導致測量結果失真。測量結果的準確性的直接影響因素便是預加應力值,預加較小的應力,導致能量損耗在測量過程中無法消除;較大的應力,回彈值會增大幅度會隨著應力的增大而增加,所以預加應力值應該合理適宜進而保證試驗結果可取。通過試驗研究得出:本文混凝土強度等級不同,施加不同應力,最終確定預加應力范圍是:60 kN~80 kN。
3.2 分析混凝土采用回彈法測量的準確性
影響準確性的因素較多,主要包括:養護條件、齡期、混凝土等級和成型方式。以下便針對這四種影響因素逐一分析。
3.2.1 分析混凝土強度等級差異測得回彈值的準確性
標準值和回彈值差異較大的是等級較低的混凝土,但是都不超過15%,在可控范圍內。隨著不斷增大的等級,二者差值越來越小,所以,謹慎對待混凝土等級較低時,采取回彈法測量的工作。
3.2.2 分析混凝土齡期差異測得回彈值的準確性
混凝土養護齡期分別選擇:90、60、28、14、7d,同時等級選擇C30、C25,進行試驗分析。結果表示:在可控范圍內,標準值與回彈值差異較小,并且齡期越大,差值越小,所以,盡可能的選取齡期盡量在28d以后的混凝土。
3.2.3 分析混凝土養護條件的差異測得回彈值的準確性
蒸壓、自然和標準養護是混凝土的幾種養護方法,由具體規范可知檢測手段是回彈法時不宜使用蒸壓保護,因此的實驗對象采取自然和標準養護,進而分析標準值與回彈值之間的差異,混凝土的等級為C30,28d養護。
標準養護下的各項數據低于自然養護的混凝土,與混凝土強度關系不大。并且,二者的差值與養護條件的影響較小,因此測量方法為回彈法時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3.2.4 分析混凝土成型方式的差異測得回彈值的準確性
研究表明,強度等級和齡期完全一致的混凝土,回彈值也會由于不同的成型方法而造成偏差,C30混凝土作為本次研究對象,搗鼓方式為機械和人工,振動停止操作的標志是有漿在混凝土表面出現,然后檢驗試驗為28d試塊,對比回彈值與標準值。
當成型方式不同,根據測量方式中回彈法的具體原理,即使搗鼓方式不同,但標準值與回彈值差別不大,保證混凝土成型后密實,回彈值就可以應用。
4 結論
(1)抗壓強度在標準試塊的表征值普遍大于混凝土強度由回彈法測算值,同時影響因素包括混凝土搗鼓方式、養護條件以及齡期和等級,使得差值出現在二者之間,通常二者之間差值不大,13.9%是其最大差值,而為了使工程質量得到保證,測量手段中可以使用回彈法作為輔助,精確度在混凝土強度上的表征不會隨著狀況的不同而產生較大的差異。
(2)使用回彈法過程中應該謹慎,避免誤判的情況發生,尤其是混凝土等級較低時,測量強度過程中應特別注意。
(3)當14d為混凝土齡期時,未完全成型的表面硬度出現在混凝土中,較大的差值出現在標準值與回彈值之間,精確度準確性得到保證的依據是齡期盡量在28d以上,此時測量強度才能采取回彈法。
參考文獻:
[1]張志遠.混凝土回彈法在實際運用中的幾點探討[J].四川建材,2021(01):21-22+31.
[2]胡淑華.建筑工程混凝土強度檢測中回彈檢測方法應用[J].散裝水泥,2020(06):20-22.
[3]喻林,楊延玉,譚濤.回彈法檢測自密實混凝土抗壓強度的可靠性分析[J].建筑施工,2020(11):2104-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