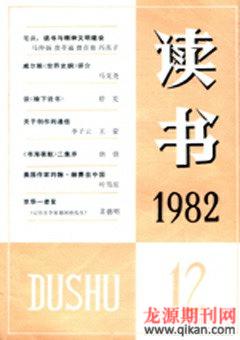書門遐思
馮英子
每天早上上班,經過上海圖書館的門口,總看見不少人排著隊,在等待圖書館開門。有時隊尾一直排到了黃陂路的轉角處。在長長的隊伍中間,青年人居多,有的身背書包,手捧書本,孜孜不倦,分秒必爭。
“為什么圖書館還沒有開門,大家就來排隊?不能等開了門再來嗎?”我問一個同行者。他告訴我說:“來遲了,怕找不到座位!”這倒說明了桌少人多,求過于供。讀書人多,求知心切,這是好事,使人看到了我們青年一代的奮發向上之心。也使人看到了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前途。但要每天一早來排隊搶座位,卻也反映了讀書不易。每天看到這支長長的隊伍,我總想到杜甫那句“安得廣廈千萬間”的詩,我們的文教經費,能否再加一些;我們的圖書館,能否再多一些,或者是再方便一些,能向一切要讀書的人開放,為一切要讀書的人服務。
讀書不易,自古已然。因為“刑不上大夫”的下面,還有“禮不下庶人”一句。雖說“齊之以禮”,也不過是“不可使知之”的“齊”法。庶人倘然懂得太多,難免七嘴八舌,以致亂說亂動,不易管教。而書本據說是總結歷史經驗的,司馬光的《通鑒》,所以稱之謂“資治”。歷來把讀書當作少數人的專利,其理也在此。至于庶人呢,讀書也無非是作為爬到“大夫”那個地位上的臺階。“懸梁刺股”的蘇秦,終極獵獲的還是那顆“六國相印”,佩著它威風凜凜地驕于鄉里罷了;“鑿壁偷光”的匡衡,后來也官拜丞相,封為安樂侯,而且是西漢的經學名家。當然我們現在的男同志,早已沒有可以懸在梁上的長發了,而不少農村都已有了電燈,用不著偷什么光了。再說,讀書也未必有用,“大字不識,工鈿八十”,而一些助理編輯、助理工程師之類,卻不過六十、七十。這些同志大抵又都“人到中年”,不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了。正是“一識之無,便無足觀”。所以有一個時候,盡管比較象樣一點的書本都要“內部發行”,“按級別分配”,靠打砸搶起家的王洪文之流,可以有特制的大字本《二十四史》,真正想讀書的人,只好望書興嘆,甚至望到一下也不易。但大家對讀書也不很計較。讀書不易,不讀也罷。說實話,我就有好幾年不讀書、不看報,只寫“檢查”的。
現在圖書館門口排了長長的隊伍,說明經過撥亂反正,一切風氣在變了,為了真正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搞好,為了建設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大家迫切希望有點知識,有點學問。這是新氣象,是好事。可是看來讀書還是不易,那條長長的隊伍,便是一個老大的見證。
圖書館中的座位粥少僧多,這不能怪圖書館,因為這些年來,建筑這樣,建筑那樣,建筑圖書館卻是一個冷門,好象不大聽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圖書館的負責人也不例外。據說上海圖書館包括它屬下的“子圖書館”,一共也只有一千多個座位,而上海的人口是一千多萬,何況不少的人,他們到圖書館來的目的不在借書,只是找一個座位,逃避家中“三代同堂”與“四人共桌”的“陋室”罷了。從這一點上說,圖書館不應當負任何責任的。
但圖書館應當就是這個樣子嗎?我看也不見得。大抵對于圖書,過去太偏于“藏”。私人藏,公家也藏。宋、明、清幾朝,號稱“萬卷樓”的就有七、八家之多。記得前些年有個左舜生,也自稱“萬竹樓主”,當然也是藏書萬卷的了。清朝的《四庫全書》,分藏在七個地方,現在僅存的也只是杭州的文瀾閣。他們寧可毀于火,毀于兵,不肯輕易示人,更不用說借出了。現在的圖書館自然不同于從前的藏書樓,可是禁區依然不少。特別是前幾年,幾乎把所有解放前出版的書籍報刊,一概名之曰防擴散材料,圖書館則一定要為階級斗爭服務,于是不僅大批的書不能借出,連目錄也諱莫如深,非絕對親信、可靠的人不能接近。結果是實質上繼承了藏書的傳統,書籍只能關在不見陽光的地方,與蠹魚、蛀蟲為伍。我碰到過幾位從外地來搜集什么史料的朋友,盡管拿著蓋了公章的介紹信,可還是不得其門而入,不得其書而查。托朋友,找熟人,說好話,轉了不少彎,才算略窺門徑。一般讀者,還能隨便登堂入室,一窺究竟嗎?
我不說所有的圖書館都是這樣,但至少有些圖書館、或有些圖書館的某一時期是這樣,圖書以“藏”為主,領一張借書證,也要以“級別”為標準,好象只有“高干”和什么“家”之類,才具備讀書的資格。學習列寧的作品時,知道他不少文章,是依靠瑞士蘇黎世圖書館供給材料的。他對這個圖書館作了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對他們那種為滿足讀者需要,多方設法,有求必應的服務態度。我不知道當時蘇黎世圖書館中,有沒有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史無記載,不便虛擬。但他們為這位無產階級大師熱心服務,使馬列主義的武庫增加這么多輝煌的遺產,終究值得稱道。又從美國史中可以看到,美國開國之初,也曾發起過圖書館運動,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要提倡精神文明,就得讀書。而解決讀書難的問題,扯起來頭緒萬千,不勝枚舉,你有你的困難,他有他的理由,但我倒認為其中有兩條應當非常重要和非常迫切,一是呼吁國家重視圖書館的建設,當代跑在前面的國家,哪一個不是從提高人民文化開始的?二是希望圖書館從“藏書”向“借書”、“供書”發展,把死書變成活書。龔自珍詩說:“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幽谷中的蘭花,開得最好、最美,但對人類沒有好處,又有什么意思呢?在提倡實事求是、學以致用之時,先提倡一點書以致用,幫助大家解決一些讀書的困難,我想這也是建設精神文明的重要一途吧。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