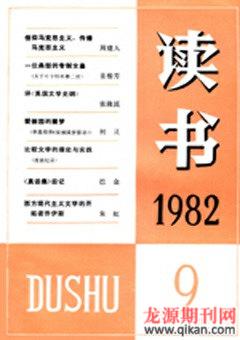學有淵源師有承
徐 瑜 錢在祥
亞里士多德《動物志》漢譯本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三八四——三二二年)是古希臘“名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未分科前,一切知識的總稱)、“哲學”的集大成者。馬克思、恩格斯把他稱為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并稱道他的睿智遠見。亞里士多德研究當代一切知識,所以他的遺著,被后世的歐洲人稱之為“古希臘的百科全書”。這些著作,歷經二千三百余年的滄桑世變,仍然保全了絕大部分。希臘文化時代,挨次而為拉丁文化時代,以及于中古文化混雜的時代,他的學術經拉丁譯本、敘里亞譯本、阿拉伯譯本的傳播,普及于歐、亞、非之間世界許多民族。文藝復興以后,法、德、英、意、西班牙、俄羅斯日本等國都從事于亞氏著作的本國文字的翻譯。我國自明末時起就有亞氏學術的介紹,但對于西方學術淵源所本的經典名著進行嚴肅認真的介紹和翻譯,卻是自解放后才開始的。翻譯亞里士多德著作的,以吳壽彭老先生用力最勤,翻譯最多,質量亦較高。單吳先生翻譯的有《形而上學》、《政治學》、《動物志》、《動物四論》(即將出版)以及現在正從事的《靈魂論》(預計一九八三年出版)等書。
吳壽彭先生翻譯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志》,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歲月。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第五版“學術研究”專欄曾預報了這本書的漢譯本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可是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史無前例”的十年中,亞里士多德的這一著作和在一九五六年科學發展計劃中預定譯印的許多世界名著一樣,一律遭到了禁錮或毀滅。一九七六年冬,在“四人幫”肆虐的文化災殃之余,出版者竟撿到了這一幸存的稿本,于是亞氏《動物志》中譯本始得出現在一九七九年書店的櫥窗里。它使人看了確有欣喜之感,因為這是經浩劫而問世的。從一九五九年出版者約請譯者翻譯此書以來,匆匆歷二十年。漫長的歲月,譯者的黑發變蒼,蒼發變白,怎能不使人痛惜時光的白白流逝和科學文化所歷盡的艱辛呢!
亞里士多德編寫這部《動物志》,曾經化了十二年時間游歷了地中海沿岸和島嶼。他收集、觀察、解剖、記錄了若干水陸動物。大量的資料是他編寫《動物志》的基礎。公元前三三五年亞里士多德在雅典創辦了“呂克昂學院”。在二十年的教學生涯里,他繼續對各種動物進行征集和研究。亞里士多德裔出于希臘醫學和醫業世家,自幼習熟了解剖功夫。動物學是呂克昂學院的基礎課程。各城邦來就學的學生也幫助亞里士多德收集動物標本,協助他解剖和繪制圖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一個學生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亞歷山大支持他童年的老師的動物研究工作,曾通令他國境內(包括地中海周圍歐亞非地區)的臣民,凡獲得珍奇動物都要送交雅典的亞里士多德學院。這學院當初除了教室、圖書館之外,還特設有博物(標本)室。亞里士多德和他的學生們還常常走訪獵戶、牧民、漁人,廣泛地聽取和記錄他們的見聞與經驗。這部包括有五百多種動物的記載和研究、以及當初在學院的一些報告和講稿的書,后來竟不期而成了二千年來世界各國動物研究的祖本。
現在出版的《動物志》翻譯的底本是普魯士研究院貝刻爾校訂的《亞氏全集》(一八三○——一八七○)中希臘文本第四冊。漢文譯者著手于這本書時,先用原文和希臘文的鮑尼茲(Bonitz)索引,匯集了書中五百多種動物的名稱與其種屬,校比了拉丁譯本、英德文譯本的各個索引,編著了自己的希臘——英——漢文索引,尋繹了西方分類學上相關的史實,所征引的俗名與學名,也從中國舊辭書以及中國詩文中鳥獸蟲魚的箋疏和現代動物學上的名稱作了相應的對證。對于數以千計動物學、解剖學、生理學、胚胎學的古希臘學術名詞和歐美現用名詞及中國現用名詞也一一作了對征,用此編制了全書六個索引(見于本書附錄485—569頁),并以此貫串了從頭到尾所有的章節,這樣,就保證了對原著的理解。經過這種仔細審慎的準備工作然后完成的譯文,是比較能夠免于錯漏的。
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志》是現代動物分類學的祖本。亞氏對他所收集的五百多種動物,各依它們的構造(解剖學)、蕃殖(胚胎學)、發育的實況以及生態學觀察與記錄,分成若干“類屬”(綱目),而在同一“類屬”中又憑其一一差異,分離為若干“品種”。“品種”這一自然與類的基本單位的定義,就始原于這書。林奈(Linnae-us,Carlus,1707-1778)生物與類的“兩名法”正是承接于這書的分類體系。在這本書里,可以看到大量解剖學和生態學的記載。單就鳥綱來說,就有一百六十種之多。林奈動物分類中的種屬名稱大多取自亞氏《動物志》。約略在同時代,中國動物學家們所知的鯨、
亞氏的“自然級進”(ScalaNature)觀點正是進化論的基礎。他注意到動物綱目之間,種屬之間各都有介乎其中的間體,他由這些間體想到動物界雖分門別類,千差萬別,但也可以互相過渡的。由于生活的地區不同或食科不同,或蕃殖(求偶)形式不同,就可引起種種差異。實際上它們該是可以通譜的。在卷八章一(漢譯本338-339頁),亞里士多德寫道:“自然的發展由無生命界進達于有生命的動物界是積微而漸進的,在這級進過程中,事物各級間的界線既難劃定,每一間體動物于相鄰近的兩級動物也不知所屬。這樣,從無生物進入于生物的第一級便是植物,而在植物界中各個種屬所具有的生命活力(靈魂)顯然是有高低(多少)的;而從整個植物界看來,與動物相比時,固然還缺少活力,但與各種無生物相比,這又顯得是富有生命力的了。我們曾經指出,在植物界中具有一個延續不絕的級序,以逐步進于動物界。在海中就有某些生物,人們沒法確定究竟是動物還是植物。某些生物有根,譬如江珧,是著根于某一地點的,倘予拔出,有些就會死亡;……這類<動植間體>生物,如所謂‘海鞘以及‘水母(海葵)等,它們的體質猶類似肌肉,至于‘海綿就在任何方面都象草木了。這樣,在整個動物界的總序內,各個種屬相互間,于生命活力與行動活力之強弱高低的等級差別是實際存在的。”亞里士多德在《構造》卷四章五中也談道:“自然自無生物至生物(有魂物)界,許多種屬實具有如此連綿不斷的程序,動植物間有似動似植的兩態間體”。
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級進”觀念,也見于他另一本書《生命論》的卷二章三。他說生物的發展,“各種植物進向于動物,各種動物進向于人類。”可是,應該注意的是:他在《動物志》中,雖于人類的生理解剖、蕃殖等事講得很詳細,但作為動物類別的人,還是和猿猴等一樣,列在哺乳綱(即獸綱)中,沒有特別予以論述。
亞里士多德認為級進的過程是受“生活區域(環境)”的影響的。動物所以“發生差異(造成差別)”或者說“它們身體構造得這樣特別”,那是生活環境的產物。這些論點,雖然在現代生物學上看來,論證還不夠充分,可是他的基本觀點是明白無誤的。宇宙萬物必可通譜,生物本于一源,只是積萬世萬萬世的演化,遂爾形成了當前不可勝記的形形色色的種別。
《動物志》里,那些動物生態學的描述,在在都說明這個“級進”的思想。達爾文深知他的《進化論》的那些論點和事例,亞里士多德實為先導,所以說:“林奈與居維葉各有造詣,我看到他們仿佛是生物學界的兩尊神,可是比之于亞里士多德,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學童。”(富蘭克林·達爾文《達爾文生平與其書翰》卷三,《答威廉·渥格爾(W·Ogle)書》)所以,瑞士學者布克哈特(Buckhard,J·L·)早就稱亞里士多德為生物學史上的第一位進化論者了。
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志》主要是自然的實錄,有時也間出詩筆。在西方,該書也是動物文學的祖本。書中象“悲鴻的哀歌”,“玄鶴的徙翔”,“鯽魚的播遷”,“海豚的聽歌”,“鱷、
將雛方冬來翠鳥,
莫使鳥雛傷狂飚;
海天嘉節清和甚,
靜茲漪瀾十四朝。
在這些日子里,那與昴星同來的北風暫歇,老吹著輕微的南風。……這鳥只在冬至間昴星西沒的清晨一露其羽翮。當船舶中途拋錨的時候,它偶爾下飛,曾未棲止而翩然已逝,……”。這優美的文筆,把靈巧秀麗的翠鳥活靈活現地呈繪在紙上,呼之欲出。
《動物志》最后一章是用一段“漂鳥”的詩句(附錄于后)作為全書的結尾。這“漂鳥”正是我國《禮記·月令》中所說的四月出現的“戴勝”,這十四行詩把“戴勝”乘時發情,應節換羽的美麗形象描寫得淋漓盡致。在后四行的詩里又把這超群出眾的鳥兒比擬為失意的名士,在秋風初起時,歸隱窮谷,正象《詩經》中那“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的手法一樣,把鳥兒人格化了。在這些詩句的翻譯中頗見譯者中西學術根底的深厚。以唐人七古絕句譯翠鳥詩,以西方詩十四行長句的韻律譯漂鳥詩,相當傳神。
讀了《動物志》漢譯本,使人尤覺可貴的是譯者貫串始終的那種嚴謹的治學態度,這從該書的腳注和附錄里就可以感覺到。亞氏遺文是二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臘文,其間經過傳抄轉譯,有很多難以理解的地方,譯者在腳注里分別一一銓注,使讀者一目了然。至于附錄中編錄的六種索引更花費了譯者不少心血。單就這五百多種動物的名稱,包括中西分類學上的名稱,西方俗稱,中國古籍中的名稱,要查核清楚,就是件十分細致和相當艱苦的工作。此外,生物學、生理學、解剖學、胚胎學、病理學的古希臘名詞與歐美、中國現用的拉丁文、英文、漢文名詞需要一一校對,然后才能編錄出貫串全書的索引,不花費大量勞動是辦不到的。
使人感到不無遺憾的是,這樣一本古代典籍,它的前面應當有一篇譯者的“序言”。序言中除了把本書的主要內容予以介紹和評論外,也應當把這本書問世的經歷記錄下來。
最后,在喜讀《動物志》的時候,更想到亞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版是該早日實現的,因為這個計劃還是一九五六年提出的啊!
附:“戴勝”詩
戴勝見到自己的卑微,
大神卻令穿上多樣的花衣:
有時是一只戴著盔纓的山鳥,
有時又換上了蒼鷹的白毛;
跟著節序的變易,
脫掉銀灰的羽翼,
正當春光來到林蔭,
他就重新打扮全身。
這套冠履顯得他年輕又且美麗,
而那銀灰的古裝正合老成的旨趣;
等到坡上黍黃的時候,
還得配些秋色的文繡。
然而世事總不能盡如鳥意,
他從此深隱到何處的山里。
(《動物志》,〔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1.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