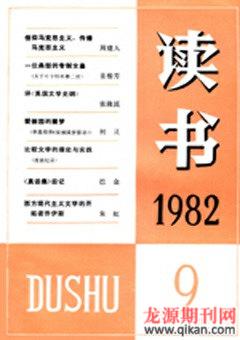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為促進比較文學研究并交流學術思想,《讀書》編輯部和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于六月二十八日邀請北京部分教授和研究工作者召開座談會,下面是發言的一部分。
比較文學研究在我國重又興起,是件好事,對認清中國文學的特點地位、推動文學的發展具有相當意義。
周玨良:比較文學的研究,在我國很有點歷史了。我們在清華讀書時,吳宓先生就搞這個。在座的朱光潛先生在三十年代發表用英文寫的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給我的印象很深。其中有一章論中國文學為什么缺乏悲劇。中國的觀眾不能接受悲劇,什么悲劇都要來一個團圓的結尾,起碼也要象竇娥冤那樣,靈魂出現,這都與中國人的倫理觀念有關。這是一篇很好的比較文學的文章。錢鐘書先生的《談藝錄》、《管錐編》更是這方面研究的優秀成果。現在有不少文章重提這個問題,不少評論家和文藝理論研究工作者對此有興趣,是件好事,令人鼓舞。
陳冰夷:比較文學研究,五四以后就已經有前輩的專家們介紹到我國來,而且在對中外文學的比較研究上作出了不少成績。遺憾的是后來有相當一個時期,這種研究方法在我國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因而被否定了。但是在我們的文學研究的實踐中,卻常常不自覺地還是在運用這種方法。例如,有不少論文和著作是評論外國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對我國現代的新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的影響的。這實際上就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影響研究”的表現。現在我們重新提出比較文學這種方法,而且已經發表了許多有關的文章,這種研究和探討是完全應該鼓勵的。
黃藥眠:我贊成把比較文學的研究重視起來,并逐漸擴大范圍。首先從我們中國文學同近鄰國家的文學加以比較。這里不能夠有民族自大主義。我們的文學史過去一直是關起門來講的,一直只講咱們這一家。一講就是“《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而且常常是越古的東西評價得越高,好象唐以后的文學就不值得一提似的,其實在我看來,中國文學史,唐以后才更加豐富。但當時如果沒有印度的音韻文學輸進來,那么唐詩還是有,可能就不象今天的唐詩那樣了。
中國的文學是生長在中國的土壤上,顯然首先是同中國人民的生活有血肉聯系。但關起門來講中國文學的特點,是難于把自己的特點講清楚的。我們也常提到變文、說唱文學、俗講、評話等與印度文學有關,但由于缺乏印度文學的修養,究竟具體的關系怎么樣就說不清楚了。
同樣是一種學說,在他們本國,影響并不大,但是傳到外國,影響倒很大。如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經魯迅翻譯過來以后,對當時中國的青年文學家影響很大,在日本倒并不大。為什么呢?據我猜測,這是由于我們當時的中國青年有很多人正處于苦悶
朱光潛強調,真正的比較研究,對縱的傳統和橫的影響都不應忽視。
朱光潛:做一切科學工作,都免不了要比較,或者相關的問題比較,或者發現了問題來比較。說比較,不外是兩個方面:縱的,文化遺產有什么,哪些是應當繼承的;橫的,各民族的相互影響,接受了什么外來的東西。我想,真正的研究一定要看這縱的傳統和橫的影響。這樣,比較文學的范圍就應當非常寬,不能狹窄。我過去在國外,搞過“拜倫在希臘”這個題目,就是用比較的方法,研究拜倫給希臘什么影響,他本人又受到什么影響。
我們既要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多下功夫,又要睜開眼睛看世界,通過比較文學的研究,我相信,一定會對我們的文學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
簡單比附是當前已經出現的一個問題,周玨良等提出,搞比較研究應當具備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的態度,不要絕對化、表面化,要把中國文學放到同時期世界文學大潮中去考察。
周玨良:搞比較文學,讀一種文學不到一定的程度不要比。特別是中國文學,用比較傳統的方法讀起,要讀透,先不要牽進外來的東西。讀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所選擇,知道哪些值得比,哪些是表面現象,不值得比。象我們的詩歌,里面詠菊花的很多,外國作家詠玫瑰花的多,這樣比,也可以,但沒什么意思。
楊周翰:比較文學的面很寬,一個是影響研究,一個是平行發展的比較,這是一個很有成果的領域。但對這個問題千萬不要絕對化,以為文學研究只有比較一途,這很危險。還是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歷史的態度,不能為比較而比較。如就因為某某作家與另一作家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比較起來,這樣不一定會出什么成果。比較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要有明確目標。
陳冰夷:對待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我們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研究。運用這種方法的時候,要避免牽強附會、簡單化、庸俗化的偏向,特別要注意排除“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影響;同時我們還要進一步努力發揚我們民族文化的傳統,創立富有我們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中國學派的馬克思主義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
李健吾:最近英國一位學者給我寄了篇論文,《論李健吾戲劇》,說《母親的夢》受辛格《騎馬下海的人》的影響。的確有影響,我那時非常喜歡《騎馬下海的人》,可也不全受他的影響,我寫的是自己的母親,苦了一輩子,很可憐。詩,我受英國整齊派的影響,每隔兩行押一個韻,大家翻早期的《語絲》可以看見我的詩。所以影響是哪個領域都存在。但誰要研究我,還必須回到歷史里去,歷史在限制,環境在限制,出身在限制,我還是我自己,不了解這一點,批評就會弄錯。
溫儒敏:比較文學要求從宏觀或整體的角度來分析文學現象,把中國文學放到同時期世界文學大潮中去考察。但我們有些文章還只滿足于尋找中國某一具體作家作品與外國某一具體作家作品的相同點或相異點。這種研究的視野未免狹窄,甚至容易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如考察魯迅如何受西方文藝思潮影響,搜羅一些魯迅有關語錄或作品,作些表面的歸納后冠之于“現實主義”或別的什么等等,再從國外思潮中找幾條印證,這樣得出來的結論就難免片面。只有從魯迅本身和他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乃至世界文學思潮總的趨勢出發,來考察魯迅是如何多元地有批判地吸取外來思潮的營養,并且分析魯迅是如何受制于時代思潮而又表現其獨創性,這才可能比較接近真實的魯迅。
桶周翰認為,中國封建文學與西方中世紀文學的比較研究大有可為,值得下一番功夫。
楊周翰:前些時候給外文所的研究生講中世紀文學,想到一個問題,中世紀文學是封建文學,中國幾千年的文學都是封建文學,都是封建文學,如果要找一個比較的基礎,這就是個基礎。所以,中西中世紀文學比較可能比出一些東西。比如,西方的中世紀文學做夢特別多,中國的這種手法也是有的,如《紅樓夢》。我特別分析了英國十四世紀的一首詩叫《珍珠篇》,說的是一個詩人的女兒死了,詩人非常懷念,在她的墓旁睡著了,做了個夢,夢見她的女兒已成為耶穌的新娘。詩人想過河跟女兒生活在一起,女兒說,不行,一個凡人只有死了才能過河。中國也有哭女兒的詩,我在《清詩別裁》里看到一首,“十歲言詩有性靈,木蘭愛說替爺征,黃泉不是黃河水,聞否爺娘喚女聲。”這與西方想念女兒很不一樣,西方常常聯系宗教,中國常講的是人倫、世俗方面的東西。我覺得中國跟外國特別是封建文學方面可研究的東西很多,可惜我們對西方中世紀文學不很注意。
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匯通,是近年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溫儒敏對此有一些看法。
溫儒敏:我做過一個大略的統計,僅一九八○年以來發表的這一類文章,就有二、三十篇之多。這些文章大都以影響研究為多。中國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一個顯著的區別,就在于它受外國文學很大影響,從文學觀念到文學形式都日益與世界現代文學融匯。五四新文學既是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產物,同時又是外國文學思潮涌進的產物。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面目,認識這短短三十多年文學史提供的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不能不進行影響研究的。現在發表的這一類文章,大都只就某個重要作家而論,而且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比較客觀地考察這些作家如何按照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對外來文學思潮進行篩選和改鑄。如魯迅對進化論、郭沫若對泛神論、茅盾對現實主義、郁達夫對盧梭的人性論等等,無一不是經過改造,植根于中國的現實土壤,才結出豐碩的成果。這種有分析的結論,和過去某些比較文學家囿于“歐洲中心論”的結論大相徑庭。他們并不把影響看作是一方施加、另一方消極接受的簡單過程,這當然更符合歷史的真實,也更能啟發人。讓人們認識到應該如何正確對待外國文學思潮。
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不妨站得高一些,視野再擴大一些,不但要繼續研究個別作家所受外來影響,更要注意從同時期世界文學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的許多現象。可以抓一些大的題目,作綜合的考察。比如,中國現代文學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走過了西方國家用上百年時間所走的途程,這造成了哪些特點?有什么經驗和難免的缺失?二十年代初葉在中國發生的東西文化大交流,無論規模還是影響之大,在世界文學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又有哪些東西值得總結?為什么在涌進中國的種種文學思潮中,現實主義能逐漸占了主導面?當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學日益轉向現代主義時,為什么中國作家卻較少受現代主義影響?這里是否光有經驗而無缺失?歐美、日本、蘇俄等不同國家文學思潮對我國不同的文學社團、流派到底產生過多大的制約或影響?現代中國大多數作家如何受制于傳統文化和現實變革而形成某種比較共同的創作心理等等。乍看起來,題目很大,但如果運用比較文學的廣角鏡來考察,也許能看得更清楚。
陳冰夷認為,文學的比較方法可以運用得再開闊些,不但古典文學可以比較,現代、當代文學也可以比較;而在當前,后者的比較研究更有現實意義。
陳冰夷:三中全會以來,由于實行了思想解放和撥亂反正的方針,我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有了空前的進展。如果我們思想更開闊些,試試運用“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比較方法來研究研究我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規律,我想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繁榮是會起促進作用的。
近幾年來,我們有一部分作家,主要是中青年作家,在創作上努力探索和開闖新的路子,發掘新的思想內容和尋找新的表現方式,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績,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學增添了新的光彩。這是可喜的現象。但是與此同時也有些作品表現了不健康的思想內容和與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人民群眾欣賞習慣格格不入的藝術形式。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現象。以上兩個方面,在許多地方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其中或多或少有著外來的、特別是西方當代文學影響的痕跡。我們是否可以在運用其他有效的研究方法之外,不妨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研究和探討一下西方當代文藝思潮對我國當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到底有些什么影響,它的得失、利弊如何,如何正確對待等等。這都是在新的形勢下發生的新的問題,要采取相應的新的方式來解決。
我們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批判吸收外來文化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足以讓我們回顧和借鑒。古代的不說,五四運動以后我國新文學的興起和發展,是繼承和發揚了我們民族的古代文化傳統和廣泛吸收了外來文化的結果。后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學習了國際的、特別是蘇聯早期的無產階級文學的經驗,在我們自己的土壤上產生和發展了我國自己的無產階級文學。這里有很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失敗的教訓,至今還沒有而迫切需要進行系統的總結,以便今后更加自覺地繼承和發揚五四以來批判吸收外來文化的優良傳統,更加自覺地避免重犯過去犯過的“全盤西化”和“照搬某國”的弊病,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學得以更加健康和興旺地成長。這項工作顯然也是比較文學方法的研究對象。
各國和各民族文學相互之間的交流和影響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對于當前我們文學界發生的上述現象,需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方式來解決。在文化上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是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于外來文化要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研究。閉關鎖國,排斥一切外來文化是錯誤的,不加分析地照搬一切外來文化,也是錯誤的。這方面我們過去有過很多經驗教訓。對于有利于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的外來文化,要放手大膽地批判吸收,但是對于不利于和有害于發展我國文學的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的思想影響,一定要堅決抵制。我們既要比較我國當代文學和西方當代文學的異同之處,更要比較我國和西方國家的社會性質和文化傳統習慣的異同之處。我們要對這兩個世界和兩個方面作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透徹的了解和比較研究,從而具體地作出判斷:哪些東西可以吸收,哪些東西應該批判地吸收,哪些必須堅決排斥。這恐怕也是屬于比較文學研究當前一項重要的任務。
通過比較東西方對文學的根本認識,李賦寧談對三類文學作品比較研究的看法。
李賦寧:比較文學研究應當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文學的性質、作用和價值。回答什么是文學或什么不是文學這個問題,東方和西方有各自不盡相同的答案。中國有文以載道的傳統看法,西方也強調文學寓教導于娛樂之中。文學的定義,也有廣狹之別。例如一般的政治、歷史、哲學著作就不是文學作品。但是其中又有一些優秀的著作卻被公認為文學作品,例如柏拉圖的《對話錄》、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等等。那么,界限應該劃在哪里?一般說來,文學作品與題材或內容的關系并不十分密切,主要看它是否具有獨創性和高明的寫作技巧。換言之,文學作品必須具備某種優秀的質量——無論是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或美學的優秀質量。具備這種優秀質量的著作才有資格進入國別文學作品的行列。但這種著作是否能進入世界文學作品的行列,這就要靠比較文學研究來回答了。這一類文學作品我們叫做第一類文學作品(或廣義的文學作品)。
第二類文學作品可以稱為幻想文學、虛構文學。這類文學作品以小說為主,也包括偵探小說、科學幻想小說等次等文學(subliterature)在內。這類文學作品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虛構性。虛構可以提出一定的改造社會的理想,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鳥》提出的“云中杜鵑城”,柏拉圖的《理想國》、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等等。這些作品屬于高級虛構文學或嚴肅文學的范疇。也還有低級的、通俗的虛構文學,如英國文學史上十八世紀末葉的哥特式傳奇等。在第二類文學作品范圍內,還可以區別優秀的、嚴肅的愛情小說和一般庸俗的言情小說、才子佳人小說。可以比較不同國別文學中優秀的、嚴肅的愛情小說,甚至還可比較研究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總之,在這類文學作品領域里,比較文學研究也有廣闊的天地。
第三類文學作品可以稱為純文學。如哈代的小說《苔絲姑娘》。這類文學作品是嚴肅的、高級的文學作品,它的特征是在作品中美學作用占主導地位。所謂美學作用,在于這類文學作品能夠發人深思,能夠凈化人的感情和靈魂,使人追求更高境界的真善美。因此這類文學潛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是巨大的。這類文學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希臘悲劇,莎士比亞戲劇,十九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當然,優秀的詩歌作品,如雪萊的《西風頌》、密爾頓的《失樂園》等也在這個行列。這里,我們可以比較研究但丁的《神曲》和屈原的《離騷》,華茲華斯的詩歌與陶淵明的詩歌等等。我認為第三類文學作品的比較研究應是我們的研究重點,因為通過這種比較研究,我們能更深刻地總結出世界文學寶庫中最優秀的作品和特點,以便國別文學作家繼承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從而創作出更優秀的現代作品,使世界文學寶庫不斷增加新的財富,進一步豐富、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
具體作家、作品的比較研究固然重要,但季羨林、張隆溪認為更應該提倡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
季羨林:前幾天開會談大百科的辭條,碰到中國文學卷、歷史卷里面的老調比較多,如對中國文學家的評價,講韋蘇州,說“風格婉麗、音調流美”,說孟浩然“自然渾成,而意境清雋、韻致流溢”,講駱賓王“格高韻美、辭華朗耀”,說張九齡“纏綿超曠,各有獨至”。過去中國文藝理論評論作家、詩人往往使用這些詞句,看著好象懂,可究竟什么意思,說不出來。我想,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時間相當久,水平相當高,人相當多,《文心雕龍》、《詩品》,多得很。特別是詩話,多極了。講神韻,講性靈,到王國維講境界,講“隔”與“不隔”,這些詞兒,要翻成外文毫無辦法,可我們的文藝理論就這些詞兒,我們的表達方式和歐洲不一樣。這些詞兒不僅是一些術語,我們的文藝理論體系和這些詞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把這些詞兒的含義弄清楚,也就弄清了我們文藝理論的體系。世界上講文藝理論只有三個地方能言之成理,自成體系。一是中國,有幾千年了;另是印度,它的文藝理論相當多,也有些名詞象中國這些詞,現在也說不清;還有西歐,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爾、歌德、席勒到近代的立普斯、克羅齊等。這三套理論的表現方式不同,歐洲評論就不說韻致流美、意境清雋這些話。我想現在我們也應該用科學的語言,明確的語言,明白的語言。三十年代初,在清華大學聽朱先生講文藝心理學,到現在五十年了,還忘不掉。我想中國的這套東西,只有用比較文藝理論的研究來解決。歸納起來就是說,以馬列主義的文藝學為基礎,再學點自然科學、心理學,這樣經過努力,我們中國文藝理論就能用明確、科學的語言說清楚了。
張隆溪:只有加強理論的比較,具體作品的比較才能深入。我講一個例子,這也涉及到文學和哲學、文學和宗教間的關系。
中國論詩講神韻,以禪入詩,實際是把宗教概念借到文學當中來。中國詩講含蓄,似也和宗教的神秘性有關。錢鐘書先生早在《談藝錄》里就指出過詩秘與神秘間的關系。柏拉圖《對話集》的《伊安篇》中講到靈感的問題,他認為詩人本身只是平常的人,只有神靈附在他身上,有靈感時才能寫出好詩。西方講這個東西最多,但丁就用中世紀解釋《圣經》的辦法來解釋自己的《神曲》,借用了宗教的神秘性概念,認為詩的語言有高于字面意義的象征意義。在中國,最早在周易里講“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實際上這是講了言、意、象三者之間的關系。書面的語言文字,甚至形象,都不能完全傳達詩人的意圖,于是要追求所謂“象外之象”、“韻外之致”,于是要含蓄,要暗示,要“言有盡而意無窮”。這在歐洲講的也很多,如德國近代哲學家卡西列在《語言與神話》一書中說,任何語言都只是一種象征,是個中介、媒介,而任何媒介又必然要濾掉某些本來的意思,因此任何說出口的語言都不全是本來真正要表達的意思。他引席勒的一段話說:“當靈魂說話的時候,說話的已經不是靈魂了。”這段話頗可以拿來為神韻派的理論作注腳。美國當代詩人麥克利希(A.MacLeish)在《詩藝》一詩中說,詩應該是沒有聲音的,詩不應該有意思。這實際上是神韻派那種理論。就是說字面的語言不能表達詩人真正的意思,應該有一種韻外之致,讀者體會作者的意思要通過分析作品本身去細細體驗。我覺得這些都只有通過比較的研究,廣泛地把中國的、西方的、古代的、當代的聯系起來,甚至聯系到其他藝術領域,如音樂、繪畫,聯系到文藝以外的領域如哲學、歷史等等,有些文藝理論才能講清楚。孤立在一個國家,或孤立在文學作品的范圍內研究,就很難看清楚。這說明,比較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存在并且發展,正是由于它能夠提供一些我們在局限的范圍內不能得到的啟示。我想,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應該是大有發展前途的。
嚴紹
嚴紹
目前,當比較文學研究在我國文學研究領域里興起的時候,我們應該在繼承世界比較文學研究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致力于創建具有東方民族特色的“中國學派”。只有這樣,才能與中國文學的悠久歷史,和它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相稱。
這一構思中的“中國學派”的研究任務,我以為至少應該有三方面:
第一,探討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發展的影響,從而闡明它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同時,也探索外來文學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影響,從而闡明中國文學對外來文學的分解與融合的能力。這一研究任務,應該看成是構成“中國學派”的基礎。
第二,在與世界文學的比較研究中,真實地(而不是臆想地)揭示中國文學的民族特色,闡明這種特色形成的過程、與外來文學的關系、在世界文學發展中的意義,并力圖使這一研究成果成為當今作家從事創作的借鑒。
第三,把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發展中的一種形態,與各國(民族)文學相比較而探索文學的一般規律,從而闡明人類形象思維的基本特征,揭示文學的本質。這一任務,應該作為構想中的“中國學派”的最終目的。
要實現這樣一些任務,我們在方法論上應該有所突破,所謂“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都不是絕對的,而常常是互相包容的。事實上,實際的研究中還必然會采用文學史的方法和文藝批評的方法,否則無法得出結果。因此,我以為“中國學派”既不排斥“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更應該從實際研究中摸索出一種適合于完成我們任務的“綜合性研究”的方法論。
老一輩的學者,為創造“中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但大量的實際研究,還有待于中青年來做。我們現在面臨的狀況是,既有興趣卻又缺少素養。比較文學研究,它必須在熟悉兩國以上文學及其歷史文化的條件下進行工作,簡單的“比附”與“類比”,不能給人以什么啟示。我以為,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比較文學研究者要以更加踏實的學風,進行更加刻苦的學習和實在的研究,提高修養,不務空名。只有這樣,比較文學的研究才能逐步在我國得到發展,我們也才能在世界的比較文學研究中,創建起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國學派”。
座談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