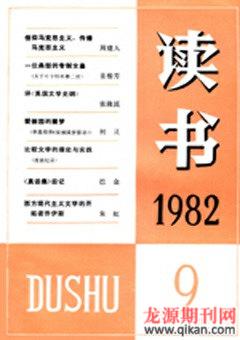社會信息及其反饋
盧昌亞
人對世界的感知依賴于大腦的活動,而大腦這個神經中樞大約要接受四百多萬條神經纖維所傳來的脈沖信息。在這其中,通過兩只眼睛傳入的纖維就有二百萬條(占一半!)之多,所以一閉上雙眼,切斷了視覺信息,腦細胞就非常容易處于抑制狀態,甚至進入睡眠。這是神經生理學的事實。它告訴我們,信息是大腦活動的必要條件。
讀了控制論的創始人諾伯特·維納(NorbertWiener)的《人當作人來使用——控制論與社會》(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以后,誰都會感覺到眼界為之一開。原來社會中也充滿著信息因素,而且社會信息的傳輸和反饋也正是社會得以存在并發展的條件。維納在本書中把他的控制論原理在倫理學和社會學方面的某些含義作了說明,因而使得他的思想不但為自然科學家,而且也為社會科學家所注意。維納寫道:“信息是我們適應外部世界,并且使這種適應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過程中,同外部世界進行交換的內容的名稱。接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過程,也是我們在這個環境中有效地生活的過程。現代生活的需要及其復雜性,對這個信息過程提出了比以往高得多的要求。我們的報刊、博物館、科學實驗室、大學、圖書館和教科書都有責任滿足這個要求,否則就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要有效地生活就要有足夠的信息。”
人類社會的事物無不處在社會信息流的某一循環之中。就拿一本書的命運來說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籍,是依賴于編輯提供了信息,而編輯的信息則是從作者那里獲得的,作者又是從其本人所接觸到的生活中攝取原始信息的,經過思維活動和藝術加工而定稿。反過來,一本書籍出版了,給讀者帶來了新的信息,讀者對書籍的反應和意見又成為一種信息,再輸送到作者那里,供其作為再版、修訂或寫作新書的參考。
這后面一個相反的過程,就是維納所謂的反饋。反饋是從英文“Feedback”譯過來的,照字面譯是“反過來喂”的意思,譯作“反饋”顯得更文學化、技術化了。饋者,送也。簡單地說,反饋就是信息的反向輸送。比如上述的讀者對書籍的意見再輸送到作者那里,就是一種反饋。有正反饋和負反饋之分。如果反輸的信息強化了原來的過程,叫做正反饋;如果是削弱,就謂之負反饋。
運用這種反饋理論,能說明社會上的很多現象。例如,文學藝術是社會信息大系統中反應極為敏感的一個子系統,信息的反饋作用也體現得尤為明顯。作者(包括作品的所有創作人員)從生活的源泉中汲取原始素材,在符合一定的文藝政策的前提下,通過藝術加工,創作出新的作品。作品進入社會,在群眾(包括讀者、聽眾、觀眾等)中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果。這種社會效果必然會導致一定傾向的評論,而這種評論又對作者及其再創作產生影響。而且,文藝領導部門對文藝政策的決定和調整又離不開社會生活的實踐和作品傾向所導致的社會效果。要之,上面各個環節之間的信息傳輸和反饋關系能夠構成一個封閉的體系。
上述多信息系統各個環節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密切和相互作用的。對于整個系統的穩定來說,存在于環節之間的信息流的傳輸和反饋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中評論信息從質的方面來說有兩種:贊揚和批評。前者可以看作是對系統的正反饋;后者則可以看作是負反饋。這兩種反饋在不同的情況下都是極為重要的。正反饋有利于肯定佳作,鼓勵作者,激發才智,不至于埋沒有生命的萌芽;負反饋則有利于揭發錯誤,糾正偏頗,克服缺點,不至于助長邪惡。
事實上,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遇到大量的信息和反饋的問題,不論是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和文學等領域都普遍存在。人們要組織有效的社會生活,就不能不去深入地研究各種社會信息及其反饋,特別是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日益趨向整體化的今天,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