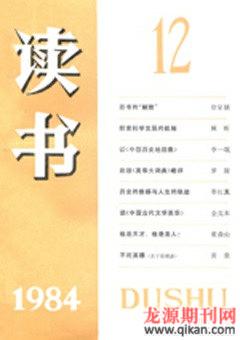詩的窗戶
鐘元凱
中國古典詩論述評(續)
三.技巧的批評
在古代,寫詩并不是少數詩人的專利,它是知識階層中普遍的風氣。廣大公眾對詩歌技巧的關注,使批評家不敢表示冷淡和漠視,何況他自己即使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也至少是個寫詩的人。僅僅為了社交的需要,他也要從前人或同時代人的詩作中尋找門徑,從自己的甘苦中總結經驗。這樣,技巧的批評理所當然地就占有了一席之地。
技巧的批評雖和審美的批評不屬同一層次,但兩者的關系卻至為密切。如果說對某些技巧的追求,是以一定的審美趣味為根據的話;那么,審美趣味的轉變,也經常為技巧的批評開辟新的方向、確立新的重點。舉例來說,中國古代文學從六朝發展到兩宋,審美趣味發生了很大變化:六朝可說是一個追求典雅和文飾的時代,至兩宋則進入了一個崇尚“平淡”和寫意的時代。這在理論上表現得十分明顯。在《文心雕龍·體性篇》里,劉勰歸納出八種風格,這“八體”中占據首位的是“典雅”,其中沒有“平淡”的位置。到了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中,“沖淡”卻一躍而為第二,僅屈居“雄渾”之下。到宋代,人們更競以“平淡”為尚。歐陽修稱贊梅堯臣“以閑遠古淡為意”①,梅自己也說:“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②。蘇軾極力推崇“發纖
這類批評乍看之下比較零散甚至失之于瑣屑,但如果用歷史的線索把它們貫串、排比,仍然不難理出其發展的脈絡來。圍繞著詩歌“文情”和“聲情”兩個方面,傳統的技巧批評也可分為“主文”和“主聲”的兩路:前者側重探討用字煉句、修辭結構等問題,后者側重探討聲韻格律等問題。兩者都有歷史的軌跡可循,例如對字句的錘煉,陸機的《文賦》即已提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心雕龍·隱秀》又指出“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宋人或主張“煉字只于眼上煉”⑤,或主張“字字活字字響”⑥;至劉熙載則提出所謂“通體之眼”和“數句之眼”,⑦可以看出這些批評意見不是在同義反復,而是在不斷向縱深發展的。又如對聲韻的探討,從沈約等人提出永明聲律說,到明代李東陽的《麓堂詩話》,清王士禎的《律詩定體》、《古詩平仄論》,趙執信的《聲調譜》等,都有許多探幽發微的獨到見解,所論范圍也從平仄律的規矩格式推及更廣義的聲調。如果我們把前人關于詩歌技巧的批評意見集中起來,將不僅有助于對中國古典詩歌的鑒賞,而且對于了解漢民族詩歌語言的特性、建立今天新詩的語言形式,也會提供極可寶貴的資料和極有裨益的借鑒。
四、文學史的批評
中國詩歌的發展,使批評家更多地站在史的制高點上作綜合的俯瞰,用以考鏡源流變遷,確定作家作品在縱向坐標上的位置。時至今日,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似乎已經劃然為二,各自成為獨立的學科;可是在傳統批評中,從文學史的角度對作家作品進行考察和估價,卻一直是批評家談詩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成為一個普遍的慣例。
這種慣例的形成,得力于史學的發達。中國自先秦以來就已顯露出史官文化的特征,從兩漢到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史學的興趣空前濃厚,“史筆”的運用也日趨廣泛。于是以史家的眼光和方法,描繪文學發展的歷史并“溯其起源,考其正變”,亦漸浸染成風。首先是一些歷史學家開始了這項工作。班固《漢書·藝文志》中關于“詩賦略”的總論,也許是文學史批評的最早的材料之一,但那是綜論詩賦的,還沒有把“詩”單獨論列。南齊時沈約所寫的《謝靈運傳論》,則可以說是評述詩歌發展史的第一篇完整的論文。沈約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詩歌以“風騷”為源,同時具體論述了自兩漢至劉宋長達幾百年的詩歌變遷的歷史。沈約之后,肖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也闡述了詩歌自建安至劉宋的發展概況,并把時行的三種詩風,一一從歷史上追溯其風格之源。班、沈、肖等人都兼史家身分,這幾篇批評文章也都隸屬于他們所寫的史書之中,由此可見文學史的批評原是從史學中派生出來的,可以說是史筆的擴大和活用。與此同時,這種方法也引起了其他批評家的注意,并為他們所樂于采用。如果我們把《文心雕龍》中的《辨騷》、《明詩》、《樂府》、《通變》、《時序》諸篇合起來,可以看出劉勰對一部詩歌史的完整看法。鐘嶸《詩品序》劈頭一大段,則可視作一部關于五言詩的專史;書中追溯各家風格歷史淵源的方法,也和肖子顯相類似。此后,文學史的批評就一見于史家論著之中,一見于文評家的談藪之中,后世的選家們也恥居人后,每每借選本的“序”或“凡例”來洋洋灑灑地大談詩史,如高
傳統的文學史批評以描述風格的演變為主。在許多批評家看來,一部詩歌史也就是各種藝術風格陵替更迭的歷史。沈約和劉勰在各自的批評著作中,都相當準確地勾勒出自先秦兩漢以來各個時代不同的文風特點。高
這種對風格的描述,又常常伴之以價值的估定。鐘嶸把詩分為上、中、下三品,高
傳統的批評偏重于風格的演變,這個特點同時帶來了長處和短處。其長處是使史的批評執著于文學作品本身,而避免了和作品的過分游離,因為文學批評說到底應該是對作品的批評。但風格畢竟又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只見“果”不見“因”,那我們就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何況時代風格也罷,個人風格也罷,總是相對固定的,盡管批評家的辨析有精粗深淺之分,在個別點上時有精辟的創獲,但大體上卻總是比較一致的,一經前人拈出,后人難免沿襲成說,遂使這種描述愈往后就愈雷同化,好比“百首以上,青蓮易厭”。同理,把史的發展僅歸之于若干風格“一物克一物”的盛衰代變,那也只是對事實的認可,談不上是對規律的認識,最后還很容易走進循環論的死胡同。由此看來,如何在前人描述風格的基礎上,進一步從多方面探尋其形成和更迭的原因,剖析其賴以表現的各種因素,揣摩其歷史意義,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今天的文學史批評理應取長補短、勝古人一著,作出一系列新的發明。
上述這些不同的方法雖然取徑各異,但對傳統的批評家來說,它們并不是河水不犯井水的陌路人,更不是水火不容的冤家,倒象脾性不同的一家人,因此把它們兼容并包在同一著作里,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這個事實說明,古人并不把某種批評方法視為自足的、封閉的體系,他們力圖通過多扇窗戶來窺測藝術的奧秘。圓融、通達的批評態度,是獲得闡釋自由的前提,執一廢萬難免成為跛足的批評。在東西方文明進一步撞擊的今天,我們也許有了一個新的機會,可以把批評的窗戶開多些、開大些,但這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認識自己傳統的緊迫感。因為只有植根于中國的文學土壤之上,只有和綿長的傳統根須相連,絢麗的批評之花才能盛開,才能有悠久的生命力。
一九八四年五月
①《六一詩話》。
②《讀邵不疑學士詩卷》。
③劉克莊語,見《后村詩話》。
④《潛溪詩跟》。
⑤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⑥呂本中《呂氏童蒙訓》。
⑦《藝概·詞曲概》。
⑧《答章秀才論詩書》。
⑨《雪濤閣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