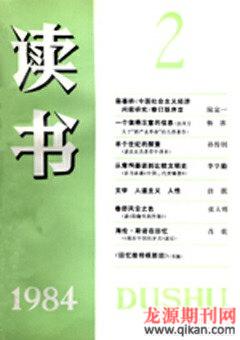丁聲樹同志的治學精神
楊伯峻
丁聲樹字梧梓,凡是和他相交較早較久的,很少人不稱他為梧梓,我寫這篇文字,還是習慣地稱他梧梓。
他的確是“由愛國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他的愛國主義不始于堅決拒絕去臺灣,而是至遲開始于七七事變時。他于一九三八年寫了一篇《<詩·卷耳、
去歲盧溝橋之變,島夷肆虐,馮陵神州。……不自揣量,亦欲放下紙筆,執干戈以衛社稷,遂舉十年中藏讀之書、積存之稿而盡棄之。人事因循,載離寒暑,未遂從戎之愿,空懷報國之心,展轉湘滇,仍碌碌于幾案間,良足愧也。
自然,怎么樣才能真正“衛社稷”,當時只是埋頭書本的丁梧梓是不甚了解的,結果落得“空懷報國之心”而已。那幾句話,不僅是自愧,其中包含多少酸辛。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時,他喜歡聽錢玄同先生的“音韻沿革”和《說文解字》兩門選修課。他是玄同先生的得意學生。他熟于《說文》,又于殘本《切韻》、《廣韻》以及歷代韻書、字書有研究。他寫的畢業論文,玄同先生給他一百分,一時傳為美談,足見他于古人所謂“小學”功力之深。他又長于“經學”,于《詩經》用力尤深,好幾篇關于《詩經》的訓詁論文,結論都鑿切不移。關于他的治學方法,可以說出下列幾點。
第一,能結合實際,解決實際問題。重慶有個北碚,碚字讀培,還是讀倍,不見于各種字書。不少人也不愿意探討這個問題的。一則管它讀陽平聲或者去聲,無關宏旨。二則古今字書都沒收這個字,在古今若干萬部書中去尋覓這個字的音讀,實在太費勁了。梧梓不這樣看待。我不曉得他查了多少書,他卻肯定以“碚”為地名的,不止北碚,更有著名的宜昌蝦蟆碚、荊門十二碚,于是乎遍考兩宋人詩文集和與此有關的書,用各書異體字作“背”,蘇軾、蘇轍兄弟唱和詩都有“碚”字,依詩的格律,應讀去聲。另外還用了若干宋人材料作論證。真是獅子搏兔,用盡全力。古今字書所沒有的字,今天《現代漢語詞典》卻有了,說:“碚,bèi地名用字:北碚(在四川。”連注音短短十一個字,得來好不容易!讀者試翻閱《“碚”字音讀答問》,便足以知道了。山西省南部有個
第二,他每為一文,一定先把有關資料搜集得十分完備。引用各書,必參考不同版本。如果引用“經書”,甚至還參考漢石經殘字,如《釋否定詞“弗”“不”》(載于《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引用《尚書·盤庚中》“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便引《隸釋》所載《漢石經》“弗”作“不”。又如《廣韻》入聲“物”韻“弗”紐內有“不”字,并注云,與“弗”同。梧梓考之敦煌唐寫本《切韻》殘卷,故宮博物院所藏王仁胸《刊繆補缺切韻》和唐寫本《唐韻》,“物”韻內都沒有“不”字,便斷定今本《廣韻·物韻》里的“不”字是宋代人所增加。這樣細密而認真,一直是他治學和工作的負責精神。他的論文所引用的資料是無懈可擊的。
第三,他每為一文,不但收集正面例證,更重視反面例證,也列舉和他論點不相涉的有關例證。總之,前后左右每個方面都考慮周到。拿《論<詩經>中的“何”“曷”“胡”》(載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一文而論,某些用法,只見于《詩經》,《尚書》卻和《詩經》有所不同。即在《詩經》中,也有不同用法,梧梓也舉了出來;甚至《易·損·卦辭》只有一條不符合他的論點的例句,他也舉出來。再舉《詩經“式”字說》(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一文論,他從“式”字每與“無”字對言,“式”又與“雖”字對言,審其辭氣,斷定“式”是“應當”之義。復從“式”字說到“職”字,“職”和“式”古音相近,《詩經》“職”字也有和“無”對言的,因此,“職”也和“式”一樣外,可以解作“應當”。除此之,《詩經》中還有難以解釋的“式”字,他都一一列舉出來,好使其他學人繼續研究。他這種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實足以為今日治學者的楷模。
第四,他每為一文,不但不抹煞前人的成就,就是同時人的幫助,他一定也注明出來,從不掠美。譬如《<詩經>“式”字說》,曾引朱熹《詩集傳》,然后說:“朱因《詩》之上句言‘雖,故增‘亦當二字于下句以足其義,初非以‘當解‘式,而適符‘式字之本旨,妙得詩人之語意矣。”朱熹僅僅偶然得詩人之語意,他也給以說明。又如《<詩·卷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