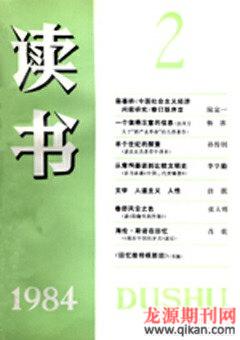關于“三余”
1984-07-15 05:54:46徐正唯
讀書 1984年2期
關鍵詞:美學
徐正唯
北京大學出版社八二年一月版《美學向導》119頁,張岱條下說:
張岱贊賞過去的林和靖與蘇東坡,十分推崇當時的董遇。他說董遇的“三余”之游,即于歲之余——冬,日之余——雨,月之余——夜游覽西湖,能發現和領略一般人平時所不能賞到的湖山之美。
查《西湖夢尋》卷一頭條“西湖總記·明圣二湖”,張岱原文是這樣的:
“……故余嘗謂:‘善讀書,無過董遇三余。而善游湖者,亦無過董遇三余。董遇曰:“冬者,歲之余也;夜者,日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雪
兩段文字相比較,前者把善讀書的三國時人董遇,說成了與張岱同時代的明末人。董遇“三余”讀書的故事,是十分著名的。《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裴松之注,三國時魏人董通常教學生利用“三余”時間讀書。他說:“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也。”晉代的陶潛先生《感士不遇賦序》也說:“余嘗以三余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可見作為典故,“三余”一般是與讀書聯系在一起的。張岱說的是:善讀書無過董遇的“三余”,善游湖的人(即引文中那個“者”字),也要會利用董遇所說的“三余”。并非是張岱“十分推崇”“董遇的‘三余之游。”
另,《三國志·王肅傳》裴注,引董遇原話“三余”為:“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張岱改“陰雨者時之余”為“雨者,月之余”,而《美學向導》作“日之余——雨”“月之余——夜”。董遇“陰雨者時之余”本意最通且貼切,張岱“雨者月之余”勉強可解,而《美學向導》中“月之余——夜”則該作何解?
猜你喜歡
杭州(2023年3期)2023-04-03 07:22:36
美食(2022年2期)2022-04-19 12:56:08
新世紀智能(高一語文)(2020年10期)2021-01-04 00:43:52
瘋狂英語·新讀寫(2020年4期)2020-06-03 07:01:20
文苑(2019年22期)2019-12-07 05:29:06
現代蘇州(2019年16期)2019-09-27 09:30:34
現代裝飾(2019年7期)2019-07-25 07:42:08
商周刊(2018年22期)2018-11-02 06:05:26
現代裝飾(2018年5期)2018-05-26 09:09:26
Coco薇(2017年8期)2017-08-03 0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