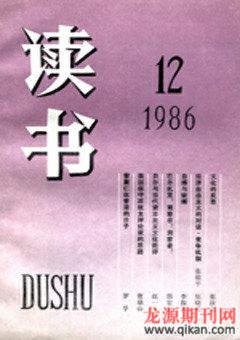音樂王國的西西弗斯
趙鑫珊 丁 聰
“哲學的目標是尋求基本原理的基礎;頭腦是需要借助于哲學才能達到崇高境界的。”
——貝多芬同女友貝蒂
娜的談話
被當代美國小提琴大師斯特恩(Stern)譽為當今最偉大的大提琴家馬友友(美籍華裔)拉了二十幾年的巴赫組曲,如今對巴赫的音樂依然不時有新的發現,賦予新的理解。
為什么會如此呢?對巴赫的一首曲子難道也會不斷有新的發現和理解嗎?要知道,天地人間只有少數幾樣東西才需要人類對它們不斷作新的發現,賦予新的理解。德國古典音樂正在這幾樣東西之列。因為它們都是人類靈魂的披露和人類本身的再現;德國古典音樂是旋律化了的德國古典文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總的匯合和交融。我們對巴赫、亨德爾、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音樂的新發現、新理解,就是對人類本身,對我們自己靈魂的廣度和深度的新發現、新理解和新的驚異。
在整個西方音樂史上,貝多芬大概是談論哲學最多的一位作曲家。當然,他所談論的哲學是一種廣義的文化哲學,即對人、社會和大自然以及這三者的內在關系的緊張而深沉的思索。
當貝多芬用德語陳述自己的哲學見解的時候,他充其量是一個三流(甚至還不能入流)的哲學家;可是,當他一旦改用旋律(音響)語言在鋼琴、提琴和銅管樂器上陳述自己的哲學思想和世界觀的時候,全世界都要畢恭畢敬地傾聽他那雷鳴閃電般的英雄絕唱。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只有外在的生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有的人(如偉大的科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除了外在的生活,還有波瀾壯闊的內在生活。然而正是這看不見的內在生活,正是他們的思想感情,正是他們的靈魂、胸臆和意志,才造就了他們,使他們形骸不存而精神不朽,使他們“其人雖已段,千載有余情”。
貝多芬當在這萬古不朽者的名單之首。
“貝多芬的一生算得上是幸福的嗎?”——近年來,當我聽完他的樂曲,看完他的書信和有關傳記,我就常常會這樣問自己。
這個問題可不容易回答。因為它涉及到人生哲學的最微妙處。而哲學問題的答案往往是模棱兩可的。也許,哲學只有不斷提出問題而沒有最后的答案。
論外在生活,貝多芬的一生當然算不上幸福。耳聾、經常處在孤獨之中、多次失戀(終生沒有點燃起家室的爐火)和其他種種的疾病、煩惱、痛苦纏身,還有經濟拮據,生活上的窘迫,哪有幸福可言?
那末,論他的內在(精神)生活呢?
我想起了古希臘有關西西弗斯的神話。
西西弗斯被眾神判決推運一塊巨石至山頂。由于巨石本身的重量,到了山頂總要滾下山腳,于是西西弗斯又得把石塊推上山去,如此反復,永無止境,永遠也沒有盡頭。眾神認為,讓西西弗斯服這永恒的勞役是最嚴酷的懲罰。作為一種哲學比喻和象征,西西弗斯的命運仿佛就是人類的命運。貝多芬和歌德的命運,還有康德和黑格爾的命運,都是西西弗斯式的,而且都很典型。
一八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歌德對愛克曼說:
“人們通常把我看成是一個最幸運的人,我自己也沒有什么可抱怨的,對我的一生所經歷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地工作。我可以說,我活了七十五歲,沒有哪一個月過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象推一塊石頭上山,石頭不停地滾下來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將是這番話的很清楚的說明。”(《歌德談話錄》,第20頁)
歌德嘔心瀝血,不停創作辛勞的一生,是典型西西弗斯式的一生。但是他并不抱怨。他飽嘗了創作的甘苦。
貝多芬的一生又何嘗不是如此?附在本書后面的貝多芬生平活動年表也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從十二歲起,貝多芬就開始服西西弗斯式的永恒勞役,推命運的“巨石”上山。一七八二——一七八四年,即從十二至十四歲,少年貝多芬便創作了三首鋼琴奏鳴曲、兩首鋼琴回旋曲和一部鋼琴協奏曲(另外還有其他許多作品)。十五歲那年,貝多芬還寫了三首鋼琴四重奏(即C大調、降E大調和D大調)。從一八○○至一八○一年,即從三十至三十一歲,貝多芬一口氣竟創作了二十一首杰作。其中包括著名的《第三鋼琴協奏曲》!
他只活了短短的五十七個春秋,卻創作了九首交響曲、五首鋼琴協奏曲、一首小提琴協奏曲、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十七首弦樂四重奏和五首大提琴奏鳴曲等三百多個大大小小的作品(包括從簡單的歌曲到不朽的歌劇)。
用西西弗斯式的語言來說,貝多芬一生反復推運“巨石”上山總共計三百多次。每當一部作品完成,巨石滾下山腳,他又鼓起那超人的意志和壓倒命運的勇氣,操起那永恒的勞役,接著再往山頂上推,創作另一首樂曲。
他的一生所作所為,那一串大大小小的堅決的選擇和果敢的行動,本身就是一部《英雄交響曲》,而且還是一首未完成的英雄交響曲。在他撒手離開人世的時候,留下了一大堆誰也辨認不清的手稿:《第十交響曲》、《b小調交響曲》、《D大調鋼琴協奏曲》和《巴赫序曲》等。
貝多芬所留下的哪里是一堆手稿啊,那分明是留下了無限、發散的追求空間。這在我看來,便是構成幸福人生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是的,幸福的人生應死在無限的希望、追求和眷戀之中。悲哀的死是面向天邊的落日;幸福的死則是朝著冉冉升起的太陽。——在這種意義上,貝多芬是幸福的。這是一種高層次的幸福。它來自煩憂、孤獨、悲憤和搏斗。
西西弗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貝多芬則是人類文化藝術史上的英雄。他們對自己(對人類)命運的哲學內涵都有清醒的意識,并為此感到極度的煩憂和痛苦。然而他們都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戰勝命運的堅強意志面對人生沉重的十字架,正視那嚴峻而冷酷的石塊,不斷地把巨石推上山頂。
當代法國著名文學家加繆在散文《西西弗斯的神話》中表述了這樣一種獨特的見解:對自己(對人類)苦難處境的清醒意識給西西弗斯帶來了痛苦,同時也造就了他的勝利,因為在他的心目中決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藐視并戰勝的。頂頂重要的是,不要對神有任何期待,面對嚴酷的命運要有清醒的意識,要對它表示藐視和對抗——
“征服頂峰的斗爭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應該設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貝多芬又何嘗不是這樣?應該設想,貝多芬也是幸福的。貝多芬不期待什么上帝(盡管他經常呼喚上帝)。面對嚴酷的命運,他深信“天助自助者”。
貝多芬的一生就是用超人的意志來滿足自己,并鼓舞千百萬人,去喚醒他們昏睡的頭腦,點燃起他們內心世界的熊熊之火。他的音樂,就是對荒誕命運的挑戰、報復和抗衡。
在推巨石上山服永恒勞役的過程中,貝多芬仿佛是借用西西弗斯的口吻說出了這樣一句著名的箴言:
“……daβ Musik h
最后,若用愛因斯坦的人生觀來衡量和判斷,那末,貝多芬的一生也是夠幸福的。愛因斯坦認為,一個人的生命只有當它用來使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優美的時候它才有意義。
貝多芬本人也持有這種幸福觀:
“你可不要做那種專為自己而活著的人,你要為他人而活著:
只為自己無幸福可言,要在你的內心世界,在你的藝術中去尋找
更多的幸福……”(F.Zobeley《貝多芬傳》,德文版,第50頁)
今天,由于電子技術高度發達,收錄機普及,地球上有多少人因為可以隨時聽到貝多芬的音樂,才使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充實、更高尚和更優美啊!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貝多芬之魂》并不是一部關于這位作曲家的流水帳式的外在生活傳記。筆者的寫作意圖并不重在貝多芬的生平細節上化濃墨重筆,而僅僅是在一些關鍵性的事實(生平與創作)的基礎上,努力揭示貝多芬的精神進展軌跡,他的心路歷程,他那西西弗斯式的意志、勇氣和人生的崇高使命感,以及他的音樂哲學體系同與之相對應的德國古典文化其他幾條近似于平行的曲線(如康德、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曲線和歌德、席勒的文學所劃出的曲線)的相互關系。試圖揭示這些內在的相互關系,正是本書副標題《德國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貝多芬音樂》的涵義和“主旋律”。
其實,貝多芬一生的內在生活,他的心路歷程所劃出的曲線,本身就是一部宏偉、悲壯的“交響曲”。它也有“主題”,有“副題”,有主題之間的較量、斗爭、否定、變化和發展,還有突如其來的“轉調”,也有對故鄉波恩、青少年時代的如煙往事的再現。
貝多芬的音樂曲線只不過是他的內在生活和心路歷程曲線的回聲、映象和投影。
我們這些現代人的靈魂和內心世界同貝多芬音樂發生共鳴,其實也是兩條曲線的共振和大致上的重疊。或者換言之,貝多芬只不過是用千變萬化的音響在一種廣闊的文化背景上更優美、更深沉地表述了人類整個心胸的起伏和波動。
有兩種傳記:關于一個人外在生活的傳記,關于一個人內在生活的傳記。普朗克和愛因斯坦都寫過有關自己的科學自傳;那是很典型的陳述內在生活的思想傳記。羅素和波普,還有卡爾納普所寫的哲學思想自傳,也是屬于揭示自己內在生活的傳記。
在《科學自傳》中,普朗克開宗明義就指出:
“我決心獻身于我的科學,并且從青年時代起就使我熱衷于它的,正是出于下面這一絕非不說自明的事實:我們的思維規律和我們從外部世界獲得印象的過程的規律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們就有可能通過純思維去洞悉那些規律性。在這個事實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外部世界乃是一種獨立于我們的絕對東西,而去尋找那些適合于這種絕對東西的規律,這在我看來就是科學生涯最美好的使命了。”(M.Planck《科學自傳》,德文版,第7頁)
那末,在貝多芬的心目中,什么是藝術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呢?《貝多芬之魂》這本書也將努力揭示這一點。
凡是筆者在本書中說錯了或說得不夠確切的地方,都將由貝多芬的樂曲一一加以糾正和補充。貝多芬音樂是第一性的原始標準,是最高裁判,是校正一切試圖用普通語言文字對貝多芬及其音樂藝術世界進行界說的“標準米”原件。
普通日常語言文字的終點,恰好是旋律語言的起點。
我想起了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著名的格言: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darübermussman
schweigen.”(凡是不可以言說的,對它就必須保持沉默。)
維特根斯坦是一位單簧管吹奏者,一生酷愛德奧古典音樂,具有非凡的音樂記憶和識譜能力。在他的哲學著作中有許多涉及到理解音樂性質的喻示。
所謂哲學思考,在他看來,就是弄清楚普通語言的界限:究竟什么東西是我們能說的,什么東西是不能(無法)用普通語言加以說清楚的。
貝多芬音樂的功能正在于超越普通語言的界限,打破人類在說普通語言時的沉默。象莫扎特一樣,貝多芬總是習慣在鋼琴的琴鍵上,通過音響和旋律,陳述人類意志本身那驚心動魄的隱蔽的故事,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思想感情,或自言自語,或同別人進行推心置腹的交談。
例如,當貝多芬的好友(著名的女鋼琴家)多羅蒂婭·馮·埃爾特曼失去了最小一個孩子的時候,起初貝多芬并沒有去她府上安慰她。只是后來他才邀請她來他家作客。當她一走進來,貝多芬便坐到鋼琴旁邊,并且對她說:
“現在讓我們通過音響彼此來進行交談吧。”
就這樣,貝多芬連續彈奏了一個多小時。
許多年后,多羅蒂婭·馮·埃爾特曼在回憶中非常激動地把這個故事告訴門德爾松:“他把一切的一切都這樣告訴了我,我最后得到了安慰。”
這無疑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動人心弦的故事。將近三十年,貝多芬的音樂不也是把一切的一切都娓娓動聽地告訴了我,使我得到了許多高于哲學智慧的啟示和甘美的慰藉么?
巴赫、亨德爾、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何以會有這種奇妙的功能呢?從青年時代起,我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今天,我的須發已開始變白,我還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意識到了其中確有一些不能言說的神秘性。我想起了十九世紀英國著名文藝批評家拉斯金(JohnRuskin)的一段話:
“每一部偉大作品的精華部分,總是無法解釋得很清楚的。因為它好,所以它好。”
是的,大自然和人生,科學、藝術和哲學,都有其內在的、不可究詰的神秘性。正是這種神秘性激起了人類歷久不衰的探索熱情。關于這種熱情,愛因斯坦在《廣義引力論》一文中寫道:
“存在著求理解的熱情,正象存在著對音樂的熱情一樣。……要是沒有這種熱情,就不會有數學,也不會有自然科學。”
當然也不會有貝多芬音樂,不會有力求深深地去感受、去理解貝多芬音樂藝術世界的涵義的《貝多芬之魂》這本書。
——哦,演奏不完,聽不完,說不完的貝多芬音樂!
(《貝多芬之魂》,趙鑫珊著,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