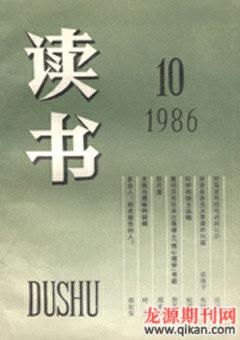新尺度
周介人
一本文學刊物,就是一種精神尺度,因此也是刊物主持人物化了的心理狀態。在一冊生氣勃勃的刊物上,我們處處能感應到編者、作者自由自覺的心靈之光;而當你面對著一本老氣橫秋的雜志時,似乎也就看到了一列舉步
當然,《文學評論》自創辦始,歷來是一本學術性強而有份量的理論刊物。但是,當份量由于過重而壓得讀者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份量也會變成一種滯澀靈智的負擔。因此,依我之見,學術刊物不僅需要有份量,而且需要有氣量。如今的《文學評論》正是如此。自從去年第六期和今年第一期刊載了主編劉再復長篇論文《論文學的主體性》之后,今年第三期即以顯要位置發表各種不同意見。此舉的意義不僅在于證明一般學人可以批評學界領導,那只是說明各自的某種膽量;此舉的實際意義恰恰不在表明膽量而在揚明氣量。所謂氣量,就是論爭各方各自理解、寬容、尊重甚至欣賞對方在美學見解上的各種不同質地的片面性。
片面性的確是具有各種不同的質地的。就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按照馬克思的劃分,人的認識大致經歷三個階段:先是對某個問題形成“一個渾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然后對表象加工,“經過更切近的規定之后”,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于是,“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最后,許多抽象的規定重新綜合,“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參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及導言),但此時的具體已成為豐富的多樣性的統一了。實際上,人在以上三個認識階段上都可能產生片面性,然而這三種片面性的質地是不等值的。當概念的等級停留在整體表象階段時,雖然顯示出“全面包容”的品性,但此刻的“全面包容”是渾沌的、不明不白的、是知其然(表象)而不知其所以然(許多具體規定)的,因而是一種知的不知、知的淺知、知的待知,這時產生的片面性是粗淺的感性的片面性。當思維進入抽象規定階段時,由于整體已被分解為部分,現象的有機聯系被暫時切斷,因此,就突出地產生了思維的角度問題。毫無疑問,此刻的思維角度變得狹窄了。狹窄可能帶來片面,狹窄也可能帶來專注。正是由于狹窄與專注,往往使思維者在理解自己的對象時比以往鉆得更深。在這個階段上產生的片面性,是知性分析的片面性;在片面之中,它常常帶有某種深刻性與啟示性。那么,當抽象再次上升為具體之后,思維所掌握的已經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此時是否還可能產生片面性呢?仍然可能,因為這時思維所掌握的總體是一種思維總體,它仍然是人和理解力的產物。而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因此,人的頭腦所產生的思維總體,比之在人的頭腦之外保持著自己獨立性的實在主體來,仍然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簡化的描述,于是也就無可奈何地伴隨著片面性。但這種片面性恰恰是被人視為理性的片面性,因而是最為切近現象界的片面性,是最高層次的片面性。
在我們的學術史上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出于某種需要,人們便習用感性的片面去批評別人知性的片面(這時使用的武器便是“渾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或者是用知性的片面去責難理性的片面(這時使用的武器便是被斷章取義的語錄)。于是,低級階段的認識反而成為氣度非凡的批判者;而高級階段的認識則被宣判為被批判者。如此倒置,給認識的前進、探索、深化帶來了重重困難。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習慣似乎至今未曾絕跡。然而,今天的《文學評論》之可貴就在于:他們不再以一種片面討伐任何一種片面;在主體性問題上,他們理解并尊重各種不同質地的片面性見解;這就是他們的氣量。這樣的氣量不僅僅出自禮貌,更深刻的是出自理性。因為健康理性告訴人們:這些不同質地的片面性見解正由于是不等值的,所以它們在同一個認識系統中的功能也是相互不可替代的;健康理性還告訴人們:在美學見解方面,比一般的社會科學理論更需要尊重偏見,不管這種偏見是源自感性,還是源自知性,或者源自理性,只要它有鑒賞力、智力、才力的支持,它總會或遲或早結出果實;健康理性還告訴人們:思維的進展常常遭遇到概念的貧困問題,此時就不得不借助舊概念或者其它學科的概念來表達新的意義,此時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語義學方面的相互詰難,只有通過這樣的詰難,才能廓清概念,完善思維,促進理論研究的發展。
除了文學主體性問題的提出與討論,《文學評論》在最近一年的另一個重要革新措施是:開辟專欄,廣泛約請作家、評論家(其中大部分是年輕的作家與評論家)撰寫“我的文學觀”。其實,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雖然未列入該專欄,卻是一篇最有份量、并且名副其實的“我的文學觀”。長期以來,我國文學界不僅對創作主體未曾作過深入的探討,而且更不重視文學理論的主體性問題。事實告訴我們:是文學理論家創造了文學理論,而決不是從先在的許多文學理論中自然而然地分泌出文學理論家。既然是文學理論家創造了文學理論,那么就應該容許并且鼓勵各個個性不同的研究者,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充分調動自身的本質力量,包括他們各各不同的實踐經驗、傳統理論的素養、思考方式、思維技巧、氣質、想象力,來構筑具有自己風格特色的文學理論模型。劉再復關于主體性的長文之所以引起熱烈反響,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他充分調動了自己對于文學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構筑了一個打著劉再復鮮明的性格印記的文學理論模型。這個模型有著強烈的現實感(因為他構筑這個模型的目的是明確地針對現實的),然而歷史感尚嫌不足(如回避康德、黑格爾、存在主義關于主體性的論述;對“文學是人學”的歷史評價也不盡恰當),這樣的缺陷恐怕同劉再復不僅是理論家,而且是具有理論氣質的詩人有關。因此,別人盡可以不同意他的理論模型而從另一個角度、另一種線索、另一些特征出發來構筑自己所喜愛的理論模型。但我相信,文學現象如此源遠流長、豐富復雜、變動不居,哪怕是比提出主體性問題更全面的理論家,他所構筑的模型對于文學原生系統結構而言,也仍然是一個側面;而且往往是愈擺出“全面”架式,既強調這一面,又強調那一面,最后用大概念煮大鍋飯的模型,愈顯得大而無當。基于此,我就十分贊賞“我的文學觀”這樣的專欄,通過這個專欄,每個具有個性差異的作家、理論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體驗、理解、需要、愛好來構筑或多或少被主體簡化了的文學理論模型,這些模型在微觀上可能相互排斥(因為文學現象本身具有相互排斥性),但在宏觀上卻又相互補充,相互映照,其總和就可能構成對文學系統原型的一個相對正確的認識。
可能有些青年讀者會對“我的文學觀”專欄中的某些文章感到不夠滿足或者不夠過癮,因為他們總是希望理論家們不斷推出新的文學觀點,不斷作出新的理論結論。我十分理解他們的這種熱切期待,但這種期待中卻包含著對理論的某種誤解。現代化高效率的生活方式常常使今天的青年人重視結果而忽視過程,這樣一種心理特點也影響到他們對理論的態度中來。他們讀一篇文章希望一下子就抓到一個新的結論。殊不知所謂理論的進展不僅僅是觀點的進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論證方式和論述結構的進展。觀點是一種“硬知識”,而滲透、貫串、蘊含、流動于硬知識之中的思想脈絡、邏輯結構、網絡聯系、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種種啟示,則是“軟知識”。如果只知道抓“硬知識”,而不知道同時發現“軟知識”,那么被你抓到手的“硬知識”就會變成一堆“死知識”。只有既重視“硬知識”,同時更重視支撐這些“硬知識”的“軟知識”,那么被你學到手的理論才能活躍飛騰起來。
從這樣的尺度來看魯樞元、孫紹振、劉心武、南帆、李慶西、莫言等同志發表在“我的文學觀”中的文章與見解,我還是忍不住要拍手稱好。魯樞元的“從心理學眼光看文學”,孫紹振的從生活、自我、形式“三維結構”看文學,劉心武的從“文學本性”看文學,李慶西的從“二元對立”看文學,莫言的從“心靈情感經歷”看文學……一下子沖破了多年來我國文壇只從幾本教科書來看文學的沉悶空氣。或許他們在這里發表的一些文學觀點已經在他們自己的其他文章或別人的其他文章中出現過,或許他們的觀點還不夠成熟,甚至偏頗而有可商榷之處,但這一點并不見得象原來想象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各自以極不相同的思路,極不相同的結構,極不相同的方式,極不相同的語言又一次論證了這些極富個性化的文學觀點,維護了理論主體的創造性本質。在理論建設方面,有些同志誤以為只要用“新磚”(新材料),就一定能創造出新房子,于是他們整天為尋覓“新磚”而奔忙。而只要這些同志尚未意識到自己頭腦中的“軟件”必須首先更新,那么,很可能他老是找不到“新磚”,或者他即使拿著“新磚”,造出來的也依然是“舊房子”。“我的文學觀”中的大部分文章卻證明:即使在舊材料中,也可能蘊藏著新的理論內容,因此,只要理論家的眼光改變,構想改變,不管用的是“舊磚”還是“新磚”,都能創造出富有特色的“新房子”。由此看來,“我的文學觀”要奉獻給讀者的不僅僅是觀點,還有賦予這些觀點以活力的思維脈絡。作為一個讀者,完全可以對其中很不相同的思維脈絡進行自己的選擇,或者認同,或者拒絕。而一旦你真正領悟了別人的思維脈絡,那么,即使他交給你的只是一朵尚未充分開展的蓓蕾,你也能夠在自己的心靈中繼續澆注而使之變成美麗的鮮花。
如果我們注意到:一九八五年被文學理論界稱為“方法年”,而恰恰在“方法熱”中,《文學評論》卻熱衷于談論文學觀念,那就能更深一層發現這家雜志的眼光。
長期以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們的文學研究確實存在著視角單向、方法劃一、眼界狹窄的弊端。正因為如此,當一批中青年的研究工作者引進自然科學方法論和西方文壇的批評方法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時,劉再復同志曾著文熱情肯定,認為這是“開拓思維空間”的大好事。于是,“方法論”的熱潮滾滾而來。但是,當這股熱潮到達沸點時,《文學評論》依舊保持著成熟的冷靜。南帆于一九八五年第四期《文學評論》上著文指出: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活躍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文學批評的活躍。但是,假如批評家的所作所為僅僅在于急功近利地襲用一批新名詞,忙不迭地宣告新的研究方法名稱,勇氣十足地以新的獨尊一家反對舊的獨尊一家,那么,這往往還僅僅是一種幼稚的活躍。”
這不僅是南帆個人的憂慮,也是當時一批參與新方法的比較嚴肅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共同的見解。《文學評論》敏捷地選擇并認同了這樣的見解。就在發表南帆文章的同一期,“我的文學觀”專欄開始出臺。這表現,刊物的主持者們已經清醒地看到了觀念與方法的聯系,他們要把新方法置于文學新觀念的推導與制約之下。這一部署,不僅使那些“無觀念”的“新方法”相形見絀,而且也使某些“舊觀念”的“新方法”窘相畢露了。
新觀念新方法的提倡,給《文學評論》的創作研究園地帶來了一片青蔥。《文學評論》的評論對象歷來是一些有定評的作家,但這種不成文的規矩也在最近一年被突破:李
人在實踐中創造了現實,現實愈是具有普遍性,人就愈是受到現實普遍性的制約。但是,人的感性力量與理性力量總是不會滿足于這既存的現實普遍性,無時無刻不在尋找、選擇、設計、試探某種改革的可能性,以突破既存普遍性的限制。于是,人類就有了代代相繼、生生不息的物質創造與精神創造,歷史才會前進。我們的學術刊物,義不容辭的應該是人的創造性實踐的推動者。令人遺憾的是,恰恰是某些學術類刊物,卻引起了讀者的厭煩。這是為什么?依我之見,恐怕是同某些刊物拘泥于現實性尺度而沒有放眼于可能性尺度有關。這樣的刊物往往固執地認為,只有普遍性的東西才是有份量的、可靠的、因而具有最大安全系數的。他們對暫時還不具有普遍性的新鮮的思想、思路、思維空間,統統投去懷疑的一瞥,然后匆匆擦肩而過。于是,厭煩情緒就首先在精神要求比較高的讀者層中產生了。正如一位大作家所說:厭煩就是“由未被利用的力量引起的痛苦,是被埋沒了的可能性和才華造成的痛苦”。
這一年來,《文學評論》卻真正顯現出與眾不同的眼光。它真正聽到了現實中那些未被重視的文學智慧、未被調動的文學可能性的呼喚。于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尺度:既不脫離現實性,又不從屬于現實普遍性的尺度;這個尺度,就是現實可能性尺度。按照這一尺度,某些具有現實可能性的知識,不一定就沒有份量;而某些具有現實普遍性的知識,不一定真正具有份量。這是因為,一切知識在其形成的初始階段,都帶有猜想的性質,都是由個別到普遍的一種推斷,因此,它僅僅是作為可能性而存在的。但是,人就是憑著可能性知識的積累、升華而逐步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所以,可能性總是高于現實性。然而,可能性知識的力量一旦在普遍性實踐中發揮出來,就逐步轉化為普遍的現實性,就成為一種常識,它就會顯示出凝固性,顯示出自己在時間與空間方面的局限。于是,就需要人不斷地在現實中重新尋找、選擇、設計、超越普遍性局限的新的現實可能性。而學術刊物,決不僅僅是收藏普遍性常識的木板箱,它應該是推動這種尋找、選擇、設計、超越的一種主體性力量。
我以為,這就是一年來《文學評論》的新尺度,這個新尺度中,包含著一本具有現代意識的學術刊物的新的份量觀與新的氣量觀。
這個新尺度,將使《文學評論》不僅能夠提高評論,提高文學,而且能夠提高人,提高人把握世界的能力,提高人的智慧與品格。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