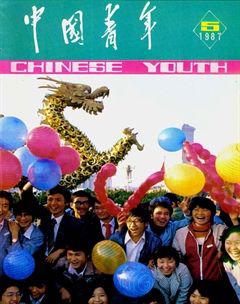一個沒有文憑的男子漢
方正
在中國科學院這個最高科研機構里,沒有文憑的科研人員幾乎已經絕跡。按人們的說法:就連“工農兵學員”也呆不住,要么“回爐”考研究生,摘掉“帽子”,要么自動調離,以免“受擠”。而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里,有一個高中生從1974年一直奮斗到現在,腳跟站得很穩。他不是沒有機會,“文憑”曾幾次敲響了他的大門,卻又在唾手可得之際溜過他的身旁。這對有些人來說足以遺憾一輩子,但他卻很快擺脫了困擾,只牢牢記住:人要有真才實學。
他叫溫遠影,“文革”中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干了6年,1974年“困退”回京進了植物研究所。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制度,溫遠影也報了名。說起來動機很簡單,他想借此檢驗一下自己的水平。他只填了兩個志愿:北大化學系、北師大生物系。要上就上個好的。當時他工作很忙,只復習了十來天就進了考場。考了4門,門門提前交卷,成績出來了,是西城區前10名:數學110分,理化100分,語文93分,政治差一點,71分。不過這不代表他的思想水平,初中,他是班里第一個團員,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高中畢業前就要被發展入黨了。
但這兩所全國著名的大學都沒有錄取他。問題出在眼睛上。上小學時,他用彈弓打人家已點燃的“二踢腳”,結果崩壞了一只眼睛,校正視力還不到0.01。聞名遐爾的清華大學卻“慕名而來”,通知他去談談。可當他得知畢業后不能回到他熱愛的工作崗位時,便婉言謝絕了校方的盛情。在他看來,干自己喜歡的工作比名牌大學的文憑更重要。
人逢盛世,機會又一次敲響了他的門。高校擴大招生范圍,試行“走讀”。這次是師大化學系寄給他正式錄取通知。但他決定不上大學了,他迷上了植物所的工作,哪兒都不想去了。這個行動可是有點個性,需要相當的勇氣,而勇氣來自自信。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從未對自己的這個決定后悔過。他不喜歡“悲悲戚戚”,也沒有胡思亂想的習慣。歸根到底,他還是相信自己的實力。不過,那時他確實還不知道“文憑”的厲害。他只是想,來日方長……
1978年春,他所在的植物所招收研究生,名額只有一個。此時,溫遠影已自學了大學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還初步掌握了英語(他上中學是學俄語,成績在全年級數一數二)。每天早上按照他的老習慣,6點半鐘第一個到所里,打一套形意拳,然后一頭扎入知識的海洋,注意力絕對集中。他相信,他有能力直接考取研究生。
他以總分第一名列榜首。但是命運乖舛,幸運之神繞過了他,將桂冠套在了第二名的脖頸上。可他總分要高于第二名12分呀!答案終于有了,四門考分中的三門都高于第二名,偏偏生物化學比第二名少了2分。當然這不是關鍵,關鍵在于第二名是個本科畢業生,是個畢業后就執教于中山大學的助教。人家是科班出身,受過基本訓練,功底扎實。而你呢?你的真才實學人家總是看不大清楚,因為上面蒙有一層世俗的面紗。
溫遠影沒有怨天尤人,他只是明白了,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并非一件易事。這里人才薈萃,幾乎個個都有文憑。同時他也明白了,自己是個過河的卒子,已無退路可走。他更加發憤苦讀。隨著孩子出生后的拖累,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也有頭疼的感覺了。但他絲毫沒有退縮。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每天練習英語聽力長達8小時,錄音機的耳機總是戴在他的頭上。他還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能用英語看所有的業務書。業務書全是英文的,含糊不得。
1982年底,中國科學院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聯合舉辦的英語培訓中心第二期開始招生。完成了這里的學業,科學院系統的工作人員出國可免試外語。
入學考試的內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看卷面上的中文讀出英語來;再掉過來,看卷面上的英文,用漢語讀出。第二部分是聽錄音,一個題同時有幾個答案,讓你選擇哪個答案正確。
溫遠影一炮中的,以全所入學考試第一名的殊榮,在這個外語培訓中心學習了7個月,學習期間成績也名列前茅。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他不是弱者,雖然他沒有“金字招牌”—文憑。
1984年10月,所里派他赴日本學習一年。對此議論頗多:哎喲,沒有文憑的還能出國呀!我們有文憑的還沒輪上呢!出國前又出現了一個小插曲:他們雖然通過了外語培訓中心的學習,但還是要再通過“EPT”,理由是外語培訓中心的結業早了點。考試160分是滿分,110分便能通過。溫遠影考了119分,他走定了,他沒靠“后門”,憑的是真本事,他問心無愧。
在東京明治藥科大學的藥品化學研究室里,負責帶他的梶原正宏教授冷淡地扔給他兩本英文版的書《有機化合物波譜分析》和《有機化學》:“先看看,一個月后再說吧。”這就是師生頭一次見面的情景。梶原教授不理解眼前這位“溫桑”怎么連個大學又憑都沒有。也難怪,在日本沒有這種情況。在相當于中國科學院的機構里,科技人員起碼是個“正牌”大學生。
第一本書是100道考試習題,第二本是美英大學生的課本。一個星期后,溫遠影將這兩本書還給了教授,“完了?”梶原有些疑惑地翻看第一本書,100道題的答案無一錯誤;教授又隨意指著第二本書的幾個段落讓他講講,看他懂了沒有。他用英文熟練地作了正確回答。“哦,不簡單。”教授認可這位有些土氣的學生了。后來他向他的日本學生鄭重宣布:“溫桑是我的好朋友,我完全信賴他。我不在時,他就可以代行我的職責。”
在日本一年,溫遠影最多休息了7天。機會得之不易,他只能拼命干。了解他的人對他早有定論:目不斜視,只干自己事業范圍內的事。活動的“軌跡”是“兩點一線”—家里到所里。“砍大山”、“搗騰外快”等等,對他來說無異于“天方夜譚”。
一年里,他不但完成了梶原的題目,還有所發展。要結業了,梶原拍著他的肩膀說:“跟我再干二三年吧,到時,我準能幫你弄個博士學位!”梶原教授從這個沒有文憑的“溫桑”身上,認識了真正的中國人:正直、勤奮、進取、頑強。正在這時,植物所的所長率代表團出訪日本,也來到了東京。他見到溫遠影的第一句話就是:“所里快要評職稱了,每個人都要通過報告,你快回去好好準備準備。”
溫遠影就要啟程回國了。梶原教授動情地說:“我給你爭取到了兩年10萬元的學習經費,馬上再來吧。”回到祖國,他將有10萬元學習經費的情況匯報給了領導,他愿意把這個名額讓給別人。
職稱的評定用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溫遠影的臉消瘦了,下頦尖了。別人是研究生才能評上助研,他沒有文憑也評上了,自然會有人不服氣。從精神歷程上說,他的確是掉了一層皮。不過他還是原來的他:樂觀、堅毅、執著。他風趣地給我講了一個小故事:他們室里要出一個人參加講師團。本來擬定的人選是新從四川大學分配來的畢業生小王,小王業務剛進入情況,離開一年,不免有些猶豫。溫遠影說:“要不,我替你去吧。”上級領導按精神辦事,沒有批準:“不行,沒有文憑,不能去,大專畢業生才符合條件。”這在有些人看來是“因禍得福”,可其實對他有意無意還是一種否定。看來,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文憑”仍要在他生活中扮演一個角色。不過他不怕,他還是相信那句話:人要有真才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