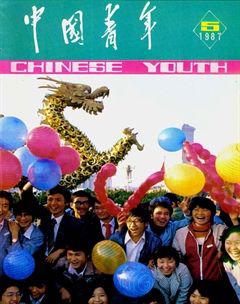第二次誕生(小說)
20年前一個涼爽的夏夜,她誕生了。四壁,白雪般的顏色。媽媽躺著,大汗淋漓,呻吟著。突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曾有過的“哇呀……”一聲,終止了媽媽的呻吟,她慘白的臉上露出如釋重負的驚喜和甜笑。經歷了那么長久,那么劇烈的痛苦,盼來了這赤條條的小生命。這個小生命將起名秋爽。她躺在媽媽胸懷里吮吸著乳汁。她看見世界一片潔白。
20年的風雨過去,她長大了……
一
一生產科的兩間屋子門對門,南邊的大,有9人辦公;北邊的小,是秋爽一個人的天地。
她每天上班都先到大屋打個卯。今天屋里只有頭發灰白的張師傅和與自己同齡的陳曉菲。
“怎么了?”望著她氣喘吁吁的樣子,陳曉菲吃驚地問。
“擠不上車,走了兩站地,遲到了!”秋爽說。
“讓門口值班的記下來了?”曉菲猜得真準,“你真是個傻瓜!估摸要遲到了,干脆回家;呆到九十點鐘再來。碰上值班的,就說去開會或去看病,不就得了嗎?”
一旁的張師傅正在全神貫注地查閱報表。她年過半百,頭發花白,仍然做著統計員的工作。每天上班鈴聲一響,準時辦公,這是她的習慣;曉菲也是統計員,也有她的習慣:
“秋爽,你這身衣服有點靠色。”她說,“藍褲、藍褂的多呆!你比我還小3個月呢,干嘛不穿得艷一點?”
秋爽笑笑沒有回答,不由得掃了一眼曉菲。是呀,她高跟船形黑皮鞋,肉色絲襪,淺藍彈力牛仔褲,黑底大紅方格茄克衫,頭發用不銹鋼卡盤起時髦樣式,劉海卷得很俏。眉毛修剪過了,眼里閃著流盼的光,確有一種嫵媚感。
“今天怎么這樣清閑呀?”秋爽轉移了話題。
“副科長到公司開會,游子興上午有課……”曉菲有問必答,掰著手指一一數說著。那股熱情勁使秋爽想起兩周前剛來廠時,她領自己換飯票,領工作服,參觀車間的情景。掰到第7個手指,曉菲說:“張師傅,科長4號走的吧?”見張師傅不答,便自語道:“都兩個星期了,也該回來了!”
科長阮宇出差,至今還未見過面呢!秋爽想。
回到北屋,她坐在辦公桌前望著窗外,外面除廠院的磚墻,便是一方天空。小屋僅是大屋的1/3,剛夠放6個資料柜。曉菲不愿和“背手將軍”(曉菲給退居二線的老科長起的綽號)對面坐,曾動員秋爽搬到大屋去。
“這兒安靜,我喜歡。秋爽謝絕了她的好意。
午飯后,大屋敲開了“三家”,秋爽便從抽屜里翻出日記本。記日記是她從小養成的習慣,即使考試復習階段也未停止過。那是她的精神寄托,有她從未向第二人訴說的秘密。
“怎么不去玩牌?”游子興不知什么時候進來了,“記日記哪?當初我也一本接一本地寫,有什么用?”
秋爽收起日記,問:“你上課去了?”
“嗯。當初有記日記的時間多讀點書,也不至于現在還為大專奔命!你知道,當廠長還要有大專以上的文憑呢!”
“那你想當廠長了?”
“夢想過。雖說我初中沒畢業就當了兵,可讓我去車間,我還不干呢!”
“你當的準是‘后門兵!”
“那還不都是我家老頭子的主意!他還說為我好,結果除了拿張黨票,什么也沒得到!”
秋爽從心底里厭惡“后門兵”,他們當時不就是為逃避插隊嗎?眼下知識分子吃香了,又后悔了!秋爽想著未說出口,只是用筆不住地敲桌子,以示自己的怨愾之情。
“聽說你是沒考上大學上了中專?那可夠虧的!”游子興繼續聒噪。
提起高考,秋爽心中隱隱作痛。當時離錄取線只差7分,可是父母的臉色、社會的議論足以使她透不過氣來!
秋爽再不想聊下去了,她站起身說:“你中午不休息休息?”
游子興知趣地走了。
辦公室的人向來對下班鈴最敏感,只要鈴一響,抬屁股就走。可秋爽還不具備這種“條件反射”,況縣城家里并沒有什么樂趣。直到暮色臨近窗戶,她還坐在辦公室出神地望著窗外。
誰?門虛掩著還敲。“進來!”秋爽道。
“怎么還不開燈?”
來人順手拉開了燈,耀眼的燈光下,秋爽好半天才恢復視力。來人二十六七歲,寬肩、厚胸、高個子;面帶倦容,眼睛卻炯炯有神。棱角分明的面龐,有一種堅毅的氣質。
“你是新來的?”他把右肩的大旅行包放下問。看到秋爽點點頭,便說:“剛下火車,想把東西放對過兒,可鑰匙不在。幸好這屋開著。”
秋爽笑了。她知道眼前這青年準是阮宇。
“怎么還不回家?”
“我走了,您怎么進來呢?”在他面前,秋爽說話總想輕松、幽默一些。
“你喜歡設備檔案管理員的工作嗎?”
“剛來,還說不好。”秋爽注視著他,在等待他新的問話。
“這工作可是年輕女同志求之不得的,你要珍惜呀。”阮宇站到桌前,象是等著她表態。
“既然別人求之不得,我怎能不珍惜!”秋爽心頭突然涌起一絲不快,狠狠地把額前發向后一掠,答道。
阮宇在房間走動起來:“我是說,這工作不是隨便都能干好的,你是中專生,在咱們廠算是大知識分子了。設備檔案工作需要動腦子,要干好,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他見秋爽托著頭認真聽的樣子,便換了語氣說:“我不是在訓話,干嘛那么洗耳恭聽?”
“那你要我怎樣?”
“我叫你……”他沉吟了一下,“快回家!時間不早啦!”
二
第二天一早。
“哎喲,我的大科長,什么時侯回來的?可讓我想死啦!”曉菲一見阮宇就驚叫著。看著曉菲快活的樣子,秋爽在一旁直皺眉。
“這月生產任務完成得怎樣?”阮宇轉向張師傅問道。
“一車間,3100;二車間,2800。”曉菲伸手從張師傅的辦公桌上拿過報表搶先答道。其實秋爽清楚,曉菲只負責二車間報表,而實際上兩張報表都是張師傅一人的筆跡。
“二車間的碎修工時還有多少?”曉菲沒想到阮宇問這個數字,卡殼了。
“5小時。”張師傅立即說,“阮宇,你可得說說二車間,任務完不成,耗電倒超了。”
阮宇馬上撥電話:“喂,二車間嗎?找你們主任。不在?那找副主任!你就是?生產任務完不成了,你知不知道?通知各班長,下班后開會。上班開?為什么?有電影?生產上不去,你看電影心里踏實嗎?”
曉菲沒看出阮宇生氣的樣子,指著玻璃板對他說:“你的電影票,我還給你留著呢!”
“先放在你那兒吧!”
“你不看啦?”曉菲嬌嗔地說。
“恐怕去不了。”阮宇抱歉似地答道。
秋爽悄悄退了出去。
三
“看人家秋爽多老實!”一次曉菲跟游子興打逗,游子興冒了一句。這話真靈,曉菲當即停手,訕訕地說:“誰叫你惹我生氣!”
對科里,秋爽并非漠然置之;她更習慣用眼睛去發現,去觀察。
早晨,張師傅總是第一個來,掃地,擦桌子;除廠里規定的大掃除,屋里的活她全包了,卻從未表白過自己。日久天長,都認為她是理所當然的了。
曉菲呢?每天都上班,可常常是早晨打個照面就走,快下班了才回來。若科長問,張師傅就說:“剛出去。”實際是干私事,還是找人“砍大山”,誰知道?她出門前,先打聽科長的去向,若科長外出了,她膽子就大多了。科里都睜只眼閉只眼,不過心里誰都明白。
這天,秋爽忍不住想讓張師傅勸勸曉菲,就搬過椅子到張師傅身邊。
“張師傅,您別把秋爽的耳朵咬掉了!”曉菲突然出現在門口,惡聲惡語地說,那話象從牙縫里擠出來的。
“游子興,”曉菲見沒人理睬,極不甘心,便轉臉看看掛在窗口的小黑板,上寫著“明天上午8點科里全體同志開會”,問道:“什么會?”
“好戲。”游子興帶搭不理地說。
“你別賣關子,到底什么會?”曉菲伸出拳頭問。
“評選先進。”游子興只好說。
四
風拍打著門窗,天降下了夜幕。
阮宇推門而進,順手拉開了燈。見秋爽仍坐在桌前望著窗外,不耐煩地瞥了他一眼之后,又恢復了那塑像般的姿勢。“上午評選先進的會沒開完,你就出去了,去哪兒了?”他問。
“去廁所了。”她依然望著窗外。
“可你一直沒回到會場上來!”見秋爽側著頭不理,他的聲調降下來說,“你對上午的會有意見可以提嘛!”
“我提什么?先進不先進與我有什么關系?統計只一個名額,不是張師傅就是曉菲。曉菲怎么樣?她認真坐下來工作過嗎?你不知道還是裝傻?”
“其實,我比你更了解曉菲。”阮宇說,“在車間,我和她一個班。”
“還有一段‘羅曼史。”秋爽用鼻子哼了一聲。
秋爽曾見過曉菲抽屜里有張照片—阮宇、曉菲都穿著游泳衣,一個站船頭,一個站船尾,相視而笑。
“你知道了?”阮宇驚奇地說,“那時我才22歲。”
“你跟我解釋這個干嘛?”秋爽“撲哧”笑出了聲。
阮宇焦躁地在屋里走動起來:“今天會上的事,你一定會說我窩囊。我說上兩句,也不至于把張師傅給否了。可是從老科長分的范圍你看不出來嗎?不選張師傅,她老實巴交也不會爭辯,不選曉菲怎么得了?老科長出面干涉,我能不尊重他的意見?”
“他提拔了你,就要拍他的馬屁吧?”
“什么話!當科長之前,我怎么知道要提拔我?是誰提拔我?”
“可你提了職,就想著怎樣感恩,怎樣保住自己的職位,是不是?”
“你說得太刻薄!”
“怎樣?給我穿小鞋,我可不怕。”
阮宇呆呆地看了秋爽一會,慢慢地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望著窗外的黑暗,搖搖頭,說:“你把我看成什么樣的人了……受累、挨罵,每走一步,都有許多條條框框限制你,前后左右,有許多你不得不去照顧的關系,有看得見的,也有看不見的。苦點,累點,我不在乎,苦惱的是,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說著,他雙手交叉在腦后,仰靠在椅背上。
秋爽慢慢地轉過頭,大膽地注視了他一會兒,輕輕地說:“你的胡子該刮了。”
五
過了幾天,阮宇進門來,裝作不經意的樣子問:“這屋子亮堂多了吧?”
“可能。大概是今天天氣好。”阮宇找把椅子在秋爽對面坐下,鄭重地笑著說:“今年先進工作者已經有張師傅了!”
“謝謝你!”
“你又在嘲笑我?”
“不,是真心!”秋爽誠懇地說,“我該向你匯報工作了。你就那么放心?我不說,你也不問!”
“年底,光忙著抓車間生產了,”阮宇說,“不過今天沒什么事,你說吧!”
“我有個設想,”秋爽頓了頓說,“我想把廠的設備資料重新整理一下。現在的分類編號體系很亂,查找起來,管理起來都很困難。”說著她展開自畫的一張圖。
那是一張“設備管理結構圖”。阮宇走到秋爽身邊俯身去看。秋爽感到他的下巴就要碰到自己的頭發了,一股男子身上特有的烈火般的氣息向她襲來。
“好啊,原來你在這兒!”門哐地一聲被重重地推開,曉菲委屈地說,“剛才有你的電話,他們說你在車間,讓我白跑了一趟!”
“誰來的?”
“公司來的,找不到你,就給掛了。”
阮宇點點頭,又俯身看圖,曉菲聽不清也看不見到底什么東西吸引了他們倆。便重重地帶上門,旋又折回,在門口探頭道:“阮宇,我找你有事!”
阮宇隨曉菲進了大屋問:“什么事?”
“你不看看這月的報表嗎?”
“什么時間不能看?下午再說吧!”阮宇慍怒地出去了。
曉菲十分吃驚。叫他過來,不管怎樣,也得跟自己說會兒話,不就把秋爽曬了?可現在多尷尬!她越想越窩火,把報表使勁摔在桌上。
“你怎么了?”張師傅驚訝地問。
“沒怎么!”她帶著哭腔,想把一肚子火都撒給張師傅。
六
第二年秋天,辦公室出了件露臉的事:游子興考上了大專。
這事兒,秋爽早就知道了來龍去脈。在報名前,公司只給廠里一名額:全脫產半年復習,今年6月考試,學習兩年拿到大專文憑。這樣的名額,竟在科長不知道的情況下,叫游子興直接找廠長爭取到手了。那次游子興了為托秋爽給他幫忙辦事,透露了這項秘密,還透露了曉菲仗著爸爸是公司經理,前年從車間提到生產科,連科長都發怵她三分等等“內部參考消息”。
今天他終于考上了。他揮著通知書宣布:“晚上請諸位到我家赴宴!”并走到阮宇面前,拍著他的肩膀,十分真誠地說:“阮宇,一定去啊。我先走一步,去準備準備。”
吃飯就座時,曉菲坐在阮宇右側,秋爽在對面。曉菲搶先斟酒。給阮宇、游子興各倒一杯,又給自己倒了一杯,然后按逆時針方向為其他人也倒上了酒,唯獨漏過了秋爽的酒杯。
秋爽心里自然明白,從張師傅評上先進,她倆沒說上10句話。背后誰也不議論誰,可兩人的對抗在無聲地進行著。
阮宇碰了曉菲,示意秋爽的杯里沒倒上酒。見曉菲說聲“忘了”,卻沒任何動作。秋爽呢,光和大家說話,根本不看酒杯。阮宇便說:“子興,我不喝這酒,給來點白酒。”說著把杯子遞到秋爽跟前。秋爽先看了阮宇一眼,才挾住杯子點點頭。這一眼實在夠分量,得讓曉菲難受半天。
“我提議為子興考上大專干杯!”阮宇端起酒杯。
舉杯。碰杯。
游子興喝酒上臉,一杯下肚便紅光滿面,連喝3杯后,話就多了起來:“考上大專,對別人來說沒有什么,對我可是不易呀,我底子薄,考了3次才考上。這兩年,我一門心思考學,工作能拖就拖。能不干就不干,工人們罵我,科里人對我有看法,我都知道。有時我也想:為這張文憑值得嗎?拿到文憑究竟有多大用?現在上學是好事也是壞事,聽說很快要搞工資改革,我這一去兩年,好事是輪不到了,到底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還是撿了西瓜丟了芝麻?”
秋爽和阮宇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他們會心地笑了。
游子興又喝了一杯酒,接著說:“阮宇,過去你我之間的不愉快,咱統統忘掉,今天打開窗子說亮話,我佩服你。我他媽算什么?工廠的希望還是在你這種人身上。”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阮宇趕緊舉起酒杯:“喝酒,干!”散席時快深夜了。
阮宇騎車上了秋爽回家的路。他多少有點繞遠,可跟別人分手時卻說,說:“嗐,差不多遠。”
沒有行人;偶而有自行車飛過。他倆的車并排,路燈擎在頭頂,為他們披上金色的紗;夜空幽谷般敞開了柔情的胸懷。
“剛才你生氣了吧?”
“值得嗎?”
“那就好。”
“阮宇,別人都千方百計搞張文憑,難道你就不想?”等倆人都輕捏了一下閘,她接著說,“雖說不該單純追求文憑,可是沒有文憑今后吃得開嗎?”
“那你的意見?”
“你工作忙可以上半脫產的嘛!”
“我上的是不脫產的!”
“我說正經的呢!”
“我沒騙你。我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已經通過了13門!”
“是嗎?我怎沒看你學習過?”秋爽一驚,車把一歪,差點與阮宇撞車。他倆咯咯地笑了。
“科長帶頭到辦公室學,咱們科還不成教室了。你呢,八小時以外干什么?”
“吃飯,睡覺,”秋爽故意停一停說,“外加學習。”
“明年局里開設半脫產電大班,你考考吧。”
“我不想。”
“滿足于中專畢業?”
“你的家過了吧?”
“早過了。沒關系,我送送你。”阮宇接著說,“以后大專生一多,中專生就不起眼了。”
其實現在中專生就讓人瞧不起。前些時,秋爽父親的同事要給她介紹男朋友,那人一聽她是中專畢業,竟說:“中專生我這兒可以用簸箕撮。”這大大地刺傷了秋爽的心!
“我考別的,你批準嗎?”秋爽問。
“看什么學校。”
“今年的高考。”“那怎么行?還有一個月就考試了。”阮宇有些不快,“本科文憑比大專體面,是嗎?”
“你不允許也沒用,我可以辭職。”
“我不明白。”
“理由,以后會告訴你。”秋爽不溫不火地說,“但是有一點我現在就該讓你知道:我可不愿呆在生產科!”
“就為曉菲?”
“你看不出來?”
“我叫她回車間。”
“怕你做不到,她有后臺。”
“那就試試吧。我有充分的理由!”秋爽笑著搖搖頭,指了指前方的樓群說:“我到家了。”
兩人下了車,扶車把面對面站著。
“你那笑真叫人琢磨不透。”阮宇的眼睛閃著激動的光。
“我不笑就是了。”她的回答柔和而平靜。
“什么時候我能看到你的心?”他憂郁地說。
七
8月12日,秋爽來得比張師傅還早。還是坐在桌前看著窗外。外面比剛來時多了兩棵小楊樹。那是開春廠里搞綠化剩下的,她從用它打逗的兩個小伙子那里要來栽到樓后。它雖頑強地活到現在,可秋風一來仍然有片葉子飄落,圍樹干繞了兩圈伏在樹根上。
這小屋,這燈光,環境,書柜,卡片,書籍,圖紙……她太熟悉了。而自己就要離開了,一股感傷的情緒涌上來。
“你怎么來得這么早?”她呆呆地看看來者幾秒鐘,才問道。
“我向你祝賀!”那是阮宇的聲音。
祝賀什么,是無須解釋的。當她拿到準考證時,他竭力阻止她,以至發火,可最終說:“你去吧,考試時,別想其他的事!”
“我可以不走,”秋爽沒敢抬眼睛,怕他看到自己的眼淚,“如果你反對。”
“為什么反對?”阮宇望著她,“只是你能告訴我,當初決定參加今年高考的理由嗎?”
秋爽從抽屜里拿出日記本,遞給阮宇說:“全在這上面。看完了留你那里也可以,還我也可以。”
阮宇打開日記本。哦,秋爽,這本是屬于你自己的領地,是讓我栽種秧苗,還是讓我分享果實?
“什么時候我能看到你的心?”阮宇真想問問她。她卻低垂著眼簾看著日記本。他明白了,這顆心就捧在自己的手上。
作者簡介馮榮華,女,1962年生中專畢業,現在北京市某公司黨委宣傳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