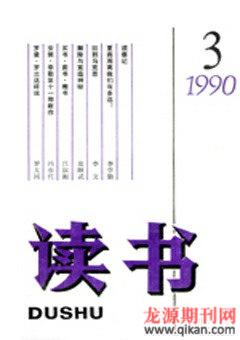羅曼·羅蘭這樣說
羅大岡
從五十年代最后兩年開始,直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由于工作需要,我閱讀了羅曼·羅蘭的文學作品以及書信、日記等材料,隨手摘錄了若干精辟的文句,對于我自己立身處世,修養品性人格,很有幫助,至于寫文章時作為參考,尚在其次。何況現在我已屆耄耋之年,限于時間與精力,今后寫大部著作的可能性已不存在,至多憑手頭占有的一點材料和讀書時想到的一得之見,寫幾篇短文,聊供讀者參考而已。
下面是羅曼·羅蘭的箴言摘錄,以及我的膚淺體會。
(一)“倘若人活著不是為了糾正自己的錯誤,克服自己的成見,擴大自己的思想和胸懷,那么活著有什么意義呢?”(見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中譯本第二冊)
人生于世,犯錯誤常常難免。錯而不知,知而不改,才是最可怕的事。羅曼·羅蘭生平非常重視反省。反省就是自我檢查。用羅曼·羅蘭常用語說,就是“良心的檢查”。他認為人之一生就是錯誤與改正錯誤的斗爭過程,也就是“靈魂”成長和升高過程。善于反省(不是“反思”,不是泛思,)必須把“我”放到思想斗爭中去,反省決不能脫離“我”的實際,否則是“泛思”,是空想。
(二)“我們需要尋求那些給人以清新之感的靈魂。這種靈魂是極稀少的。我們必須去創造這樣的靈魂”。(見羅曼·羅蘭寄女友索菲婭的信《親愛的索菲婭》卷下,第46頁,此書無中譯)
這里說的是藝術創作,具體說,是指寫小說。羅曼·羅蘭的兩部多卷本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母與子》的主要人物,中心人物,都是“給人以清新之感的靈魂”,這是由于克利斯朵夫與安乃德都隨時檢查自己的靈魂,常常反省,保持良心的清白純潔。我國宋朝理學家朱熹有一首絕句:“半畝方塘一鑒開,山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里說的“方塘”就是良心(意識)的形象。“方塘”中的水為什么永遠是澄清的?因為有“源頭活水”滾滾地流入“方塘”。這里“源頭活水”就是指人經常自覺地反躬自省,善于認識錯誤,勇于改惡從善。或者說,不斷地提高自己對于真理的認識。思想之水必須經常流動,新陳代謝,否則就成為一潭死水,濁水,腐臭的水。這是人與禽獸主要不同之處。
(三)“誰要是愿意為他人效勞,首先必須自己是自由的。即使是愛,如果是奴隸對主人的愛,那也是一文不值的。”(見羅曼·羅蘭反戰小說《格萊朗波》,第232頁。此書無中譯)
這兒“自由”一詞是自覺自愿。愛祖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這種感情如果是建立在真誠的覺悟上的,那么即使為了實現這種愛的激情需要以自我犧牲為代價,也在所不惜,也會感覺自由,甚至感覺幸福。
這種自由和剝削階級所謂“自由”完全不同。剝削階級要求的“自由”是滿足個人欲望的“自由”,是自私自利的“自由”,損人利己的“自由”。剝削階級的“自由”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的個別人的“自由”,是以他人的不自由為條件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解放全人類,然后解放自己的自由。只有在天下人人皆自由這個條伴下,個人才能夠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天下人人皆幸福的條件下,個人才能夠真正幸福。
(四)“真理是自由人的祖國。”(見《母與子》中譯本下冊)
把自由和真理聯在一起,問題就比較容易說清楚。可見真正的自由絕對不是個人主觀要求,主觀判斷的“自由”,而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自由。
什么是真理?真理決不是某人強權在手,強加于別人的觀點和判斷。真理是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一切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所謂掌握真理,乃是個人主觀自覺地符合于客觀規律,服從客觀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這樣辦事對于人人都有利。
(五)“自由向來是一切財富中最昂貴的財富。”(見《母與子》)
世界上并非人人都自覺自愿服從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自愿按客觀規律辦事。要是全世界的人全部按客觀規律辦事,那么組織一個公平合理的人類大家庭就不困難了。可是要辦到這一點,必須經過漫長的斗爭,付出昂貴的代價。因為我們所向往的自由是全人類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少數人胡作非為的自由。
(六)“對我來說,文學不是一種游戲。”(見羅曼·羅蘭回憶錄《貝濟傳》,上冊第25頁。此書無中譯)
羅曼·羅蘭對文學藝術的態度一貫十分嚴肅真誠。這是由于他的人生態度一貫嚴肅真誠。他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與藝術,反對輕率和玩世不恭的態度;反對脫離現實,反對逃避個人的或社會的實際問題。這種實事求是的思想常常出現在他的作品中,雖然他沒有用這個題目發表過系統的長篇大論。
(七)“在所有的偽善之中,唯美派的偽善最使我反感。”(見《母與子》,第462頁)
唯美派用華麗或輕松圓滑的外衣,掩蓋人生的苦難或社會的矛盾,而且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錯誤口號,蠱惑人心。這是羅曼·羅蘭最反對,而且痛恨的。也就是說,反對文學與其他藝術的形式主義。反對為形式而形式,以形式為主,思想感情的實質為副。反對內容遷就形式。主張以內容為主,形式為內容服務,而不是相反。
(八)“一切能永存的藝術作品,是用時代的本質鑄成的。藝術家不是獨自一人進行創作。他在創作中反映他的同時代人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熱愛和夢想。”(見《母與子》,法文版第914頁)
這里提出一個重要問題:藝術創作是個人性,和作品影響不可避免的社會性,兩者之間的矛盾。我們要求藝術家真誠,嚴肅;要求藝術家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真情實意,而不是人云亦云,或逢迎時尚的一套把戲。然而我們必須提醒藝術家(哪怕他是最了不起的天才),即使是他內心深處的寶藏,也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的,不可能是從母親肚子里帶來的,而只能是社會生活,文化熏陶逐漸成為他的心智,他的“靈魂”。藝術創造固然要強調個性,但這和個人主義是兩回事。藝術家如果認為一切屬于他自己,屬于個人;一切為了他自己,為了個人,必然走上醉心名利,只求名利,不顧一切的個人主義錯誤道路,而在創作過程中完全喪失社會責任。這是羅曼·羅蘭堅決反對的。
(九)“不但藝術作品要真誠,藝術欣賞也必須有真誠的心。只有真誠的心能領會藝術魅力。”(見《母與子》中譯本卷下)
有一次,安乃德和她兒子瑪克一同到音樂廳去聽演奏。安乃德被交響曲的強大深沉的波濤(旋律)感動得泣不可抑。兒子瑪克畢竟比母親年輕二十多歲,他對于這種樂曲不十分敏感,他覺得這種音樂屬于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當然,藝術作品也有年齡,也有老中青的分別。)但是瑪克聚精會神地聽這個對他來說已經不十分“及時”了的樂曲,他也聽得入迷了,因為他是懷著真誠的心在欣賞音樂。羅曼·羅蘭一貫強調用真誠、嚴肅的態度對待藝術作品(包括文學),反對用輕率、浮淺的低級趣味,和無聊消遣的態度對待藝術。他甚至認為藝術作品的完成并不是藝術家單方面的事,而是藝術家與群眾(讀者、觀眾、聽眾)雙方的合力創造。由此可見,對群眾,尤其對青年,進行藝術教育是多么重要。
(十)“克利斯朵夫從來不自詡為正確的人,但他始終是誠懇的人。”(見書信集《親愛的索菲婭》下冊,第167頁,無中譯)
羅曼·羅蘭幾部小說中的中心人物突出的性格都是真誠、懇摯。他本人也是如此。他在晚年寫的回憶錄《內心旅程》中說:“我畢生沒有什么優點,如果有,那無非是真誠而已。”
“真誠”二字是我們研究羅曼·羅蘭,學習羅曼·羅蘭時必須掌握的一把金鑰匙。
(十一)“我們自己只有在夢幻中創造(并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大眾)幸福與偉大,而夢幻卻比現實更加現實。”(見羅曼·羅蘭書信集《瑪爾維達》第167—168頁。此書無中譯)
“夢幻比現實更現實。”這句話出現在理性主義者羅曼·羅蘭筆下,十分引人注意。因為這個觀點是二十世紀法國(從本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現代派文學家的主要理論武器。羅曼·羅蘭這句話大約寫于上世紀末年,或本世紀初年。那時唯心主義哲學家柏格森(一八五九——一九四一)的生命力論與直覺論正在法國風行(而且不僅在法國,可以說在國際上)。羅曼·羅蘭可能不知不覺地受一點柏格森的影響,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他創作小說《母與子》時期(從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初期),正是法國現代派主流超現實主義盛行的時期。在小說《母與子》改定本(出版于五十年代初)的《導言》中,作者強調一個人真正的生活,是他(或她)的內心活動,而不是可以看得到聽得見的表面言行。這種論調有它深刻的一面。
(十二)“我何所求?我所求的是指引人類前進的種種規律獲得勝利。而且我現在比以前更親切地感覺到,這些規律無論如何是會勝利的。”(見《內心旅程》第297頁)
從羅曼·羅蘭平日的言論以及他的著作看,他在這里所說的“指引人類前進的種種規律”,無疑地是指全世界勞苦大眾的解放,科學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