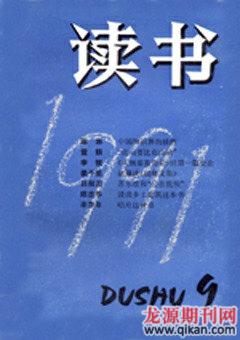胡繩談《胡繩文集》
《胡繩文集(一九三五一一一九四八)》,重慶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出版。胡繩在和我的一次談話中,談到這本文集。現在我把談話記錄稍加整理,并征得胡繩同志同意予以發表。以下的談話記錄中發問的是我(姜千里),答復的是胡繩同志。
問:胡繩同志,最近我們看到了《胡繩文集(一九三五——一九四八)》。這本書收有一百七十篇文章,七十多萬字。根據您生于一九一八年推算。這些文章是您在十八歲到三十歲時寫的。我想問胡老,您能不能談一談為什么您能在這樣年輕時就寫出這么多文章?
答:好的,我就來談談。我在三十歲以前寫的文章,實際上還不止這些。我在編輯這本文集的時候,把收集到的文章選擇出大約一半,編在這個集子里面。其他還有些文章已經收集不到,而且大多我也不想去收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還寫過、出版過六、七本專題的書。所以,總的來說,在那時期我寫的東西可以說是相當多的。
為什么要寫這么多?主要由于客觀的需要。那時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客觀上確有許多問題,許多現象使人心神不安,使人苦惱,使人激奮,需要思考,需要評論。而且也有些報紙、雜志要我寫文章。我當時雖然還有些別的工作,但主要工作就是為報紙雜志寫文章。
問:那么胡老,請問您是怎樣開始寫作的?
答:要說開始寫作,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樣,最初的寫作就是在小學、中學的作文課上。但我在中學生時已經開始寫作文課以外的文章。記得在初中時候曾和兩個同學一起,把各人寫的文章謄寫出來,訂在一起互相傳閱。到了高中時候,我還和一些同學辦壁報。那一年是一九三三年,正是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我們為紀念馬克思出了一期壁報。至于說把文章用鉛字排印出來,除了給學校的校刊和作為中學生投寄到學生雜志上的文章以外,我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是在一九三四年。那時我投稿給《中華日報》的一個叫《動向》的副刊。這個副刊是左翼作家聶鉗弩編輯的。當時我并不認識聶紺弩,他發表了我這個高中學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這些文章現在我都沒有再去找尋了。在魯迅先生的《花邊文學》中的一篇《漢字和拉丁化》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繩,他指出我在《走上實踐的路去》一文中的說法是不恰當的。那時魯迅先生在《動向》上發表了不少文章,不過用的是筆名,我并不知道這是魯迅先生的文章。所以,我開始寫文章在報刊上發表是在一九三四年。但是收在這個文集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卻是在一九三五年寫的。
問:您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
答:我這個文集里按文章性質分了四個部分,也就是四輯。每一輯里的文章,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輯“雜文”中的第一篇。這篇文章題目叫《報復》,那是一九三五年我在大學一年級時寫的。(我只在大學讀了一年)文章的末尾還記明是“三月十六日晚在北平圖書館”,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圖書館。對這篇文章也可以簡單說幾句話。我本來已經忘記了這篇文章。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新文學大系》(雜文卷)中收入了《報復》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當時是投稿給上海由曹聚仁主編的《芒種》雜志的。我很佩服雜文卷的編者,他竟然這樣勤于爬羅剔抉,注意到了這篇短文。因為《新文學大系》選登了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氣把我在二十歲以前寫的這篇文章收入這本文集里面。
問:那么,您在二十歲以前寫的文章,在文集里還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滿二十歲。所以一九三六、三七年寫的文章都是二十歲以前寫的。在這個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當然只占極小部分。這十幾篇里多數是收在“思想文化評論”這一輯里的。對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兩篇說一說。一篇是《胡適論》,那時我參與辦一個名叫《新學識》的雜志。這個雜志起先叫《生活知識》,被國民黨當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識》,又被禁,然后才改成《新學識》。參加辦雜志的有一位搞戲劇的張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這個刊物上搞點新的欄目。于是我們就開始設立一個人物評論的專欄。張庚寫了一篇《梅蘭芳論》,我寫了一篇《胡適論》。這篇《胡適論》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前。后來在五十年代批評胡適的運動展開時,有人找出了這篇文章。有的同志覺得這篇對胡適的評論還是比較公允的。附帶說一下,在我的這個文集里面涉及胡適的文章有好多篇。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胡適從國外回來,準備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我還寫了一篇對他表示歡迎的文章(即題為《新文化運動所需要的根、枝葉和所需要的陽光》的一篇)。但是胡適并沒有當北大校長,卻參加了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而且從蔣介石手里接受什么憲法草案。我就寫了一篇很尖銳的批評文章,這就是時事政治評論中《制憲不如散會》這一篇。后來胡適又向學生說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我忍不住又寫了篇短文加以駁斥(“雜文”輯中《理未易明么?》)。
現在回過來還是說一九三七年我寫的另一篇文章,這篇的題目大概不大引人注意,就是《我對于現階段中國思想的意見》。當時,就在《新學識》雜志上,我們的一個朋友寫了一篇文章,認為既然要抗戰,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種思想的區別。他的說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種主義中的高遠理想暫時擱起,而共趨于民族解放之途”,由此他主張“思想的統一”,而且要由政府來統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紛爭”。我看了這篇文章,認為這個意見是錯誤的。我的文章認為,在抗日這個共同大目標上應該求得一致,但是這并不妨礙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許各種思想相互論爭。我的文章中說: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敵救亡的大目標下自由地發展,這樣才能保證中國思想的活潑的發展和光明的未來。這些話當然是針對想用一種錯誤的思想來實行統一的國民黨而說的。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反對寫上述文章的那位朋友。我記得當時我這篇文章發表以后,在參加這個雜志的一些同志聚會座談的時候,還有人指責我對自己的朋友提出批評是不對的。現在看來,我以為我的這篇文章的基本論點是站得住的。當時正是從十年內戰轉入抗日統一戰線的時候,在進步人士中間不免由于誤解統一戰線而產生某種糊涂的觀點。我這篇文章提出的論點可能是有意義的。我記得,夏征農同志在抗戰開始時選編出版的一本關于思想文化問題的文集中曾收入這篇文章。附帶說一下,我在一九三七年雖然提出和那位朋友不同的意見,但他是個很好的同志。我們以后還曾一起過地下黨的組織生活,合作得很好。他就是已經逝世的經濟學家狄超白同志。
問:我們知道您曾出過《理性與自由》這個論文集。有些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思想發展的書,提到這本集子中的文章。不知道這些文章是不是都收在現在這本文集中了?
答:《理性與自由》這本集子是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評論集。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現在這本文集中的第一輯“思想文化評論”中了。但是,這一輯比那一本論文集的文章多得多。剛才提到的在抗日戰爭開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沒有收入《理性與自由》這本集子中間。還有抗日戰爭初年,現在也增加了幾篇文章。那本集子是出版在一九四六年,當然一九四六年以后的一些文章也是在那本集子中沒有的。
“思想文化評論”這一輯也許可以說是我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這里面我評論了當時存在著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學說。用現在的話來說,我是參加了當時的百家爭鳴。在那時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處于被壓迫的地位。馬克思主義者參加百家爭鳴,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簡單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沒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體地進行分析,認真地講清道理。記得在十年前,我在美國遇到一位從臺灣出來的學者,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和我說,他對于我評論錢穆的文章很感興趣,曾經在臺灣復制了這篇文章,在朋友間傳閱。最近有個朋友看了我的文集的第一輯以后,表示欣賞這些文章,并且引用禪家公案的話“有理不在高聲”加以稱許。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說,這些批評文章不是靠放大嗓門、虛張聲勢來壓倒人,而是靠說清問題,講清道理來說服人。這些文章難免有缺點,有失誤之處,但如果在寫法上還有點可取之處,恐怕超不過這位朋友的說法。
問:您剛才說,第一輯“思想文化評論”是這本集子的主要部分,但我們對第二輯“史事評論”和其他兩輯的文章也很感興趣。我想問您,為什么在第三輯“時事政治評論”中只收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文章?是不是在這以前您沒有寫過這方面的文章?
答: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我在一些報紙、雜志上已經發表過不少有關時事政治評論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比較零碎,我覺得已經沒有保留的價值,不會引起現在讀者的興趣了。但是我對一九四六年以后寫的這些評論文章是有點偏愛。一九四六年到四八年是中國經歷著劇烈的巨大的震蕩的時期,從抗日戰爭后的和談轉入大規模的內戰。我們黨先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努力爭取和平民主的局面,進行自衛戰爭,然后由于客觀局勢的發展轉入團結全國人民用革命戰爭來把舊中國改造成新中國。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局勢發展迅猛,各方面的情況變化很快,出現了極其錯綜復雜的形勢。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重大時期。對于寫時事政治評論的人,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時機。當時又有上海的幾個進步刊物,包括柯靈、唐
問:那么,您能不能再談談您的文集中的最后一輯“雜文”?按篇數說,這一輯的文章最多。
答:這一輯的篇數確實最多。但是,按篇幅說卻不是最多的一輯。因為這里面大多數都是很短的文章。我在這本文集的序言里說,這一輯中的文章有一些可以說屬于文學界賦予特定含義的雜文,例如這一輯的第一篇《報復》。其他許多文章可以說是屬于隨筆、雜感、短小的散文、短小的論文等。這一輯涉及的內容也很廣,有對當時國內政治社會現象的評論,也有涉及國際政治的評論,有涉及文化文藝問題的評論。甚至我還寫了篇對于電影大師卓別林的評論,這樣的題目是我一生以后再也沒有涉及過的。我之所以把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因為我覺得這些文章從各個側面多少反映了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正在經歷著嚴重的苦難,并且進行著艱苦奮斗的時代,也是對于光明的明天充滿著希望的時代。
問:最后我還想請教胡老一個超過你的文集范圍的問題。在中國近代文化界、著作界里,三十歲以前已有著作問世,編成文集的有沒有先例呢?
答:這樣的先例有很多。試舉文學界最突出的例子:郭沫若在三十歲前出版詩集《女神》,曹禺在二十四歲發表《雷雨》,他們的這些作品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我是望塵莫及的。至于出版文集,據我現在想到的,有梁漱溟曾印過《漱溟卅前文錄》。近代中國的學者,年輕時著作豐富,且有巨大影響的,我想應該首推梁啟超。梁啟超生于一八七三年,他在參加戊戌變法時只二十五歲,那時他已經發表不少引起世人注意的文章。從《飲冰室全集》可以看到他在三十歲以前所寫專著和論文,方面之廣,數量之多是驚人的。他在青年時期的論文當時已編輯出版,廣為流行,而且影響了一代人的思想。就這情形說,在近代著作界中,恐怕是沒有人能比得上梁啟超的。
(《胡繩文集(一九三五——一九四八)》,重慶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版,13.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