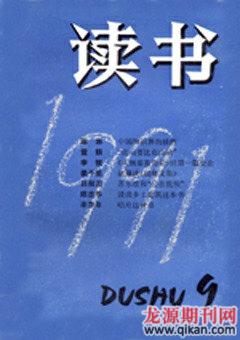理學的兩面
廖可斌
《宋明理學與文學》一書以理學與文學的關系為切入口,對這一階段內文學發展的各個重要環節,都作了新的審視,從而提出了一系列發人之所未發的新見解。例如,關于元雜劇的盛衰,該書首先考定元雜劇興盛的時期是在“太宗取中原以后,至元一統之初”,而非元貞年間;元雜劇興盛時期的劇作家全是北方人,元后期的雜劇作家則幾乎都是南方人或流寓南方的北方人。然后指出,宋金對峙以迄金元之際,程朱理學在南方廣為傳播,北方士大夫則對之持輕蔑的態度。他們主要是繼承北宋蘇軾等人學術思想的影響,因此有“蘇學盛于北”之說。元朝前期,蒙古統治者的文化政策比較疏略。直到仁宗延
文學本質上是生命意志的自由表達,它必須以人們豐富生動的生活內容和思想感情作為反映和表現的對象。從思維的旨趣到方式,理學與文學都是相互排斥的。因此,自理學誕生之日起,它就與文學勢如水火,互不相容。從宋元到明清,可以說理學盛則文學衰,而文學的每一次蓬勃發展,都與理學統治地位的動搖及反理學思潮的高漲相伴。要弄清這一千年間文學發展的軌跡,理解這一時期內文學藝術的精神意蘊,而忽視對理學與文學相互關系的考察,必難中肯綮。幾十年來,我們比較注重研究社會經濟和社會階級斗爭對文化的影響,這是一個進步。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意識形態各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忽視了當時的學風和統治者的文化政策對文學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但如果有人對此進行歪曲,說經濟是唯一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他就是把上述命題變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謬的廢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各種因素,如政治制度、法律、哲學思想、宗教觀念等,也都要對各種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對斗爭的形式起主要的決定作用(見恩格斯一八九○年九月寫給布洛赫的信。)只有對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狀況進行詳細考察,我們才可能把握包括文學發展在內的各種歷史進程的真象。從這個意義來說,《宋明理學與文學》一書的價值,并不限于它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見解,更重要的還在于它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在研究方法上能給人以啟迪。
當然,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理學對文學的影響也是復雜的,這種復雜性根本上又源于理學本身性質的兩重性。理學一方面宣揚“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官方哲學;另一方面,理學的創始者及其大師們對理與氣、格物與致知、一分為二、合二為一等許多抽象的哲學命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對推動中華民族理論思維能力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邏輯思維的發展,對崇尚渾樸圓融審美境界的古典詩歌及以風情旖旎為審美特征的詞曲的創作不利,但對促進宜于說理敘事的散文的創作有益。因此,幾乎是與理學的萌芽同步,散文(古文)的創作在中唐興盛起來。入宋以后,隨著理學的發展,古文創作更趨繁榮。自此理學與古文便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唐宋八大家到元代的姚燧、虞集(他們兩人被黃宗羲推為元代古文家之冠),再到元末明初的浙東派、明中葉的唐宋派,以至清代的桐城派、湘鄉派等,著名古文家幾乎都與理學有牽連,其中不少人本來就是理學家。他們的散文大多用詞簡煉準確,邏輯性強,說理透辟,與過去帶有詩的性質的賦、駢文相比,理性思辨水平確實大為提高了。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雖然一強調“格物致知”,一強調“致良知”,但它們在以探究主體的性命為宗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由程朱理學到陽明心學再到王學左派和異端思想,可以說是理學發展的邏輯結果。只是到了陽明心學特別是左派王學和異端思想,理學那種倡導主體精神的特點表現得更為鮮明突出罷了。而明中晚期包括公安派在內的浪漫文學思潮,就是在左派王學和異端思想的直接孕育下產生的,沒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奇妙,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最后竟演變成倡導個性解放的進步思想潮流和文學思潮的母體。如果我們不承認理學性質的雙重性及其對文學的影響的復雜性,就無法解釋上述理學與古文、理學與包括公安派在內的浪漫文學思潮的關系,尤其是后者。
(《宋明理學與文學》,馬積高著,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版,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