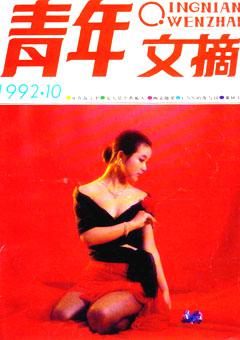玻璃珠里的天堂
可 人
偶爾在小侄女的玩具箱里看到一粒彈珠,淺藍而渾圓,記憶便似脫僵的野馬,飛回泰順街古老的日式宅第,飛回梳著辮子念再興幼稚園的四歲的童年,最后停駐在一顆淺淺的、藍色的彈珠上。
我上幼稚園的時候,眼淚多,歡笑少。爸媽那時都上班,幾經輾轉,我念了不下五、六家臺北的托兒所、幼稚園。但我憎恨去上學,那里吃了飯就得午睡,下午三點一到就強迫抱著玩具玩上一個小時。
我常常一個人溜出去坐在滑梯上遐想;彈珠是怎么來的,已經不復記憶,只記得它總靜靜地躺在掌心里。很多老師都知道幼稚園有這么個古怪的孩子,只喜歡玩彈珠和寫字。
古怪的孩子受不了幼稚園的生活,提出要做小學生。面對這樣的奇想,父母是開明的。那年秋天,我六歲的生日還沒過,已是一年3班的學生。為此,媽媽辭了職。
那個半都市、半鄉村的學校日子是美好的,六年的光陰,由黃梅調、大肚魚、知了的叫聲連綴而成。雖然塑膠的“昂阿仙”在小學生中風靡一時,我對彈珠卻始終不曾忘情。三年級那年的圣誕節,班上轉來一個外校的男生,卻偏偏成了我同桌而坐的芳鄰;在那對男生恨之入骨的年代,我簡直討厭死他。他卻從不以為忤;圣誕前夕,桌子上擺了一張卡片和兩粒豪華而巨大的彈珠,他對我笑著說:“我哪天要去拜訪伯父、伯母。”我不曉得他哪兒學來的這么文縐縐的話。
回家之后,我學著說給爸媽聽,一家人都笑彎了腰。多年后,我見到這位年輕優秀的醫生,提及這段“伯父、伯母”的往事,仍有九歲那年的會心。我的青梅竹馬之戀,雖未開花結果,兩粒彈珠卻在時光流轉間,愈見晶瑩;多年后,我仍愛撫拭把玩,它里面有純稚的友誼,有成長中的寬容和喜悅。
長大以后,我開始鐘情玻璃制的小動物。心里雖印有一片孩子的天堂,但生活卻被升學的壓力逼得喘不過氣來。
高中時代,我是有名的叛逆,似懂非懂的看尼采、叔本華和禪學。總覺得自己是聯考制度下犧牲的天才,不知怎的,成天一腔悶氣。綠衣黑裙的女孩,不想進臺大,開始逃學、逛街,一心想上山修行。
有一天,我走過新公園前的地攤,一個黑瘦的小男孩用他的大眼睛看著我,他的面前擺了一堆小狗、小鹿,他的腿上,擺了一本四年級的算術,我癡癡的買了一對小狗,然后坐上車,回家,想了一整夜,想透了自己的自私、幼稚和幸福。第二天,決心做個安分的學生。那時候,五月的蟬聲正濃,有即將來臨的一場大考,有新的前程,有另一份人生不同的風景。于是,我真高興自己回來了。多年后我看到那對小狗,想起自己曾經執意做個好老師的心意,仍覺得很溫柔。
二十初度,好友出閣,我穿著白紗禮服,陪她走過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紅氈路。第一次穿高跟鞋,第一次戴首飾,第一次似懂非懂的為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的誓言覺得幸福;也是第一次,開始揣想多年之后,自己是否也會如此走向一個衷心等待的誓約。新娘指上的鉆戒與頸間閃亮的項鏈,再度勾起我幼年時代的玻璃珠情結。散席之后,我對媽媽說:“以后我出嫁,媽媽也給我買一串那種很亮的項鏈吧!”媽媽笑著看我,“媽媽一定給你買最好的!”
多年之后,媽媽果然千山萬水的帶來了當年的承諾,只是我戴著它,心中竟無了歡喜,只有茫然,一步一回首,是進還是退?多年來,自己凡事不落人后,情感的生活,一經等待公主和王子式幸福完美的結局。波浪雖美,仍是生命的漣漪;向往安定,卻把自己交給另一個混亂惘然的生活。當一切閃亮的人聲喧嘩,歸于平淡,我拿著那串項鏈,孤獨的想起二十歲的那個日夜……
緣起緣滅是人生的心折,當傷痕累累的發現自己夢中的玻璃屋原來易碎,象牙塔里的小公主也不得不收起王冠,走向真實的沙石泥土,在陽光風雨中,我已經失去寫詩、作夢的權利,眼淚遂成深遠的眸光,汗珠成為陽光下健康的膚色,碎了的玻璃娃娃,一點一滴的絕處逢生,發現自己又可以微笑的時候,我的玻璃心變成水晶;水晶是多年磨練的礦石,如果生命了無挫折,我們永遠看不到光波折射的美麗。也許我仍該慶幸,慶幸自己在成長中的體會與了解;慶幸自己仍能無怨無恨的生活;慶幸自己仍有一個玻璃珠里的天堂。
(豆豆摘自《南洋華人散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