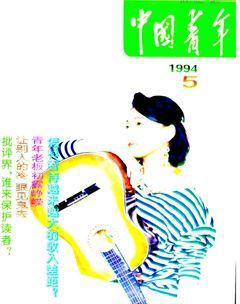“青年領袖”專業,路怎么走?
張力
共青團組織在全國有著一支近23萬人的專職干部隊伍,這支隊伍具有明顯的年紀輕、文化高等特點,就其從事的事業而言,又有人稱他們為“青年領袖”。多少年來,這支隊伍戴著用“朝氣蓬勃”“前途”“希望”等詞匯編織起來的美麗光環,吸引著無數渴求進步的有志青年和年輕干部。
然而,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他們忽然發現周圍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頭上的光環在慢慢失去光澤。
團干部轉業越來越困難了
專職團干部,顧名思義,就是專門從事共青團工作的干部。這些人必須年輕。中組部曾轉發團中央組織部對各級團委書記任職年齡上限的規定,該規定從團縣委正、副書記至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都有具體的年齡要求。這就意味著,在共青團崗位上不能退休養老,團干部必須轉業,也就是二次就業。職業既是謀生的手段,又是實現生命價值的最基本途徑,所以,對于處在步入人生發展時期的青年干部來說,轉業自然成為一件頭等大事了。
建國初期,各地黨政部門大量抽調共青團干部,因此出現了團干部調出多于調入的情況。為此,共青團中央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多次發文強調,團組織既要不斷向黨政部門輸送優秀干部,做到“一池活水”,又不能過于頻繁地選調團干部,強調團干部的輸送要“先入后出”、要“保留骨干,以資熟手”。“保留骨干,以資熟手”作為團史上一個特有的用語,記載了共青團干部供不應求的緊張局面,記載了共青團為黨輸送干部的最輝煌的歷史。而今天,那個時代似乎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團干部面對的卻是另一番情景:
——某省團干部調出與調入的比例,1979年至1983年為107.8:100;1984年至1987年調出少于調入,比例為71.12:100;1988年至1990年該比例繼續失調為43.7:100。近二年也未見扭轉。
——某省團委幾個處級干部,年齡早過“不惑”快近“知天命”,但對外聯系工作幾年,對方不是說沒有編制就是沒有職數。其中幾位找工作已找得“三而竭”,反倒平靜下來,看樣子要在這個青年工作部門“養天年”了。單位領導不無憂慮地說,過幾年共青團是不是也要成立一個老干部科了。
——某省搞過一項調查,全省共有999名招聘的鄉鎮團委書記,他們月工資人均80元左右,年齡平均30多歲,至今很多人仍在苦撐著。這是因為他們不甘于這樣轉業,這樣轉業的出路似乎仍要回到土地上。抱著對遙遙無期的“鐵飯碗”的最后一線希望,他們欲上不能,欲下不忍。
——1987年至1992年底,某省共轉業處級以上團干部56人,其中按原職級轉業的31人,降半職級使用的25人,不過這25人中有11人在任命書上括上了“原級別待遇”,這就算不錯了。
轉業,在團內確已成為一個令人憂慮和頭痛的大問題。
共青團真的是不干遺憾,干也遺憾
如今,一些過來人,常常評論團的工作:我們那個時候,多么活躍,開展各種活動,青年是一呼百應啊!哪像現在這樣!—可事情并非這么簡單,“我們”那個時候,文化設施少,信息傳播渠道少,貧乏、單調是當時青年業余生活的特點。所以,搞個簡單的文體活動,包括集中起來政治學習,拿份報紙雜志念一念,你再去煽一煽,就足以讓小青年崇拜你一陣子。現在,社會傳播渠道多種多樣,誰比誰知道的多不了多少,怎么是那么簡單的一個“活躍”就了得?另外,那所謂輝煌的時代是在建國初期,社會管理機構尚不完備,黨、政、婦、武、團等幾個部門縱橫天下,團組織與團干部的位置也就相對顯得突出了;階級斗爭天天講的年代,突出政治,團的政治屬性在社會上引人注目,相應地團干部的職業也令不少年輕人向往。那么現在呢?幾十年傳統體制下形成和建立起來的青年工作機制,隨著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隨著社會利益分配機制的重新調整,共青團工作運行的某些條件已失去;社會管理方面已有上百個部門,作為小字輩的共青團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們且不論這種變化是社會發展的階段性需要還是歷史大趨勢,且不論其擁有多少歷史的遺憾和社會進步意義,僅是這種變化與目前共青團管理機制和運行方式的不適應,僅是這種變化與舊有的對共青團活動的評價標準的落差,就足已影響社會對共青團和團的干部的價值評判。
一位團干部見到熟人,人家打招呼“忙嗎?”剛要回答正在籌備一項什么活動,忙得要死,話到嘴邊尚未出口,對方已經“理解”了:“你們那個地方有什么事呀,全是些虛的,趕緊挪個窩算了。”一下子被噎得背過氣去,未出口的話伴著苦澀艱難地往肚子里咽。需要理解時不能被理解,成就欲望最強烈時沒有成就感,成為團干部的突出心態。
一位團縣委書記說:現在基層鄉鎮,衙門最小的是團委,活兒最忙的也是團委。武裝部長是副鄉級,婦聯主任也是副鄉級。鄉里一大群副鄉級。團委書記最年輕,官當然最小。配合中心工作是壯勞力,要打頭陣,當先鋒,本職業務只有在中心工作之余來干。
如果說共青團干部年紀輕,提拔快曾一度呈現優勢并為外界羨慕的話,那么今天,隨著組織人事部門對干部管理的逐步規范化,這種優勢已徒有虛名了。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同一年的大學畢業生,幾年之后,人家又是業務職稱,又是行政級別,哪頭合適靠哪頭。而團干部在單軌道上“熬”,就是比人家慢。再說即便同一職級,內涵也不相同,人家是實打實的,你就是有折扣的,因為你還要二次就業,還要重新被考驗、被選擇,很可能要降職安排。降職被看成是順理成章的,因為你或許是不該輪上提拔的,你或許是占了共青團崗位提拔快的便宜。
干部管理權限下放后,團干部轉業的困難更大了,中層干部的轉業,要靠團委自己想辦法安排,而對接受單位來說,安排一個人就意味著占了一個職數,大家都想提本單位的人,這或許得賴干部管理體制的分割與封閉?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的今天,不少團干部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會議上、生活中,談論起來,財政稅收、金融債券、高新產業、投資政策、對外經貿……感到插不進嘴,接不上話,怪自己嗎?社會分工不同,當自己踏進共青團時,崗位工作就是進行對青年人的正面教育和對團員的組織管理,從沒有懈怠過。誰知卻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變成了知識結構上的“瘸腿”。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懷疑自己的價值,懷疑自己的選擇,憂慮自己的未來,這支隊伍中,一種嚴重的群體失落感正悄然蔓延。
于是,人心不定,思走、思動。一位曾多年從事團的領導工作的某省委書記曾深有感觸地說:“共青團工作可干,但不可也不能常干。”一位轉業到中直部門的團的領導干部說:“共青團工作不干遺憾,干久了也遺憾。”一位團省委書記出身的市委書記說:“我看共青團工作不干也沒什么遺憾的。”
我們知道沒有人愿意否定自己的歷史。我們卻不知道,什么原因使他們得出這樣復雜的結論?
上下求索探索團干轉業出路
從共青團的生存和發展計議,團干轉業的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一些團的組織在幾經沖撞、苦求無門之后,便已退而結網,苦練內功了。
某省團委為使自己的隊伍有良好的素質,決定先嚴把“入口”關。對調入的團干部要求有一定的專業特長。他們還要求縣級以下專職團干部中配備科技副書記,一是為了有利于工作,二是要帶出一批懂業務的隊伍。
團干部們在意識到了自身前景的不樂觀后,也在以一種進取的姿態迎接命運的挑戰。前些日子,《中國青年報》上有消息傳來,某省級團校為團干部和團員青年服務,掛出了“青年職業技術學院”的牌子;又聽說某地團委對機關團干部實行上下掛職鍛煉;還有的地方團委制定了鼓勵團干部在職攻讀第二專業的政策,舉辦團干部微機班、經貿知識培訓班、外語強化班……
今年某省一個部屬的研究所工會與團委合署辦公,團委書記又兼上了工會主席,從而引發了團內的一場是工會“吃”了團委,還是團委“吃”了工會的討論。但不管怎么說,據我了解,團委現在用工會的設施搞活動,工作比以前活躍多了。我還想這位團委書記現在如果要動一下地方,似乎條件要優越一些了,至少沒有理由壓他半級安排。
去年12月,共青團十三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我國青年工作戰略發展規劃》,關于團干部有這樣一段文字:“適應市場經濟、機構改革和團的工作需要,著眼于團干部的長遠發展,切實加強對團干部的培養、教育和管理,努力把團干部造就成為既能從事青少年工作,又能全面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復合型人才。”培養能全面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復合型團干部,看來是今后團干部培養并順利實現二次擇業的關鍵。作為一個團的干部,我期望著也相信著團干部轉業更加美好的明天,因為那明天畢竟對于今天在崗的團干部是一份鼓舞,一份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