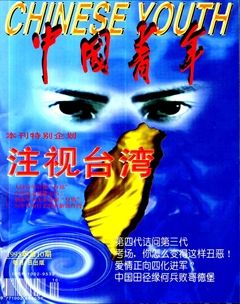我能!我能!我能!
劉新平
說話需要夸張口型。雖然累點,但姜明彩心里松快。跟孩子們在一起,耐心跟教室一樣必需站在陽光里,他們聽得見自己生長的聲音A
濰坊。
1995年的春天;雨下得特別勤。
已經很晚了,雨還在下。路燈黯淡,映照著路面上一洼一洼的積水。騎在自行車上的姜明彩不由重重地打了個寒噤。
她已騎了整整一天的自行車了。找了所有該找的單位,打問了一切熟悉和不那么熟悉的人——她放下一個年輕姑娘的矜持甚至自尊,只為了給她那些耳聾的學生們找一個可以棲身的學習和生活的場所。但她得到的,是一次次的失望。
地方其實有的是,可你付得起昂貴的房租嗎?
20天以前,她和她的學生們是有教室和休息室的,雖然那只是由自行車棚略加改造而成,簡陋而潮濕,但因為孩子們的存在,卻總是充溢著一股掩不住的勃勃生機。
但不幸總是那么突如其來。那天,她剛在黑板上寫下一首兒歌,轉身,上前幾步,夸張著口型,準備教孩子們念。突然,轟的一聲,她剛剛站過的地方,落下一堆瓦片和土塊,棚頂上立刻開了一個大大的天窗。隨即,一股嗆人的灰塵彌漫了整個教室。她無暇細想,猛的沖將過去,一邊一個挾起了兩個學生就往外面跑。放好,再沖進去……當學生們都離開了那個暗藏殺機的教室,她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教室已無法容身。家住濰坊的學生們都回家“待學”,外地的高倩和史程程一時無法離開,她只好將她們領回家。她家住一套兩居室,4口人,本來就不寬敞,一下子多了兩個孩子,便顯得局促和雜亂起來。更糟的是,沒過幾天,又有3位學生家長將孩子送了過來,說是孩子不愿呆在家里,想老師想同學,不吃不喝整天鬧,非得來……
一般而言,聾兒比正常孩子更多一份惡作劇的天份。要讓他們沉靜下來,幾乎就不可能。5個孩子在狹小的空間里上演著一出出大鬧天宮的游戲。姜明彩的父母幾無立錐之地,看著同樣愁眉苦臉,一籌莫展的女兒,老倆口嘆口氣,打著雨傘出門了。
一天,她下樓給孩子們采購,一位鄰居板著臉迎上來:“你們家那些孩子住到什么時候走?”她明白,她那5個除了吃飯、睡覺就無一刻安閑的學生實在是把左鄰右舍給吵煩了。她陪著歉意說真不好意思對不起請多包涵,等等。
以后幾天,不斷有樓上樓下的鄰居見面就問孩子什么時候走。她只得一遍遍解釋、道歉,一次次重復同樣的保證:新教室將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
她意識到了情況的嚴重性。
這之前,她曾拜托幾個昔日的同學幫忙找房子,但一直沒有結果。“不行,我得自己去找!”B
春雨連綿。
事實證明,找一處便宜又寬敞的教室對姜明彩而言實在是一項力有不逮的大工程。
已經很晚了。她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蹬著車。她不敢回家。“怎就這么難呢?”她在心里無望地問自己。
1992年,姜明彩畢業于濰坊職業高中幼師專業。這個來自農村的女孩,成績一直都是全班最好的。因為這一點,她被推薦到聾兒語訓學校當老師。
語訓學校的學生都是些4到8歲的聾啞兒童,有的是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藥物中毒致聾。聾兒語訓的目的就是充分挖掘孩子們的殘余聽力,進行特殊的訓練、學習,引導他們逐步恢復聽力,恢復語言功能。對聾啞兒童的康復語訓,已被列為本世紀末中國殘疾人的三大“搶救工程”之一。
開始上課的時候,孩子們只是不停地打手勢與她交流,她不懂;她說的話,孩子們更是聽不見、聽不懂。孩子急,她更急。她明顯地感到了學識和經驗的貧乏。第一個月的工資,她買了一堆有關聾兒康復和語訓的專業書,廢寢忘食地讀。有不懂的地方,就一遍遍向其他老師請教。不少老師被她問急了問煩了,對她頗有些不以為然。
一年多的時間里,姜明彩在語訓學校的工作熱忱和工作成效有目共睹,她的專業水準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她的心卻常被刺得傷痕累累。
有人發現分發給孩子們的水果少了,懷疑的目光便盯上了她。理由太簡單了:她只是個臨時的,聘用的。更主要的是,她來自農村;農村人偷食學生水果,當在情理之中。她急了,斷然否認。有人去搜她的包,包里自然什么也沒有。就回轉身來,意味深長地盯著她瞧,像要用一雙“火眼金晴”照出她內心里的“妖孽”。
收拾了一下簡單的行李,姜明彩憤然辭職。跨出學校大門的一瞬間,她的眼淚奪眶而出。那是屈辱的淚,那也是……依依難舍的傷別的淚。
“不管怎么說,教了孩子們一年多,我跟孩子們已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說心里話,我不舍得離開他們。若不是萬不得已……”兩年以后,談起這段往事,姜明彩如是說。C
姜明彩的母親在濰坊市里開了一家服裝店,生意挺紅火。姜明彩就到母親的店里幫忙。她腦子靈光,手巧,對于服裝裁剪極有天賦。裁制出的服裝,單看款式,就令母親嘖噴稱奇。
姜明彩卻怎么也興奮不起來。人格受辱的傷痛已漸漸平息,代之而起的,是對班上那些孩子的深深思念。但她已不再是他們的老師了,她也只能在心里給他們送去一份深深的祝福。
那段時間里,她努力地克制著自己,不去想學校,不去想學生們,也不再想她曾受過的深深的傷害,她要讓自己平靜下來,平平靜靜地做一個小裁縫。
如果不是幾個學生家長的意外來訪,她無疑會沿著這條路平靜地走下去。
那天中午,姜明彩正在店里吃飯,突然聽見一個讓她心跳的聲音:“老……師!”她猛抬頭,原來是她班上的高倩。高倩的父母站在后面,正沖她微笑。
高倩的母親拉著姜明彩的手:“姜老師呵,你不知道,自打你離開學校,高倩就老哭。后來死活就不想去學校了。沒辦法,我和她爸只好領她回家。回家也不安生,整天鬧,哭著喊著要見你。沒辦法,就來了。”
高倩家住淄博,父母是雙職工,來一趟濰坊,顯然不易。姜明彩心里面熱熱的,將高倩拉到懷里。
“姜老師,你看這樣中不中:先讓高倩在你這呆上一段時間,我和孩子爸爸這就找保姆。等保姆找到了,我們再把高倩接走。”
姜明彩望著高倩母親那期待的目光,有一種久違了的情感在心里慢慢復蘇。
巧的是,中午剛留下了高倩;下午,原來她班上一個叫史程程的學生的爸爸也從昌邑趕到了濰坊。
“姜老師,俺孩子想你,在家里鬧得慌。要俺說,你不如也辦個聾兒學校吧,把俺程程收了,你學校里的板凳桌椅什么的,俺都免費提供。”史程程的爸爸是位做家具生意的個體戶,也是個最豪爽不過的山東漢子。他的這番話使得姜明彩怦然心動。“對呀,干嘛不能自己辦個聾兒學校哩!”她對自己說。
但她腦海里馬上就浮現出一些鄙薄的面孔來:農村人,想吃天鵝肉哩!自個辦學校,你能嘛?
我能!我能!我能!
姜明彩在心里吶喊著。
1993年7月,濰坊市奎文區私立聾兒康復學校正式成立。
學校開辦之初,只有高倩和史程程兩個學生,每個學生每月交100元錢,除了付租用教室的150元,就只剩50元了。這50元,也僅夠兩個學生的零花錢。其他花銷,就只有自掏腰包了。雖然如此,姜明彩卻活得充實而滿足。看著學校的那塊牌子,她就激動得想哭、想笑。她想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個農村女孩子,也能憑借自己的力量,辦起一所學校來。
兩個學生的進步是明顯的。她們已漸漸地可以進行日常會話了,更重要的是,她們已經極少再借助于手勢來表述了。
姜明彩以其教學成果證明了自己的實力,也贏得了聾兒家長們的信服。很快,她班上的學生增加到8個、12個。原先寬敞的教室顯得擁擠起來。小的四五歲,大的七八歲,10來個孩子,一下課就將教室鬧成了一鍋粥,把姜明彩也給吵得昏頭脹腦的。但她高興。
也有煩的時候。當某一個字音怎么也發不出來,她急,孩子也急。孩子急了,就罷學,就悶悶地低了頭,絕不看老師。看著孩子難受的模樣。姜明彩心軟了下來。再一遍遍地教,口形夸張著,指給孩子看,然后大聲地將音發出來。孩子跟著念,仍然沒有成功。這時,她會小心地說:“今天沒學會不要緊,明天咱們繼續學。只要有信心,就一定能學會。告訴老師,你有信心嗎?”孩子眼里噙了淚,大聲回答:“有—信—心!”第二天,果然就成功了。
學校紅紅火火地辦著。誰會想到教室會突然塌頂呢?而且,誰又會想到,找一間教室,竟會比建一棟大樓還要難呢?D
雨還在下。姜明彩又饑又渴,又冷又乏。總不回家也不是辦法呀!她掉轉頭,開始往家里騎。她幾乎是一步步蹭上樓梯的。推開門,母親正守著已睡熟的5個孩子。脫了雨衣,她一頭扎進母親懷里,傷心而無助地哭了。
母親摩挲著她濕漉漉的長發:“你這是何苦?要不,聽媽的話,就別干這學校了!”
姜明彩停住哭泣,站起身:“不,我明天還要找教室去。”
第二天,安頓好5個孩子,她又騎車出去。到下午,終于有了著落。一個高中同學的姐姐幫她在廿里堡街一個幼兒園租到了教室。她去看了,很滿意。教室挺寬敞,邊上還有一間,可以作她和學生們的寢室。更讓她滿意的是,她的學生們能常跟正常幼兒園的孩子們接觸,對提高他們的聽說能力,很有幫助。
姜明彩又有了新的教室。她的“聾兒康復學校”的牌子又可以堂堂正正地掛出來了。而且,與第一次掛牌相比,這次柳暗花明、猶如神助般的結局,更使她加深了這樣一種信念:只要充滿自心,不屈地尋找與奮爭,無論多么卑微的生命,都能散發出璀璨的光輝1作者后記:姜明彩并非孤軍奮戰。因為有一個人的目光始終都在關切地注視著她。這就是奎文區民政局長楊彬。楊彬是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聽說了姜明彩辦學的事。在和姜明彩長談一番之后,楊彬大為心動。她專門向區委、區政府作了匯報,一下子引起了所有領導的重視。無私奉獻,造福社會,應無條件支持。常委們的意見空前一致。
今年5月15日,楊彬來到區團委,介紹了姜明彩和她的學校,從書記到干事,都大受感動。小伙子李等豹騎上自行車直奔學校,采訪了姜明彩。文章很快就在市報和省內幾家報刊發表,引發了不小的反響。5月21日,助殘日。楊彬陪著市、區五大班子的有關領導視察了“聾兒康復學校”,孩子們為客人表演了詩朗頌和韻律操。楊彬介紹說,班上有個叫衛強的8歲聾童,在爺爺生日那天,突然清清楚楚地對爺爺說:“祝爺爺健康、長壽。”老人激動得老淚長流。8年了,他第一次聽見孫子叫他爺爺,他做夢都在期盼著這一天呵!
兩個月后,奎文區民政局和團委主辦了“姜明彩事跡報告會”,在濰坊市作巡回報告。一時間,姜明彩和她的聾兒康復學校成了社會關注的熱點。這一局面是姜明彩始料未及的。也因此,她萌生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借助社會的力量,擴大學校規模,在數年時間里,使學校在規模、設施與教學質量上都成為國內一流的聾兒康復之家。
當然會困難重重,但姜明彩已有了充分的信心。因為她的心里總在回響著一個倔犟的聲音:
我能!我能!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