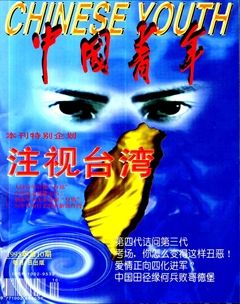高科技與市場
楊曉升 陳肇雄
陳肇雄,男,1961年9月出生,福建人,博士,研究員,中科院計算所譯機中心主任。1986年開始從事機器翻譯研究工作,首創了“智能機譯理論體系”,處于國內外先進水平,并推出了世界第一部袖珍電子翻譯機,兩年技術轉讓為國家創造直接效益860多萬美元,并簽訂了10年總額達2444萬美元的技術轉讓合同,在沒要國家資金投入的情況下,為國家建立了擁有9000多萬資產的科智公司,現任該公司總裁。曾獲中國杰出青年科學家和全國優秀發明企業家獎,并當選為中華全國青聯副主席
楊曉升:陳博士,記得你曾在中央電視臺的一次現場直播節目的“快譯通EC—863A”的演示中翻譯了這么一句話:“科學必須與市場相結合”,這句話是否是你在經歷實踐之后的肺腑之言?
陳肇雄:可以這么說,這句話的確是我的真切感受。
楊曉升:請談一下你對“科學必須與市場相結合”這句話的理解。
陳肇雄:在我看來,市場經濟說到底是效益與效率的競爭。“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如果不能為社會所應用,就無法發揮它對社會巨大的推動作用。就說計算機市場吧,這是全世界發展最快的市場,一個新產品出來,幾個月就被淘汰,你的拳頭產品剛剛站住腳,人家更棒的就將你壓下去了,中國的計算機該怎么做?國外的大公司每年有幾十億美元用于科研、開發,我們拼不過;美國每年可以吸引大批外國優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留學生,人才濟濟,這么比起來,在人才上,我們也沒有優勢。眼看著許多外國公司包干了我國的計算機市場,真讓人心急如焚!
楊曉升:就我國科學領域的現狀而言,你覺得我們現存的最大問題是什么,是缺少資金、還是缺少人才?
陳肇雄:不,最大的問題是缺少一個能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科研評價體系”。舊的“科研評價體系”是科研人員做出成果以后先鑒定,再一級一級評獎,然后再尋找生產實體,再把成果轉化為產品,這種程式,成果到市場轉化時間太長,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了!的確,說到科技投入,投入少這是事實,但政府一時半時還難以像發達國家那樣拿出那么多的錢來投入,這同樣是事實。可我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不是。江總書記講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可我們科技界眼下的現狀是投入時太平均用力、戰線拉得太長,傳統項目太多(有些項目雖有成果卻難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眼下的問題是迫切需要一個適應市場經濟的科研評價體系來引導,力爭把有限的資金和人力用到刀刃上。
楊曉升:那么,你對這個“適應市場經濟的科研評價體系”的具體設想是什么?
陳肇雄:這個體系包括學科和人才評價。學科包括基礎研究、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3個方面,也就是說在科研項目的選擇上,要考慮如何把有限的科研資源應用到理論上有創新并最有希望突破的基礎研究上,應用到具有產業化價值和良好市場前景的工程開發項目上,重點支持我國已有一定優勢和特色的技術領域,果斷放棄一些投資大而又長期趕不上國際先進水平的研究領域;而人才方面,需要培養一大批既有學術水平又有現代化管理能力的學術帶頭人。現代科技是一個團體項目,尤其是技術科學。因此,一位杰出的科學家,不能只在科研上杰出,在科技管理上也應該是杰出的,能夠根據市場變化果斷調整科研方向,并且要善于將科研成果轉化成生產力。
楊曉升:你說的要果斷放棄一些研究領域,但具體到某一個人或某一項目,恐怕操作起來有很大困難,不妨設身處地地想,這樣的事要攤到你自己頭上,你能坦然處之嗎?
陳肇雄:我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碰上這樣的事自然也不能免俗。實際上我也是在經歷過這樣的痛苦之后才走向成功的。1982年,我從華東工學院計算機系畢業后考上了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計算所高慶獅教授的研究生,開始搞的是第五代計算機核心語言“邏輯程序設計語言”的研究工作,而且已取得了不小的進展,我相信要沿著這一方向繼續研究下去,肯定會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但就在這個時候,高慶獅教授卻決定讓我去搞機器翻譯研究。
楊曉升:高教授為什么要讓你改變研究方向呢?
陳肇雄:一次,高教授出國訪問,發現很多中國學者由于語言障礙影響了學術交流,很多好的學術思想無法表達清楚,難以被外國同行接受。高教授回國后深有感觸地說:中國不是沒有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人和成果,而是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人的工作。因此,他決定安排一個研究生從事機器翻譯,讓機器幫助人消除語言障礙。在我之前,高教授曾讓兩名研究生從事這一研究,但遙遙無期的課題都只進行了一年半載就終止了。于是,高教授便把這一艱巨任務交給了我,這使我陷入了痛苦的選擇之中。要知道,一個普通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并能進行兩種語言自然翻譯,一般需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讓一臺機器像人那樣理解人的語言或文字,并將其翻譯成所需要的另一種語言或文字,其難度可想而知。這一研究課題自本世紀30年代被俄國人提出來之后,半個世紀都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被公認為世界高科技難題。
楊曉升:可你最終卻取得了成功、而且是世界性的成功。從你的經歷和實踐看,過去我們常說的那種獻身科學的“獻身”二字,其指向看來不只是獻身于自己所從事和研究的課題本身,還在于國家科學領域的全局。具體說,當你果斷放棄那種陳舊而且只能長期跟在別人后面的項目時,這本身也是一種獻身或奉獻。
陳肇雄:對科學家來說,獻身精神有時也是要講策略的,這就是我前面說到的一個杰出的科學家,要能夠根據市場變化果斷調整科研方向,并且要善于將科研成果轉化成生產力。
楊曉升:前不久,在廣東汕頭舉行的首屆國際華人物理學大會上,楊振寧教授曾說:“高科技戰場是中國超越發達國家的主戰場,也是最后的戰場。倘若不能在高科技戰場、高科技商品市場上搶占一席之地,中國將被拋于腦后。”他呼吁高層次的技術人才下海,他認為這些年來中國盡管已有不少人下海并對市場經濟的建立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這批人總體的技術素質不高,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當高科技逐漸滲透到我們日常的工作、生活時,對推動高科技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陳肇雄:我十分贊同楊振寧教授的這一觀點。近十幾年來,盡管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較快,但高科技的發展卻顯緩慢,彩電、冰箱等大都靠引進技術發展起來。長此以往地滿足于此,我們將何以趕超世界發達國家呢?不妨設想一下,2000年以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樣的,中國的經濟、政治、科技和文化將會在世界舞臺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關鍵一點,在于我們現階段在扶持什么樣的學科和項目。我們沒有多少機會和時間了,我們不能總是去拿別人的技術、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就我個人而言,現在的大部分時間仍是在搞科研,我想利用自己現有的條件去帶動一大批具有創造力和奉獻精神的年輕人,既而造就出能與發達國家競爭的高科技企業。我希望能與所有愿意投身高科技產業的人通力合作,共同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高科技企業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