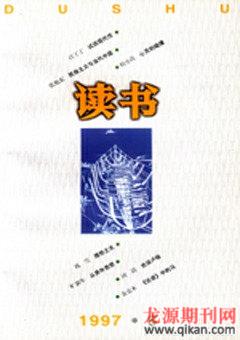也談盧梭
河 清
閑來偶讀《讀書》一九九六年七月號,崔之元先生的雄文《盧梭新論》的標題非常醒目。急急展閱之下,發現它像是為“盧梭舊論”而作的一篇辯護詞。所以,很樂意在這里插幾句嘴。
塔爾蒙(J.Talmon)的著作《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出版于一九五二年,從年代上說可能不算新論。但塔氏竟敢把極權主義與民主扯在一起,則不啻是新論,而且是奇談怪論異端邪說了。
公平地說,塔爾蒙雖然冒天下之不韙指認盧梭是“極權主義民主之祖”,但態度還是相當溫良恭儉讓的。而法國當代知名政治學家、《新觀察家》周刊專欄作家朱利亞爾(J.Julliard)則對盧梭就不那么客氣了,直言歷數“盧梭之錯”。
對于被尊為“民主合法性圣經”的《社會契約論》,朱利亞爾認之為一部“未完成”的書(盧梭自己也在開卷如是敬告讀者),“一部童話,一部哲學寓言”,并稱盧梭是“一個奇怪的謎團”:既左又右,既激進又溫和,既革命又保守,“盧梭什么都有點是,自由而任意,不忌怕自相矛盾”。
我拜讀盧梭這部名著,也吃驚于其語焉不詳、前言不搭后語之處,比比皆是。謹舉兩例。
第一,盧梭說:“從嚴格的字義上講,真正的民主從來都不存在,將來也決不會存在:大多數人來統治,少數人受統治,這有悖于自然秩序……。只有一個神明的人民,才是民主地自己統治自己。一種如此完美的政制,并不適合于人類。”但同時,盧梭又傾心贊美不止是“大多數人”、而且是全體人民自治的“民主”:“最高主權者只有當人民集合在一起時才能行事。”盧梭舉出古羅馬,即便有幾十萬公民之眾,也“很少有星期羅馬人民不集會的,甚至是一星期幾次……。全體人民都來到公共廣場,幾乎既是執政官又是公民”。盧梭一直神往古代的直接民主,曾有言:從孩提時代起,“我就自認是希臘人或羅馬人”。
同樣是出于對直接民主的摯愛,盧梭嚴厲摒斥代議制:“在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公民們都是親自動手,而不是用錢來做一切”,“最高主權是不可被代表的,正如最高主權之不能讓與。最高主權本質地在于公意,而公意則根本不可被代表……。顯然,在立法權上,人民是不可被代表的”。在盧梭看來,人民用錢請雇傭兵打仗,請代表“代議”政事,是公民們“懶惰”、“愛國熱情衰退”的結果,“一旦人民任請了代表,它就不再是自由的了”。所以盧梭很不屑于英國的代議制:英國人民一旦選舉國會議員完畢,依然是奴隸。
第二,盧梭對“自由”的論述,也多有含混之處。首先,在盧梭那里,“自由”是一個與“奴役”相對的概念。只要有一個人格化的“主人”(強者、富人等),便是不“自由”。擺脫其役使,便為“自由”。另外,盧梭描寫了一種人在野蠻狀態下的為所欲為的自由,即莊生筆下“牛馬四足”的境界,盧梭謂之“天然的自由”。但一旦人們集合為契約社會,人們就得把這種“天然自由”交出來,換以一種“公民的自由”。而這個換來的自由,是要大打折扣的。它得“服從”于一個抽象的“主人”:“服從人們自訂的法律即自由。”既要“服從”,就有那么點不“自由”的意思。盧梭自己也禁不住比喻:“法律的枷鎖”,“公共福祉的枷鎖”。“自由”也要戴上“枷鎖”!愿望當然美好:“每個人與集體結合在一塊,卻又只是服從他自己,并與從前一樣自由。”但要像“從前”一樣自由,終究是不可能的,既然“每個締約者都把自己所有的權利完全讓與給共同體,……置于公意的至高無上的領導下”,既然“最大多數人的聲音始終約束著所有其他(少數)人”。盧梭說到這里,也感到有點問題,便假托一問:“人們會問,怎么一個人被迫去服從一些不是他自己的意志而仍然可以是自由呢?”高明的盧梭來了個答非所問:“我要回答是問題的提法不對。公民要服從所有的法律,哪怕是他反對而又通過的法律……正是通過公意他們才成為公民和自由”。所以,盧梭的“自由”,大有某種強制性意味,很不那么“自由”。
盧梭對“公意”與“眾意”的區別,實際上也并不那么清楚。既然“公意只著眼于公共利益,而眾意則著眼于私人利益”,那么,“眾意”怎么能經過“正負相抵”、七扣八除之后又變為“公意”?原文直譯是:“從這些個別意志中去掉最相互抵銷和最不相互抵銷的意志,剩下的便是公意,盡管有那么多的差別”。盡管盧梭給“相互抵銷”一詞加了注,但邏輯仍然不清。尤其人們應當聯想到,盧梭始終將“公意”截然區別于“個別意志”、“個別行為”、“個別利益”。一旦“公意”的形成中摻有一丁點“個別”性的東西,“公意”便宣告毀壞。凡俗的“個別意志”,任怎樣加減乘除,也不會產生神圣的“公意”。
盧梭說對“不服從公意的人”要“迫使他自由”,崔先生為賢者諱,把“迫使”之句“更貼切地”改為“使之能夠自由”。但迫使(forcer)就是迫使,就是用“力”(force)強迫使其然。證之于盧文全句:“任何拒絕服從公意的人,全體將強制(contraindre)他服從:意思無非是人們將迫使他自由。”又是“強制”,又是“迫使”,公意的面目昭然畢現。后代形形色色的盧梭主義者,更是把盧梭的公意學說推向一種狂熱的公意崇拜。羅伯斯庇爾,這位盧梭的狂熱信徒,正是以“公意”的名義,“使”成千上萬與他“想得不一樣的人”在斷頭臺上成為“自由”,又“使”幾十萬忠于國王的旺代省農民橫尸遍野……。真是怎一個“使”字了得!
那么,在盧梭的公意或最高主權的絕對領導下,個人究竟享有多少自由和權利?按照今天自由主義的觀念,個人生而享有生命、財產之安全等基本人權。但在盧梭那里,個人的財產乃至生命權,恰恰都是“轉讓”出去給了最高主權者的:“國家通過社會契約是所有其成員財產的主人”,“個體們沒有任何權利掌握他們的生命,……當主君(prince)對他說:你死了對國家合適,那他就得死”!
縱觀當今西方自由主義政制,除了在形式上保留“人民最高主權”的口號,根本沒有兌現盧梭設想的民主,實際上倒是不動聲色地實踐了孟德斯鳩的自由主義學說。相比而言,盧梭不僅高揚“人民最高主權”,而且主張人民自己行使主權(本義的民主),孟德斯鳩則只承認“人民最高主權”,但不同意人民自己行使主權,而是讓一些人民的代表代為議政;盧梭主張每個公民親自參與公共事務,孟德斯鳩則認為人民“不宜于討論國家大事”,這件事應當讓人民的代表去干;盧梭認為人民最高主權是“不可讓與”并“不可分裂”的,孟德斯鳩則恰恰相反,不僅人民可以把最高主權“讓與”給其代表,而且最高主權也可“分裂”為立法、執法和司法。
盧梭的思想,混亂中透出一種激進和烏托邦的特征。孟德斯鳩則顯得溫和和現實,體現了一種真正的自由主義。崔先生使盡解數要給盧梭戴上一頂“自由主義”的帽子,但這頂帽子真正地應該屬于孟德斯鳩。
英國哲人羅素更語出驚人:“希特勒是盧梭的直接結果,丘吉爾是孟德斯鳩的直接結果”。
丙子孟冬于杭州中國美術學院正名書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