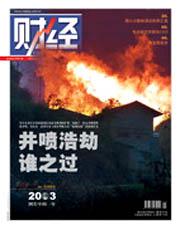川投保:與官司不期而遇
董 沛
一起無奈的官司
1999年5月26日,記者到達(dá)成都的第三天,伍幼榮又一次無奈地坐到了被告席上。開庭前,他告訴記者說,也許這個案子最能反映出擔(dān)保業(yè)的現(xiàn)狀。
事情起于去年年底。身為四川省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投資擔(dān)保公司(以下簡稱“川投保”)總經(jīng)理的伍幼榮是在毫無準(zhǔn)備的情況下坐上被告席的。
四川廣漢東嘉集團(tuán)是這起官司的原告方。1996年,名為集體企業(yè)實(shí)為民營企業(yè)的東嘉集團(tuán)看上了成都市一環(huán)路內(nèi)的100多畝地,而當(dāng)時該地皮的主人中國機(jī)械基礎(chǔ)建公司成都分公司正面臨困境。于是通過洽談,雙方達(dá)成兼并協(xié)議,東嘉集團(tuán)兼并了機(jī)械基礎(chǔ)建成都分公司,并為此陸續(xù)投入了3000多萬元的兼并費(fèi)用。
兼并不久,風(fēng)波突起。由于中國機(jī)械基礎(chǔ)建公司上級主管部門機(jī)械部機(jī)構(gòu)改革,以及成都分公司職工對民營企業(yè)管理方式的不適應(yīng)等多種原因,分公司職工強(qiáng)烈要求解除兼并。
四川省百般調(diào)解,最終雙方同意解除兼并協(xié)議,但東嘉集團(tuán)提出443萬元的損失要由有關(guān)部門予以補(bǔ)償,并要求,如果資金不能到位,必須提供擔(dān)保。
1998年10月30日,四川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投資擔(dān)保公司副總經(jīng)理王明生被省上有關(guān)部門一個電話找去。去時,除了知道要帶上公章外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在川投保還未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時,公司的公章就已蓋到了解除兼并協(xié)議書上。與此相應(yīng)的是公司要對此443萬元所引發(fā)的一切問題負(fù)責(zé),甚至包括發(fā)生糾紛所需負(fù)擔(dān)的訴訟費(fèi)。
機(jī)械基礎(chǔ)建成都分公司屬于中央企業(yè),而東嘉集團(tuán)是廣漢的地方企業(yè),由于主管方的不同,問題也就隨之出現(xiàn)。按解除兼并協(xié)議書規(guī)定,443萬元必須在當(dāng)年12月31日以前到位,而實(shí)際上由于種種原因,錢并沒有按時劃撥。直到1999年1月28日,川投保才在接到省經(jīng)貿(mào)委委托書的情況下,進(jìn)行了代償。2月3日,錢到了東嘉集團(tuán)的賬戶上。
事情并沒有川投保想像的那樣就此結(jié)束。1999年4月4日,伍幼榮接到成都市錦江區(qū)法院的起訴書,東嘉集團(tuán)以延遲付款為由將擔(dān)保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擔(dān)保公司賠償日萬分之五的滯納金和月千分之十的利息損失,共10多萬元。
面對這樣的官司,伍幼榮一肚子的委屈,擔(dān)保本就不是公司愿意作的,也沒有一分錢的保費(fèi)收入,有的只是責(zé)任。
法庭上,伍幼榮請對方一定要理解擔(dān)保公司為政府行為所作出的犧牲。最后案件通過法庭調(diào)解,以擔(dān)保公司賠償5萬元了事。東嘉集團(tuán)原本希望擔(dān)保公司再負(fù)擔(dān)4000多元的訴訟費(fèi)用,伍幼榮堅(jiān)持不肯出,原因很簡單卻也透著無奈——上面只給了5萬元的權(quán)限,多一分錢回去都沒法交賬。
在離開法院的路上,伍幼榮說,這樣的結(jié)果從法律上講我認(rèn)賬,但對擔(dān)保公司,這是不公正的。
“一舉多得”的起步
其實(shí),早在四川省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投資擔(dān)保公司籌備時,伍幼榮就已明白這并不是什么好干的行當(dāng)。
在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投資擔(dān)保公司成立以前,企業(yè)技改資金用的是“湊拼盤”的辦法,即企業(yè)自籌一部分,銀行貸款一部分,政府劃撥一部分。為此,每年四川省財(cái)政都要安排一筆預(yù)算資金用于中小企業(yè)技改和新產(chǎn)品推廣項(xiàng)目。剛開始比較少,后來逐漸從二三千萬上升到1994年的8000多萬。這樣做的最大危害在于資金通過財(cái)政一級一級下?lián)芎螅髽I(yè)會認(rèn)為這是財(cái)政撥款,不需要還的。資金使用沒有效率,財(cái)政負(fù)擔(dān)也沒有盡頭。
1994年3月,中國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投資擔(dān)保公司正式開業(yè),成為中國第一家擔(dān)保公司。在該公司1993年4月開始籌辦及1994年1月試營業(yè)時,四川省有關(guān)部門就進(jìn)行了全面的考察,結(jié)論是,投資擔(dān)保公司這一形式能有效地解決技改資金回收的問題。
將每年通過財(cái)政劃撥的技改資金集中起來組建一家公司,每年投一筆錢進(jìn)去,三四年的時間公司規(guī)模就可以做大,資金可以保值增值。原本由財(cái)政出面劃撥的技改資金改由公司出面以投資的形式下發(fā),或以擔(dān)保貸款的形式提供,還有個放大效應(yīng)。由于錢是以公司的名義投出去的,是企業(yè)行為,就不存在國家財(cái)政劃撥的問題,因此所投資金也可以收得回來。
看上去是一舉多得的辦法。
于是,有關(guān)方面決定在四川也開一家類似于中國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投資擔(dān)保公司的川投保,并進(jìn)行了相應(yīng)的籌備工作。
1994年1月,當(dāng)時在省經(jīng)貿(mào)委企管處任處長的伍幼榮接受了川投保總經(jīng)理的任命。6月30日,一系列的公司成立報(bào)批文件才送到工商局,而工商局也特事特辦,在一天內(nèi)為這家新創(chuàng)辦的公司辦好了一切手續(xù)。
7月1日,四川省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投資擔(dān)保公司正式成立。其上級主管是四川省經(jīng)貿(mào)委和四川省財(cái)政廳,公司人員主要由這兩家政府部門內(nèi)部調(diào)配。從公司成立開始,省財(cái)政便開始將用于技改的資金直接劃撥給川投保,每年約一個億左右,到1998年停止劃撥時,川投保已擁有資產(chǎn)4.3億元。
風(fēng)險無從回避
伍幼榮最頭痛的問題是,投資出去的錢回不來。
川投保現(xiàn)有的4.3億元資金幾乎全在省內(nèi)各企業(yè)使用,由于企業(yè)內(nèi)部關(guān)系復(fù)雜,錢很難還回來。
伍幼榮打了個比方:有輕工企業(yè)需要資金,它必須先向輕工局打報(bào)告,輕工局再向省財(cái)政廳和省經(jīng)貿(mào)委打報(bào)告,再向上由分管副省長簽字,最后到投資擔(dān)保公司,由公司撥給資金。這種運(yùn)作使企業(yè)很難將資金來源和財(cái)政撥款分開,很多企業(yè)就此認(rèn)為錢是財(cái)政撥的,有錢也不還。
伍幼榮頭痛的第二個問題是擔(dān)保風(fēng)險太大,一旦發(fā)生糾紛,銀行首先找的是擔(dān)保公司,而不是債務(wù)人。
在伍幼榮的心里,有這樣一筆賬:幾年擔(dān)保做下來,保費(fèi)收入400多萬,但代償卻達(dá)1700多萬元。
川投保為一家娛樂公司在銀行貸了款,當(dāng)銀行發(fā)現(xiàn)娛樂公司沒有償還能力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法院凍結(jié)了川投保的銀行賬戶。在此之前,銀行從未找娛樂公司催促還款。后來川投保只好代償了事。
在川投保幾年的擔(dān)保運(yùn)作過程中,類似這樣的事常有發(fā)生,川投保自身的銀行賬戶始終在風(fēng)雨中飄搖。
伍幼榮認(rèn)為,現(xiàn)行的《擔(dān)保法》維護(hù)的實(shí)際是銀行的利益,并沒有考慮到擔(dān)保公司的權(quán)益。而在實(shí)際運(yùn)作中,雙方的合同上什么條款都是銀行說了算,擔(dān)保公司一個字都不能動。
與銀行擠壓相對應(yīng),很多企業(yè)法人代表的觀念是,自己能躲起來,就一定要躲起來,風(fēng)險反正由擔(dān)保公司擔(dān)著。
一個賠錢的等式
面對投資和擔(dān)保過程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伍幼榮自己總結(jié)了一個公式:企業(yè)法人素質(zhì)不高+行政指令=賠錢。
公式中“行政指令”這一項(xiàng)對川投保的未來起著決定作用。
川投保的上級主管部門是省經(jīng)貿(mào)委和省財(cái)政廳,川投保進(jìn)個人都需兩家主管部門共同批準(zhǔn)。川投保在實(shí)際經(jīng)營中所投的任意一筆資產(chǎn)、所作的任意一起擔(dān)保,都需報(bào)上級批準(zhǔn)。而反過來,上邊指派給川投保的任意一筆業(yè)務(wù),都必須無條件接受下來。
伍幼榮戲稱自己的公司有三種身份:
第一種身份是經(jīng)貿(mào)委的出納員——只要省經(jīng)貿(mào)委的文件一到,該拿的錢就要拿出來;
第二種身份是財(cái)政廳的討債隊(duì)——蓋了擔(dān)保公章的貸款多半得去討,很多時候公司的三個老總一塊出去,到一個地方留下一個人,往往十天半個月都不見人回來;
第三種身份是政府的消防員——哪兒的企業(yè)不行了,公司就要趕去救火,拿出錢來往里投。
有時政府開一個會,擔(dān)保公司沒參加,但會后要求投資擔(dān)保的會議紀(jì)要就已經(jīng)來了。而由此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讓川投保哭笑不得:只要是政府會議上決定要求公司投資擔(dān)保的項(xiàng)目,企業(yè)來辦手續(xù)的人都堂堂正正、理直氣壯。原因很簡單,是上邊下文讓你給我錢,你就得給我。有一次,一家企業(yè)甚至只帶了個銀行賬號來,就要求川投保劃錢。
省政府的賓館要改造,有關(guān)部門作出決定由川投保擔(dān)保貸款2000萬元;一家明知道還不起貸款的鋼廠只因省長辦公會決定了,也就必須為其3000萬元貸款進(jìn)行擔(dān)保……
如此種種,都是川投保——一家走在風(fēng)險邊緣的金融公司每天都可能遇到的事情。不少企業(yè)是拿了有關(guān)部門文件前來辦手續(xù)的時候,川投保才知道需要給這家企業(yè)投資或者擔(dān)保的。
與擔(dān)保業(yè)務(wù)幾年時間收取保費(fèi)收入400多萬元、賠償1700多萬元相伴出現(xiàn)的另一現(xiàn)狀是,由政府指令所作的擔(dān)保很少有項(xiàng)目評審,也很少有“反擔(dān)保”,同時也很少有付擔(dān)保金的。
問及政府指令擔(dān)保中有幾成賠錢的,伍幼榮的回答是不好說,你自己想去吧。他開玩笑說自己的公司也算得上是蠟燭,點(diǎn)燃自己,照亮了別人。
今年,為躲避擔(dān)保帶來的高風(fēng)險,川投保基本上停了擔(dān)保業(yè)務(wù)。
明天會怎樣?
最近,為推動中小企業(yè)服務(wù)體系的建立,改善中小企業(yè)的生存和發(fā)展環(huán)境,解決中小企業(yè)融資難的問題,四川省正準(zhǔn)備搞一個中小企業(yè)擔(dān)保基金,初步打算是省財(cái)政拿出5000萬元,各地區(qū)配套5000萬元,企業(yè)自籌5000萬元,共1.5億元作為基金存入銀行,可按1:5的比例進(jìn)行擔(dān)保。具體運(yùn)作是在川投保加掛一塊中小企業(yè)信用再擔(dān)保公司的牌子,采用一套機(jī)構(gòu)、兩塊牌子的方法。
對此,川投保并不積極。
伍幼榮說,從大局來講,這當(dāng)然是件好事,隨著銀行貸款發(fā)生變化,擔(dān)保這一中介的產(chǎn)生是必然的,很多中小企業(yè)只要有些資金就能活下去。但現(xiàn)有的環(huán)境無法使擔(dān)保公司規(guī)避風(fēng)險,1.5億元可擔(dān)保的金額達(dá)7.5億元,只要有20%的企業(yè)還不了錢,擔(dān)保公司就得倒閉。而現(xiàn)有的情況是可能出現(xiàn)問題的企業(yè)遠(yuǎn)遠(yuǎn)超過這個比例。
伍幼榮的意見是,如果要做,就必須實(shí)行政策性指導(dǎo),采取市場運(yùn)作的辦法。作為擔(dān)保公司的法人代表,其主要任務(wù)是對公司資產(chǎn)負(fù)責(zé)。比如說,政府提供給擔(dān)保公司20家企業(yè),擔(dān)保公司要有一票否決權(quán),最終決定是否進(jìn)行擔(dān)保的是擔(dān)保公司,而不是政府的有關(guān)部門。
就四川省的具體情況,伍幼榮認(rèn)為上面這一點(diǎn)達(dá)不到的話,擔(dān)保做上二年,公司就可能損失40%~50%,也就是兩三個億左右。這樣的損失,哪家金融機(jī)構(gòu)擔(dān)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