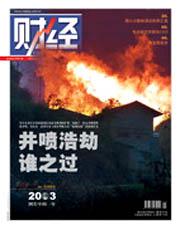當金錢的盛宴曲終人散
王 爍
流產的“第一”和開創的“第一”
1999年8月27日,上海拍賣行取消了原訂于當天下午2點30分舉行的一場拍賣。
這次拍賣的標的是滬市上市公司棱光實業(代碼600629)的4400萬股法人股——占到了棱光實業總股權的29%。它的所有者、棱光實業第一大股東恒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以其作質押,向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借款5000萬元人民幣,逾期未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委托上海拍賣行拍賣這批股權,以清償債務。
顯而易見,此次拍賣一旦獲得成功,棱光實業的第一大股東將會易主。這將創下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史上又一個“第一”——由于第一大股東借款逾期未還,所質押上市公司股份被拍賣。
然而,“我們決定暫緩拍賣”。上海拍賣行副總經理法勇生說,“重拍時間還沒有定。”法勇生不愿明示暫緩拍賣的原因,但是知情人說,至8月26日下午,未有一人按拍賣規則交來200萬元訂金。這實際上已經注定了此次拍賣流產的命運。
沒有人對成為棱光實業——盡管是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感興趣。
雖然拍賣未果,棱光實業還是創下了一個“第一”。就在8月27日當天,棱光實業發布公布稱,因大股東恒通集團——同時也是大債務人——將資本金從5.2億元減至1.9億元,棱光實業正式向恒通集團主張權利,要求清償其對棱光的負債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
據說,因大股東減資而主張權利,這在證券市場上也是第一次。
棱光為大股東擔保擔得苦不堪言
沒有人參加競拍的原因,可以從當天棱光實業公布的一系列信息中看得分明。
據棱光最新披露,該公司又為7樁訟案所纏身,標的總值達1.1億元人民幣和近160萬美元。其中絕大多數訴訟,都起因于棱光為大股東恒通集團的子公司和關聯公司作的貸款擔保。
這不過是冰山一角。截止到8月27日,棱光對外擔保總額——只是已核清的部分——已達4.11億元,其中3.5億元左右保的是恒通及其關聯公司;而因擔保引發的訴訟已有十數起之多。被法院查封資產和銀行賬戶,在棱光已不是新鮮事。棱光的基本賬戶至今仍被法院查封。除此之外,棱光有超過3億元的資金被恒通所占用。
——棱光實業的凈資產只有2.33億元。
“棱光必須對恒通主張權利。”棱光實業現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吳永強對記者說。此時,吳正坐在上海市天平路91弄一幢4層小樓的辦公室里——眼下這處房產也前景不妙。由于恒通未能清償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1500萬元的借款,法院凍結了作為擔保人的棱光公司名下的這處辦公用房,現已進入評估拍賣程序。
據不完全統計,棱光實業因為恒通所負的擔保責任而被法院凍結的資產,還涉及國家電力債券、機器設備、原材料、庫存商品等,所擁有的上海恒通電氣公司、上海棱光酵母制品有限公司等資產和股權也遭查封——棱光已經轉不動了。
棱光究竟為恒通作過多少擔保?吳永強至今仍無法給出確切的數字,3.5億元“只能說是大致”。
面相樸實的吳永強是棱光的老人。1994年4月,恒通通過收購當時棱光實業的第一大股東上海建筑材料(集團)總公司所持有的1200萬股國家股,成為棱光的第一大股東,吳董事長兼總經理變成了副總經理。大約一年后,他重返總經理的位置。棱光董事長一席則長時間由恒通總裁兼任,這使棱光為恒通貸款作擔保變得相當容易——甚至是相當隨意。當時銀行對擔保的要求也不高,有公司的圖章就行,不須董事會決議。用吳永強的話說,擔保是如此地多,以至于在他今年2月以來清查的時候,驚訝地發現許多擔保不要說沒有經過董事會研究,甚至董事會就根本不知道。
即便如此,吳永強對為恒通所作擔保的潛在風險是早有了解的。據吳永強說,他曾向恒通派來的董事長指出這樣下去的危險后果。對方的回答是:“如果兩年后(兩家公司)還這樣,那不就完了么?”
“結果,他說中了。”吳永強對記者說。一份由棱光實業董事會委托作出的法律意見書,對恒通與棱光的關系的法律后果作出如此評價:“由于棱光實業對恒通集團的巨額債權無任何保證措施,根本無法實現。如果恒通集團和下屬子公司破產,棱光實業也必然隨之而破產。”
拋棄“利潤奶牛”也就割斷了恒通與棱光的臍帶
8月27日的主張權利公告,可以看成是棱光公開表現出與恒通決裂的一個姿態。不過,裂痕在更早的時候就出現了。
1999年中報顯示,棱光實業上半年主營業務收入為1403萬元,凈利潤為-979.56萬元。這是棱光實業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更可憂的是,棱光無力尋求有盈利能力的主業。原主業半導體材料早已經接近停產狀態。
數年來,棱光的利潤主要來自于旗下位于珠海的恒通電能儀表公司。恒通電能儀表公司原為恒通集團全資子公司,1995年12月以1.6億元的價格轉讓給棱光實業。恒通與棱光同時簽訂委托代管協議,電表公司的運營委托恒通管理,恒通承諾提供2193萬元的年利潤,且每年有20%的增長。雙方還約定,如果利潤低于2193萬元,恒通必須回購電表公司。
這是一份奇怪的合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給棱光制造“利潤奶牛”,以保證凈資產收益率水平。
這頭“奶牛”在頭兩年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1996、1997兩年,電能儀表公司的凈利潤是2388.80萬元及2202.76萬元,而同期棱光實業的凈利潤是1614萬元和2214萬元。恒通電能儀表公司的利潤保證了棱光實業1996、1997兩年12.16%和10.98%的凈資產收益率。這意味著配股資格。
恒通方面也為養這頭“奶牛”付出了沉重代價。恒通高層人士對記者說,恒通電能儀表公司根本無力達到每年2193萬元并且年遞增20%的利潤水平,差額部分只好由恒通集團貼補,每年總有數百萬元。
吳永強表示,他不了解恒通貼補利潤一事。不過,1998年底,他與棱光實業監事長一起到珠海考察了恒通電能儀表廠。他們的結論是,當年電表廠不可能完成2193萬元的保底利潤。這一判斷后來被證明是準確的——電表廠的當年利潤是1200萬元。當然,彼時已山窮水盡的恒通1998年也無論如何沒有能力補貼進900萬元,也不可能注入有足夠盈利能力的項目。
對棱光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消息。配股資格怎么辦?
1998年11月22日,棱光董事會會議通過決議,要求恒通回購電表廠。一個月后,恒通集團以2.4億元的價格回購恒通電能儀表。據吳永強介紹,除了含1.6億元的原價格外,2.4億元中還包括棱光歷年的投入——棱光把歷年的利潤重又投入了電表廠。恒通以資產折抵的方式付了1.2億元,尚欠1.2億元。
憑著這筆收入,棱光1998年實現收入3018萬元。配股資格保住了。這是電表廠這頭“奶牛”為棱光擠出的最后一滴奶。殺掉了這頭“奶牛”,棱光就此喪失了利潤源泉;它的另一個后果是,割斷了與大股東恒通集團之間賴以維系為一體的臍帶。
在今年2月4日的棱光董事會會議上,吳永強“不情愿”地以總經理的身份被任命為兼董事長。會后,他與恒通集團董事長楊博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
吳:“你讓我當董事長是會后悔的。”
楊:“為什么?是不是擔保的事?”
楊博猜對了。吳永強擔任董事長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理與恒通的擔保及債權關系。4月間,清理大致有了結果,6月間開始在媒介上公布,8月底正式向恒通主張權利。從旁觀者眼中看來,一系列與恒通劃清界限的步驟有條不紊。“主張權利有什么效果是一回事,主張不主張又是一回事。”吳永強說。
吳永強對上海拍賣行拍賣棱光法人股原本是有期待的。他希望看到有實力的機構拍得股權,替換恒通成為棱光的大股東——畢竟,棱光今年要保住配股資格,惟一的希望是資產重組,這只有在新的大股東進入的情況下才可能。
“棱光比那些ST情況還是要好一些。”吳永強說。但他也承認,“如果恒通破產(這意味著棱光對恒通的債權無法收回,而為恒通所作的擔保就要兌現),就會拉著棱光一起破產,這種可能性沒有排除。”
恒通像煙云一樣的興衰
8月27日棱光股權拍賣流產,讓恒通集團董事長楊博長舒了一口氣——至少在下一次拍賣成功前,恒通還是棱光的第一大股東。這就是喘息的時間。
換句話說,如果不與棱光綁在一起,恒通就沒了希望——除了上市公司這個殼資源外,面對19億元債務以及由此而生的200多起訴訟,恒通可打的牌太少了。兩塊主要的資產——位于上海市淮海東路上的恒積大廈和位于浦東的大塊地產已經分別作過多次抵押。作為董事長,楊博日常辦公的恒積大廈投入使用已有一段時間,卻尚未正式宣布竣工。據說是因為那樣就要開始提折舊。“稍微有點價值的資產都查封了”。知情人說。
風水輪流轉。失意的恒通有過煊赫一時的過去。
——1991年創設的恒通是珠海第一家股份制企業。發起人包括寶鋼、攀鋼、東風汽車公司、深圳建材集團、交通銀行深圳分行等知名大中型企業。
——1992年7月,創立不到一年的恒通第一家通過全國證券自動報價系統(STAQ)上市,發行3000萬股法人股,集資1.2億元。
——1992年、1993年,股本高速擴張的恒通連續兩年每股收益達到0.60元。1993年底,經過在全國證券自動報價系統上的第二次融資及實施其他擴股方案后,兩年間恒通股本從1800萬元擴展到1.93億元,凈資產達到6億元,總資產超過20億元,成為當時國內頗為知名的新興企業。
這就是恒通的頂點。事后看來,恒通的“奇跡”要歸功于時勢而不是經營天才。
恒通集團1998年年報至今未出,原因不得而知。恒通總體上資產和負債的細節幾乎成了個謎。現在能找到的最新數據是1997年的,顯示恒通總資產20億元,凈資產5億元。但熟悉恒通的人都認為這是“老皇歷”,實際情況要糟得多——只要看看一筆筆貸款還不了、一起起官司打不完的狀況就有數了——盡管這只能算是猜測。
恒通的情形有多壞,有一個故事可以佐證。1997年底,某證券公司看上了恒通——恒通不是很好嗎?自己是STAQ上市公司,還控股一家滬市上市公司。于是在法人股市場上通過幾家子公司進行收購,花了1.5億元收購了3200萬股,掌握了恒通15%左右的股權;然后準備入主恒通。條件談完了,甚至證券公司的老總親自到恒通開了主要干部會議,講了一通勵精圖治的話,宣布了董事長、總裁的任命。第二天,該證券公司對恒通的調研報告出來了。老總看了以后,給楊博打了一個電話:“我們不干了”。
在恒通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重組之后,漸漸有了一個傳說:對重組方,楊博從不說恒通是什么樣子的,他問對方恒通“是什么樣子”的話愿意進行重組,然后就提供一個“那個樣子”的恒通情況——希望這只是一個笑話。
“這不是做企業的辦法”
恒通的主業是什么,人們很難說得清楚。打開恒通1992年的年報,人們就可以發現當時成立僅一年時間的恒通,“主要業務”已經五花八門——房地產、航運、通訊、高科技(電表和生物制藥)、商貿、文化旅游(“著名”的謝晉—恒通影視公司是其旗下的全資子公司),等等。
“我們曾經想過要有三個支柱:產業支柱、金融支柱……還有一個什么來著?……呵,是綜合商社。”在恒積大廈15層的辦公室里,楊博告訴記者。
這種“什么都干”的作風一直延續到恒通筋疲力盡為止。直到1997年,恒通情況已經很壞了,年開辦費仍是近7000萬元。事實證明,這根本經不起日漸嚴酷的外部環境的考驗。恒通自1994年開始走上漫長而痛苦的下坡路,當年利潤比上年下降了60%;1995年利潤又比上年下降了60%,而這兩年間公司總資產以每年4億元的規模增長,負債增長顯然過快。1996年、1997年分別虧損3400萬元和7100萬元。恒通1997年度經營工作報告承認,“集團出現了嚴重的支付困難……問題成堆,積重難返,回天無力”;另一份報告則預報了來年的情況:“既無力量發展新的項目,亦無力量保證資金的銜接”。
“多元化”戰略的失誤和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是恒通故事的全部。1993年底,吳永強考察了位于珠海的恒通電能儀表廠。他震驚于看到的情景。“電表廠的總經理只要說需要資金,恒通馬上就給”。吳永強回憶,“不要董事會決議,甚至不須任何程序”。當時,國有企業里成長起來的吳永強覺得這是決策機制靈活迅速。現在,他認為,這說明恒通沒有基本的財務管理制度和決策程序。“還有,我一直覺得這個電表廠太豪華。”吳永強說。
知情人說,恒通“鋪攤子”的方式一般是這樣展開的:先出資成立一家公司,過一段時間把資金大半拿走去做另一家公司;前一家公司要發展業務,就得憑剩下的那些錢再去貸款,于是周而復始。“這不是做企業的辦法,更像是搞社團”。一位熟悉楊博的人嘆息——在下海之前,楊博曾是光明日報社上海金三角俱樂部的組織者之一,主要工作是負責與企業家們的聯絡。自1991年創立恒通以來,他一直擔任恒通董事長。
恒通其實并非哪人哪家的公司,除了楊博控制的珠海百士公司占股10%,其他的股東股權都在10%以下。這其實是恒通成立時有意的設計,目的是盡可能少地帶入國企股東的習氣——股權比例不大,干預的積極性自然不高——彼時的中國對董事會受托責任、法人治理結構這些道理還頗為生疏。雄心勃勃的恒通管理層藉分散的股權結構確保“自主權”,結果是犯了錯誤也無從制約。
現在楊博和恒通的管理層悲嘆的是股權分散的另一種后果:恒通垮的時候,也沒有股東肯出面重組——為了10%的股權?不值得。來自外部的重組也有,但最后被證明是一場鬧劇(參見附文)。
拍賣能不能永遠流產?
楊博承認,對于棱光,恒通“利用得比較充分”。他的解釋是,恒通“從上到下”都認為,既然恒通通過“貼補”電表廠利潤為棱光的報表作出巨大貢獻,讓棱光為恒通作擔保或占用點棱光的資金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吳永強則對此不敢茍同:“這種對上市公司和大股東之間關系的理解是不是偏了一些?”
回首棱光與恒通在資本市場上的遇合,吳永強總結不出太多的經驗。他反復說的一句話是:“作為上市公司,搞資產重組,關鍵還是對象的選擇。”他希望有關部門能搞一個大股東審查制度。
事到如今,在楊博眼中,恒通的出路只有一條:與棱光合并。不用想就知道,這個計劃對于恒通能擺得出來的籌碼來說,實在過于宏偉。但是熟悉楊博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句口頭禪:“永不言敗”。本刊同行的一位攝影記者曾為他拍過1992年恒通年報的照片,此次臨別的時候,楊博緊握攝影記者的手:“希望明年你還能來拍照。”
楊博只能期待——那4400萬股棱光法人股永遠拍賣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