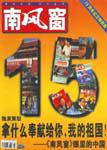堅(jiān)定的心,冷靜的腦
感受美國
圣莫尼卡是大洛杉磯地區(qū)一個(gè)緊鄰太平洋的海濱城市,一年四季游人不斷。雖然早春的海風(fēng)還有些寒意,但沙灘上已經(jīng)躺著不少老老少少,盡情享受加里弗尼亞的迷人陽光。一對(duì)對(duì)只穿著T恤、腳踏滑板的男男女女,在沿海小路上無憂無慮地穿行,自由自在地大喊大叫,那份單純和快樂,讓我有一種久違的感覺。
說真的,我有些嫉妒。比起大洋對(duì)面那塊已耕耘了幾千年、不堪人口重負(fù)、而且歷史上每隔一段時(shí)間就要來一場兵荒馬亂的土地,這里的確是一塊新大陸,一塊更年輕、更活潑的新大陸。我相信每一位剛剛來到美國的中國人都有和我類似的體會(huì)。站在海邊,極目遠(yuǎn)眺,天水一線,浮想聯(lián)翩。記不得誰講過,"美國在二戰(zhàn)中靠生產(chǎn)更多的大炮打敗了德國,在冷戰(zhàn)中靠生產(chǎn)更多的黃油打敗了蘇聯(lián)"。今天,美國又在生產(chǎn)什么呢?信息高速公路,太空探測,華爾街神話與克林頓盛世,好萊塢與NBA,對(duì)了,最新的《紐約客》雜志說將在5~10年內(nèi)攻克癌癥……除了這些,還有什么呢?
我不知道優(yōu)越是不是一定帶來譖妄,但顯而易見的是,美國正試圖在國際事務(wù)中擁有比冷戰(zhàn)時(shí)更大、也更具支配性的話語權(quán)利,它正努力為世界生產(chǎn)一套"新秩序"。在它每年發(fā)表的人權(quán)報(bào)告中,指責(zé)的國家越來越多,內(nèi)容也越來越細(xì)。人道誠可貴,自由價(jià)亦高,但當(dāng)你認(rèn)為只有自己"得道",動(dòng)不動(dòng)就要"替天行道",甚至還要用炸彈去"傳道布道"時(shí),人道正在經(jīng)受另一種嘲諷。有人把科索沃戰(zhàn)爭拔高到"二戰(zhàn)后第一場為了人道目標(biāo)的戰(zhàn)爭"、"從此改變了戰(zhàn)爭的性質(zhì)"的高度,"人道"在這里已不僅是誤用,更是對(duì)戰(zhàn)火冤魂的褻瀆。
我久久地憑海而望,我曾樂觀地相信,只要大洋兩邊的兩雙手握在了一起,它們就不會(huì)再分開。從某種角度看,今天這兩雙手是越握越緊了:截至1999年,美方已在華投資了28626個(gè)項(xiàng)目,總投資金額524億美元。1999年,雙邊貿(mào)易額近615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第四大貿(mào)易國,美國更是中國第二大貿(mào)易國。每年,有超過100萬的中國人和美國人越過太平洋相互往來,雙方合作的領(lǐng)域和程度不斷在開拓深化。就在幾天前,在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分校舉行的一場中美對(duì)話會(huì)上,我聽到美中商會(huì)會(huì)長坎普又在大聲疾呼國會(huì)應(yīng)盡快通過支持中國加入WTO的文件,并把中美間的此次協(xié)議比作"中美建交后美國對(duì)中國最具深遠(yuǎn)正面影響的一個(gè)范例"。在他看來,通過WTO協(xié)議,美國是享盡利益(allthegreatbenefits),中國是盡享挑戰(zhàn)(allthetoughchallenges)。中國要做什么?美國要做什么?在坎普的幻燈片上,中國要做10件事:到2005年,將總的平均關(guān)稅由24%降至9%;更快地優(yōu)先將部分美國產(chǎn)品的關(guān)稅在2003年前降至7%;2005年前取消對(duì)高科技產(chǎn)品的關(guān)稅;削減一半的農(nóng)產(chǎn)品關(guān)稅;對(duì)美國多項(xiàng)農(nóng)產(chǎn)品開放市場;給外國公司完全的貿(mào)易權(quán)利,消除國有的外貿(mào)公司;開放電信、保險(xiǎn)、銀行、保障、音像等服務(wù)業(yè);顯著增加外國電影的放映量;開放互聯(lián)網(wǎng)投資;加速降低汽車關(guān)稅。而美國呢?"只需要通過給中國永久正常貿(mào)易關(guān)系,然后收下這些利益。"就這么一條。坎普的理解,我不敢確定條條屬實(shí),但很清楚,中美間的WTO協(xié)議,美國商人絕對(duì)樂見其成。
按常理,有如此豐厚之所得,美國對(duì)中國多些尊重是起碼的一種態(tài)度。但情況遠(yuǎn)不如人之所料。素以中國研究見長的加大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位亞太研究專家說,中美面前有兩條同樣寬廣的道路,一條是和平相處,一條是"新冷戰(zhàn)"。而現(xiàn)在,正如該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鮑姆所言,中美關(guān)系正處在"多事之秋","一方面,許多中國人相信美國正在尋求一種旨在遏制中國在地區(qū)事務(wù)和國際事務(wù)中的上升勢頭的霸權(quán)政策,另一方面,許多美國人相信中國過去20年的現(xiàn)代化,尤其是軍事的現(xiàn)代化,對(duì)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wěn)定,是一種潛在的威脅。"UCLA所舉辦的此次中美對(duì)話會(huì),亦明白指出,中美關(guān)系已到了十字路口。轟炸使館、政治獻(xiàn)金案、核間諜案、售臺(tái)武器、人權(quán)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所有這些,都讓中國人的心蒙受著一次又一次陰影。
中美關(guān)系的客觀現(xiàn)實(shí)
今年是美國總統(tǒng)大選年,對(duì)中國進(jìn)行"妖魔化"的描述,相信又是一項(xiàng)時(shí)髦的政客談資。適逢臺(tái)灣大選,北京的《白皮書》發(fā)表,中美關(guān)系將面臨新的考驗(yàn)。美國已習(xí)慣了兩岸不統(tǒng)不獨(dú)的局面,只要一直拖下去,美國就一直享有發(fā)言空間,此為其戰(zhàn)略利益之所在,決不會(huì)輕易放棄。北京決心打破長痛的僵局,把話進(jìn)一步挑明,實(shí)在是迫于無奈。臺(tái)獨(dú)的聲音昭然可聞,美國的操控時(shí)時(shí)可感,北京必須亮出不惜一戰(zhàn)、不愿受制于人的底牌,才能將臺(tái)海局面多少導(dǎo)入統(tǒng)一的正軌。前來UCLA參加會(huì)議的北京大學(xué)國際關(guān)系學(xué)院副院長賈慶國在演講中說,《白皮書》已經(jīng)表明,"如果臺(tái)灣投票獨(dú)立,那么就等于投票選擇戰(zhàn)爭。"洛杉磯的一位華僑領(lǐng)袖說,《白皮書》不是針對(duì)臺(tái)灣某個(gè)特定的候選人,而是為臺(tái)灣問題劃了一條清晰的底線,讓他們心中有譜,不要為選情走得太遠(yuǎn)。
同時(shí),它也是臺(tái)灣統(tǒng)一的催化劑。"北京方面已由耐心等待,變?yōu)橥苿?dòng)談判達(dá)到統(tǒng)一,談最好,但你不談,也要統(tǒng)一。這就大大壓縮了臺(tái)獨(dú)的空間。北京不會(huì)看著你一邊不來談,一邊在各個(gè)層面加緊本土化。臺(tái)灣要避免動(dòng)武,必須談判。"賈慶國說:"為了臺(tái)灣統(tǒng)一,北京可能在談判條件上作出極大的姿態(tài),不僅包括原來所說的讓臺(tái)灣保留軍隊(duì)等,統(tǒng)一后的中國,就是更改國名也是有可能的。"無論是留出足夠的談判空間,還是封死臺(tái)獨(dú)的變向作業(yè),可以看到,進(jìn)入2000年之后,北京的姿態(tài)比以前更為鮮明了。如果臺(tái)獨(dú)勢力仍無動(dòng)于衷,公布統(tǒng)一時(shí)間表或許就是不久的事。在中國統(tǒng)一的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下,美國的舉動(dòng),仍會(huì)是一個(gè)值得重視的變量。
克林頓3月1日稱,美國的政策和20年前一樣,都是"一個(gè)中國",但美國認(rèn)為必須和平解決。還是希望維持現(xiàn)狀。更令人擔(dān)憂的是,美眾議院已通過《加強(qiáng)臺(tái)灣安全法》,將美臺(tái)關(guān)系納入準(zhǔn)軍事同盟的范疇,如參議院通過,將給中國統(tǒng)一平添潛在的巨大障礙。中國的事,卻要時(shí)時(shí)考慮美國的反應(yīng),這就是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客觀現(xiàn)實(shí)。到美國后,發(fā)現(xiàn)美國的確有很大的包容性。原來聽說這里是"大熔爐",而現(xiàn)在這一理論已經(jīng)落伍。因?yàn)?"熔爐說"仍有多種文化匯為一爐、定于一尊的味道,現(xiàn)在強(qiáng)調(diào)的是完全的多元化,即多種文化并存,各行其道。大學(xué)課堂上,盲人帶著導(dǎo)犬來上課,聾子還有專門的志愿者在前邊給他打手勢。在一套比較完善的法律系統(tǒng)規(guī)范下,各種膚色、背景的人都能相互尊重,平等相處(當(dāng)然,這也經(jīng)歷了一個(gè)過程)。此情彼景,心中經(jīng)常浮現(xiàn)出同一個(gè)問題:國內(nèi)如此開放的美國,為什么對(duì)中國懷有如此多的不解乃至偏見?
這問題當(dāng)然不是只提給美國人。回想20年前,甚至這20年間有些時(shí)候,美國在中國人心中又是一個(gè)什么形象?是一個(gè)要被埋葬的帝國主義代表呀(一個(gè)教歷史的美國教師曾問我這是為什么)!歷史的深深的積怨,并非相逢一笑就能泯卻恩仇的。政治家的有些話語,也許只是一時(shí)之用,但對(duì)普通民眾來說,卻可能當(dāng)成長久的事實(shí)存進(jìn)心里。
美國思維的背后
粗粗清理一個(gè)月來的思考,我想,美國對(duì)中國的不解和偏見,大概有這么一些原因:
第一,兩國天然的差異。歷史長短,自然條件,建國里程,人口來源,宗教信仰等,差別都很大。隔著世界最大的大洋,歷史上的交流和來往的方便性都不夠。
第二,近一兩百年,中國內(nèi)亂外患,相當(dāng)長時(shí)間游離于現(xiàn)代化潮流之外。與此同時(shí),美國風(fēng)云際會(huì),逐漸成為"世界霸主",一進(jìn)一出,差別更大,共同語言亦更少。
第三,長期以來尖銳的意識(shí)形態(tài)沖突。反共產(chǎn)主義(anti-communism)是美國政治哲學(xué)的一個(gè)基本立場。我頗為不解地問過幾個(gè)美國老師:"即使你們不喜歡共產(chǎn)主義,但把是否參加過共產(chǎn)黨、是否相信共產(chǎn)主義這類問題寫進(jìn)公民入籍試題,將其和納粹黨并列一起,這未免太風(fēng)馬牛不相及了吧?"他們的回答是,我們也分不很清,但那都是對(duì)我們生活方式(wayoflife) 的威脅。我解釋說中國正在搞市場經(jīng)濟(jì),有很多私人企業(yè),尊重私人權(quán)益。他們又不解了,那怎么是共產(chǎn)主義呢?
第四,現(xiàn)實(shí)的沖突。從過去的韓戰(zhàn)、越戰(zhàn)、冷戰(zhàn),到今天的貿(mào)易戰(zhàn),人權(quán)之爭,臺(tái)灣問題,中美現(xiàn)實(shí)的沖突幾乎沒有停過,可說是一路吵過來的。
第五,缺乏交流。據(jù)說美國75%的國會(huì)議員沒有出過國,所以有些中國人看來"小學(xué)生都懂的問題",美國議員的確不曉得,也不奇怪。
第六,思考習(xí)慣與表達(dá)習(xí)慣的不同。美國人講求個(gè)性自由,喜歡發(fā)表不同意見,俗語有"兩個(gè)美國人,三個(gè)觀點(diǎn)"之說。但同時(shí),表達(dá)觀點(diǎn)時(shí),美國人又很注意技巧。中國人講究中庸,很能忍耐,但忍到一定限度,就會(huì)強(qiáng)烈爆發(fā)。在UCLA會(huì)議后,我問海峽兩岸關(guān)系研討會(huì)會(huì)長李惠英女士有何印象,她說,中國人有一個(gè)毛病,覺得自己委屈,但給你機(jī)會(huì)發(fā)言時(shí),要么準(zhǔn)備不充分,言之無物,要么太刻板,都是"純官方語言",不像美國人,很會(huì)利用舞臺(tái),講得別人想聽。
第七,體制的不同。美國人不太相信政府,對(duì)政府的要求不是高效,而是權(quán)力越少越好。當(dāng)年,《獨(dú)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斐遜有言,"Hegovernsbest,hegovernsleast。"管得越少越好。三權(quán)分立,加上州與聯(lián)邦政府的分權(quán),都是為了限制某一方權(quán)力過大。美國人對(duì)政府天然懷有戒心,沒什么"魚水深情"。因此,看到所謂中國政府對(duì)人民如何如何的報(bào)道,就信以為真。
第八,美國傳媒"妖魔化中國"的影響。自1989年"六·四"之后,美國傳媒對(duì)中國的主要報(bào)道興趣似乎就沒有離開過人權(quán)和異見人士,近年更開始以"中國威脅論"為前提,對(duì)中國這個(gè)"假想敵"進(jìn)行"妖魔化"(Demonizing)。加州大學(xué)柏克萊分校新聞系主任斯切爾說:"媒體現(xiàn)在太多極端化的立場了。"《紐約時(shí)報(bào)》駐上海首席記者費(fèi)森(SethFaison)指出,美國大眾傳媒的首要目標(biāo)是:通過故事來吸引大眾興趣,而不是去系統(tǒng)地校正中美關(guān)系的失調(diào)和誤解。《洛杉磯時(shí)報(bào)》的一篇評(píng)論更寫到,"我們的傳媒一次次地報(bào)道中國的異見人士的入獄和獲釋,似乎那里只有這一個(gè)故事","西方傳媒已沉溺于那些負(fù)面的、表面化的陳年老調(diào)里","如果我們的傳媒要有高尚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那它就有責(zé)任提供那種符合我們的民主體制和我們自炫的新聞自由的新聞,由此才能為一場更平和、更理性、信息更透明的爭論創(chuàng)造基礎(chǔ)。"我感到,美國不少有識(shí)之士對(duì)"妖魔化中國"已經(jīng)看不慣了。
第九,"冷戰(zhàn)思維"的影響。中國駐洛杉磯總領(lǐng)事安文彬說:"有些美國人習(xí)慣了這么一種思維,如果發(fā)現(xiàn)不了敵人,就創(chuàng)造一個(gè)敵人。前蘇聯(lián)解體后,目標(biāo)就是中國。"
第十,臺(tái)獨(dú)勢力和臺(tái)灣當(dāng)局的影響。一邊用大把鈔票購買武器和開展公關(guān),一邊以世界新的民主樣板和經(jīng)濟(jì)楷模自居,臺(tái)灣備感優(yōu)越;一邊是北京在統(tǒng)一的大是大非上針鋒相對(duì),一邊是所謂"國際空間在打壓下日漸縮小"(目前與臺(tái)灣有邦交關(guān)系的國家只有二十幾個(gè),臺(tái)灣擔(dān)心一旦到了只有個(gè)位數(shù)的地步就會(huì)由"量變到質(zhì)變")
,臺(tái)灣大嘆悲情。如此狀態(tài),又不肯回頭是岸,只好跨洋越海,尋求美國的支持。在UCLA的會(huì)議上,一些臺(tái)獨(dú)分子的發(fā)言讓我很開了點(diǎn)眼界。有人竟說,二戰(zhàn)結(jié)束前的雅爾塔會(huì)議,只確定了日本歸還臺(tái)灣,但臺(tái)灣交給誰并沒有定。真是想"獨(dú)"已經(jīng)到了"偏執(zhí)狂"的地步了。
以更寬廣的心去融入世界
這篇文章寫到這里,也許有讀者會(huì)問:中美間有這么多障礙,中國早該多說點(diǎn)" 不"了。我們的政府為什么不能更硬一點(diǎn)?這問題我也反反復(fù)復(fù)地問自己,有時(shí)真覺得心氣難平,眼睛發(fā)酸。我想,我們這些年輕人,應(yīng)該說和美國并沒有諸如抗美援越那樣的沖突感受,也沒有前輩們經(jīng)過階級(jí)斗爭年代對(duì)美國留下的思想陰影,相反,我們至少都是美國產(chǎn)品的愛用者,對(duì)美國式的生活方式也多有向往。我們尚且看不慣美國對(duì)中國的一些做法,我們的領(lǐng)導(dǎo)人,那些堅(jiān)定的共產(chǎn)主義的信仰者,能看得慣么?顯然,中國選擇與美國發(fā)展建設(shè)性的友好關(guān)系,一定有其更深遠(yuǎn)、更合理的考慮。
首先,我想我們的領(lǐng)導(dǎo)人一定認(rèn)識(shí)到,盡管中美間差異巨大,但是美國無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而且直到今天它仍是最強(qiáng)大的國家。如果說中國在5000年的歷史上為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的話,那么,這一兩百年,中國的作為實(shí)在讓我們汗顏。相反,美國在建國200年的短短時(shí)間里,應(yīng)該說在許多方面都出類拔萃,助益了人類。中國要吸收人類一切積極的文明成果,首先就要吸收美國的文明精華。在接觸中,會(huì)有不適應(yīng),會(huì)有斗爭,但這些東西不應(yīng)成為放棄接觸的借口。兩個(gè)這么大、又有這么大差別的國家能走到一起,有些磕磕絆絆是正常的,這既是現(xiàn)實(shí),又是應(yīng)有的襟懷。其次,發(fā)展中美關(guān)系是對(duì)我們的人民真正負(fù)責(zé)任的態(tài)度。20多年來,在中國走向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jì)的道路上,透過美國這扇窗口,通過中美間各種層次、各個(gè)方面的學(xué)習(xí)與合作,不僅加強(qiáng)了了解,而且中國也獲得了極大的收益。
這收益有經(jīng)濟(jì)的,也有觀念的,有有形的,也有無形的,有現(xiàn)實(shí)的,也有可能在未來"變現(xiàn)"的。如果這20年是與美國分庭抗禮的20年,我們的收獲會(huì)有今天這么大么?我們歷史上吃"狹隘民族主義"的虧吃大了!
最后,以建設(shè)性的心態(tài)處理中美關(guān)系,也是對(duì)世界負(fù)責(zé)的態(tài)度。20多年來,中國日漸富強(qiáng),在國際事務(wù)中的地位漸漸凸顯,本身就是維護(hù)和平與穩(wěn)定的一股力量。把世界引向何處,中國肩負(fù)著責(zé)任。如何處理中美關(guān)系,亦是責(zé)任的一種體現(xiàn)。從20多年前開始改革,到站在21世紀(jì)的起點(diǎn)上,中國人對(duì)自身在未來世界的位置,有著實(shí)實(shí)在在的信心。這信心絕非當(dāng)年"超英趕美"式的信心。
中國還有大量難題待解,還需更大的打破禁忌的勇氣,但誰都不會(huì)同意將開向世界的列車再開回去。我們的希望,正在于此。
在UCLA的會(huì)議上,一位中國學(xué)者說:"由于雙方的共識(shí)和分歧都很大,因此政府的導(dǎo)向就顯得更重要。"多做信任的加法,多做加深了解的加法,無疑是明智之舉。中國的底牌,美國很清楚,不去觸犯它,就是在給兩國關(guān)系做加法。同樣,作為中國人,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表明立場,但沒有必要也不應(yīng)該把自己囚禁在委屈的悲嘆里。20年了,中國人,你的心應(yīng)該比過去更遼闊,應(yīng)該比他人更寬廣。□(注:本刊總編輯秦朔目前正在美國做短暫的學(xué)術(shù)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