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走邊看——藏南邊境行
朗 杰 尕瑪多吉

那里的人們不懼嚴酷的自然環境,滿腔熱情地工作著,他們的生產、生活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密林深處有電視
當夜幕降臨,西藏錯那縣勒布民族區的門巴族人大都打開電視機,圍坐在卡墊(藏毯)上,喝著酥油茶或青稞酒,欣賞著他們喜愛的電視節目。
勒布區區長次仁俊美說,民族區共有140多戶,其中50%的人家已有電視,而且都是彩色電視機。他說,只要有好貨,許多家庭都想買。據人民銀行勒布營業所統計,門巴群眾在這家營業所的存款達400萬元,平均每人存款6000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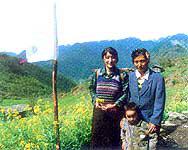
記者來到旺姆一家。40歲的旺姆是一位家庭主婦,她有3個孩子,大兒子在山上放牧,二兒子和最小的女兒在區公辦小學讀書,丈夫因為是勒鄉的鄉長,很少有在家的時候。因此,前年鄉里建了廣播電視收轉站以后,電視成了她最好的伙伴。
“我最喜歡看藏語電視連續劇,”她說,“小孩周末放學回來,愛看動畫片,而愛人又喜歡看新聞。”每當這時旺姆只好讓位,干她的家務活了。
與旺姆不同的是,麻馬鄉的格桑羅布則喜歡看“財經報道”、“經濟信息”和“世界各地”節目。他說:“通過收看這些節目,使我能夠更多地了解國內外發生的事情,特別是經濟情況。”格桑羅布和他的母親,幾年前在村里還是個貧困戶。前些年,他從銀行貸款1萬元,從澤當、拉薩等地販運日用百貨,在交通閉塞的鄉村開了商店,又用賺來的錢買了一輛東風貨車,跑運輸,一下子富了起來,還蓋了新房。初懂漢語的格桑羅布說:“電視節目大開了我的眼界。”
門巴族人主要聚居地勒布山溝。勒布(藏語美妙之意),位于喜馬拉雅山脈南麓西藏錯那縣境內,轄麻瑪、吉巴、貢日、勒四個門巴民族鄉。這里平均海拔2800米,常年山青水秀,鳥語花香。當地政府對門巴人給予特殊照顧,允許群眾自主經營部分山林。
據了解,在西藏550個鄉建立太陽能廣播電視收轉(單收)站,是1994年中央確定的62個援藏建設項目之一,總投資2800萬元,如今絕大部分鄉已經建成。勒布區所屬4個鄉的收轉站,目前可接收中央、西藏等7個頻道的節目。
次仁俊美區長說,在深山野林中也能看到電視,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跨越,不僅滿足了門巴人文化娛樂生活的需求,還能開闊視野,增長知識。他自豪地說:“世居深山密林中的門巴人,現在不出山門也能看到世界。”

門巴人的生育觀
生活在祖國西南邊陲勒布的門巴人,盡管人均收入比10年前翻了十幾倍,但當地人口從解放初的100多人發展到前些年的600多人后,近年卻呈平緩發展狀態。
擁有4萬多人口的門巴族是中國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盡管各級政府對門巴族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但勒布的門巴族人生育一般為二至三胎。門巴族區長次仁俊美說:“多生孩子負擔太重,我們希望生活過得好一點,因此不愿多生孩子。”
次仁俊美與當教師的妻子卓嘎生有一女,他對目前的家庭狀況感到滿意。他認為,保障孩子受到高等教育非常重要。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是他和他這一輩人的遺憾,他希望上輩人的不幸不要在下一代延續。過去,門巴山區的教育幾乎是一片空白。解放后,政府十分重視邊區群眾的教育工作。如今,勒布區小學在校生人數達90名,兒童入學率在98%以上。先后有近百名門巴族新人走出山區,從事各種全新的工作。
旺姆是勒鄉生育較多的母親。她在生完第三胎后主動到醫院做了結扎手術。她說,從1980年起,國家每月為門巴族人供應17.5公斤口糧,她家便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家庭副業增加收入,孩子太多不僅影響工作,還會造成家庭負擔。

原始山寨現代潮
到本世紀50年代仍生活在“刀耕火種”時代的西藏人,現在已跳起了迪斯科。
生活在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北坡察隅山溝里的人,第一次從影視上看到現代舞時,都感到“莫名其妙”,而現在,這種與當地舞蹈大不相同的外來舞,已成為察隅人日常娛樂活動之一。
逢年過節,這里的年輕人聚集在鄉政府大院或草地上,隨著錄音機播放的舞曲,盡情歡舞通宵達旦。
察隅溝公認的“迪斯科王子”達多,是下察隅鄉的普通農民,然而,與耳掛碩大的喇叭型耳墜、身穿無袖長衫的老人不同的是,達多和他的同伴有的穿西服,有的穿“牛仔”。達多說:“勞動之余,跳跳舞可解除一天的疲勞,也可豐富村里文化生活。”他說,現在手里有了錢,我們這些山溝里的人何不“吸一吸現代生活的新鮮空氣”。
尚未被承認為民族的人,沒有自己的文字,多少世紀以來使用結繩和刻木記事的辦法,平時沒有記年月的習慣。50年代以前,人被視為“野人”,他們靠“一把刀、一把火”世居山林,幾根木樁,用藤葛捆架起來,蓋上茅草屋,便是他們的棲身之地;“刀耕火種”是他們的主要生產方式。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時,在政府的幫助下,人從深山老林中走出來,開墾土地,建設新村,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如今,他們的生產生活正發生深刻的變化。
當你走進察隅溝任何一個村莊,你就會感到現代潮不僅僅涌現在年輕人的舞場上,騎著自行車上工的小伙子,滿載貨物的汽車,琳瑯滿目的路邊小店,以及從學校、農家小院傳出的瑯瑯讀書聲和悠悠流行歌曲,都顯示出現代文明之風吹遍了各個山谷。
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人,其家庭設施也不比城里人遜色,收錄機、電視機、沙發、立柜、席夢思等現代家庭設施樣樣俱全。
格桑達瓦夫婦和他們的四個大學生孩子
目不識丁的藏族老漢格桑達瓦,勒緊腰帶把4個子女培養成了大學生。
老漢為此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但他說:“值得!”
格桑是喜馬拉雅山區西藏日喀則地區亞東縣的一名退休工人。西藏解放前,格桑因不堪寺廟喇嘛的虐待而逃到了亞東,舉目無親的他仍然給當地領主當傭人,直到西藏民主改革以后,他才當上了這里的林業工人,并與一位叫普赤的姑娘結婚成家。
格桑夫婦有5個孩子,當時微薄的工資和妻子種田的收入僅夠維持一家7口的生活。但是,格桑說:“我們再苦也要供孩子讀書,他們再也不能像我們這一代那樣成了睜眼瞎,應當讓孩子成為對國家社會有用之人”。
看到孩子們一個個背上書包進了學堂,格桑夫婦舒心地笑了,可家里的負擔也同時加重了。懂事的大女兒索郎普赤上到初二就瞞著家里退了學,找了一份臨時工作,幫父母供弟妹讀書。
格桑的三女兒央宗回憶說:“我和二姐次仁念到高中畢業,也想仿效大姐,考個中專算了,好早點工作分擔家里的負擔,但被爸爸媽媽堅決阻止了。”1986年,次仁和央宗分別考上了拉薩西藏藏醫學院和陜西咸陽西藏民族學院。兩年后,她們的弟弟瓊達也考入了西藏大學。
盡管當時大學還沒有實行收學費制度,三個孩子上學的路費和生活費還是成了這個家庭的沉重包袱。6年間,格桑夫婦一共花了五六萬元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向單位和親朋借貸的。往往是孩子們揣著充足的生活費返回了學校,夫婦倆卻開始節衣縮食地生活還債。“最苦的兩年,家里逢年過節都沒錢買肉和蔬菜,”普赤說。
這時,有人勸格桑讓一個孩子退學,縣里也答應幫助安排工作。格桑說:“有兩回我都走到了縣門口,但就是邁不進去。孩子們好不容易上了大學,怎么忍心讓他們半途而廢呢!”
現在,格桑的4個孩子先后大學畢業,在自治區內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工作了的孩子們對父母十分孝敬,兒子瓊達用第一個月的工資為家里添了一臺洗衣機,央宗和次仁也常常寄錢給家里和正在讀書的小妹妹。
但這并不是格桑最關心的。央宗說:“每次休假回家,爸爸問得最多的就是我們在單位里的表現。臨行前對我們叮囑最多的,也是要干好工作,不辜負國家對我們的培養和教育。”

馬背上的西藏基層干部
在各種現代交通工具發展突飛猛進的今天,祖國西南邊陲的西藏農牧區基層干部仍然騎著馬叮呤鐺鋃地穿梭于崇山峻嶺之中。他們不懼嚴酷的自然環境,始終滿腔熱情地工作著。
記者沿著喜馬拉雅山區采訪,親身體驗到在這高山峽谷地帶工作的艱辛。我們從西藏山南地區隆子縣驅車來到加玉鄉,再往東就沒有公路了,只有騎馬前行。加玉鄉與準巴鄉之間只有25公里,如果坐汽車去,要不了半個小時,可我們騎馬足足用了5個鐘頭。這是一條十分險峻的山間騾馬道,抬頭是陡峭的山崖,腳下是咆哮的河流。我們按向導的指引壯著膽子前行。到了目的地,一個個累得腰酸腿疼。
準巴鄉黨委書記桑典介紹,全鄉4個村都在山上。從鄉所在地到各村,騎馬至少走一天,有的村路連馬都過不去,只有靠兩條腿。鄉干部一年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各個村辦事,其中一半時間都在馬背上度過。
因為不通公路,給鄉里工作、群眾生活帶來許多不便。農用化肥、日用商品,甚至食鹽,都要從幾十公里以外的縣城,靠人背畜馱進來。光處理、聯系這些看似平常的瑣事,鄉干部們就需花費相當的時間和精力。有一年夏天,桑典騎馬到縣里辦事,一場暴雨把橋沖毀,唯一的路行不通了。他想繞道回去,結果深夜在灌木林中迷了路,弄得筋疲力盡。幸虧老馬識途,天亮時把他馱回家里。
在錯那、洛扎、浪卡子等西藏南部邊遠地區采訪時,記者也遇到了騎馬下鄉的干部。西藏的許多基層干部,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工作著。如果是冬季,雪封山,路封凍,氣溫達到零下二三十度,騎馬行走更加艱難。然而,這些基層干部沒有抱怨。桑典說:“鄉親們都是祖祖輩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干部還有什么好說的呢!”他說,我們希望經濟盡快發展起來,有一天能把公路修到每個鄉村。
正是因為有無數個像桑典這樣與民同甘共苦的基層干部,即使交通不便的準巴山溝,群眾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全鄉人均收入達到100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