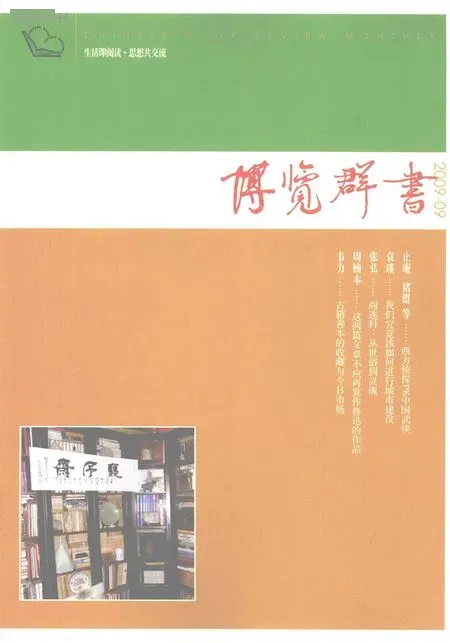術(shù)語社會學(xué)筆記——譯名通行 思路活躍 諸事順遂
陳兆福
十四、文學(xué)/出版物:出版業(yè)術(shù)語
[拉]literatura,[英]literature,[德]Literatur,[法]literature,[俄]литература,[日]文學(xué)、文藝。
凡多義詞,義項有主次廣狹深淺多層次,任人揀選,以其常見、罕用、首見、后識,為我所知悉所用。此事有時是讓人頗為撓頭的。然則,利弊相生。孳生繁、用處多、通義廣,詞中活子轉(zhuǎn)為術(shù)語穿行學(xué)術(shù),正是因此而生。從學(xué)習(xí)心理學(xué)而言,此種轉(zhuǎn)用,隨其習(xí)見,實難駕馭而時常干擾術(shù)語實際應(yīng)用,影響正確運作,令人可憐可愛。
就這方面說,首見義習(xí)慣用項,有時就這么耽誤事。眼見某術(shù)語,腦中即時閃出某義,通常即指認為此義,短時間若無難解難疏,小范圍若無礙釋解,一般亦就以此義為單行道一路前行。一時間人人以為所知義即確解,可惜那往往并非最確義,有時恰恰正在此處理解出了差錯。事過雖覺察所知義項有誤,皆因知識不全面經(jīng)驗不深入所致,但這忙中失察已經(jīng)誤了事。既然自己誤判,除了自責(zé),別無他法。此等事,若屬平常類,事后做些切實彌補功夫未嘗不能挽救損失,這里要談的卻是影響政策多年,以致形成思維定勢撥亂反正頗費功夫的一場教訓(xùn)。
說的是對列寧一個術(shù)語怎樣誤解,來源有自,延申有理,凡六七十年,而糾誤歷程又不下二十年。前此所誤解歷久業(yè)已形成思維定勢,一日須扳正,難免很失落。原當(dāng)正確對待已是言行所準,從此改弦更張,亦須自己做來,掙脫失落感重新振作談何容易。話說回來,理解轉(zhuǎn)入正確局面,打開更大通路,順暢前行,又是讓人何等欣喜。
甲、年表:思路歷程——事實簡單羅列
1、列寧填表: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абота
列寧填“蘇維埃代表登記表”、“俄共代表大會登記表”,“職業(yè)”、“工作”欄時,作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абота(寫作、文字工作),即自稱是(著作者、寫作者)。意思指他寫理論著作,政論和國務(wù)文件而非其他。有一次,他這么對高爾基說:即使剝掉我的皮,我也寫不出兩行詩來(《回憶列寧》[五卷集]第二卷第332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言外之意:他不會寫詩不寫文學(xué)作品。這話聽來深含尊敬高爾基,班門不弄斧之意。畢竟高爾基享有世界文豪聲譽。話雖聽他這么說,但他對俄國文學(xué)家自有真知卓見,不由高爾基不敬佩。
這話涉及他三篇文字:甲、《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乙、《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丙、《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主要是丙文。
2、列寧本意:探討革命活動和出版物關(guān)系(1905年)。
《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寫于十月革命時期。這十月非那著名的1917年10月,而是后者的準備。就勝利的大小而論,這時無產(chǎn)階級已經(jīng)為俄國贏得了一半自由(可惜很快又喪失了)。列寧聞訊匆匆返回彼得堡,撰文指導(dǎo)新時期文字工作,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出版物適時提出政策建議,以適應(yīng)革命寫作事業(yè)從地下轉(zhuǎn)為公開半公開,即具體闡述政論家在黨報黨刊上應(yīng)如何堅持黨性問題。
所謂出版物,不外報紙刊物書籍傳單等宣傳物。“出版物現(xiàn)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為黨的出版物”。列寧因而指出應(yīng)體現(xiàn)“徹底的黨性”,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wù)。出版事業(yè)應(yīng)是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列寧指出,無可爭論,寫作事業(yè)最不能機械劃一,強求一律,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無可爭論,在這事業(yè)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chuàng)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nèi)容的廣闊天地(《列寧選集》1:664)。
3、初期誤解:視所著為關(guān)于文學(xué)藝術(shù)的文章(1931年)
著名的十月革命勝利后,執(zhí)政黨迎來全新的日子。1931年,聯(lián)共中央列寧研究院所出版《列寧選集》收甲乙二文,編者撰附題注長文。二文評論文學(xué)家,難得如此精辟,一向深受重視。只是,題注因之推而廣之當(dāng)作關(guān)于文學(xué)藝術(shù)問題的文章予以推薦以論證文學(xué)藝術(shù)具有階級性,體現(xiàn)階級利益。
1938年蘇聯(lián)藝術(shù)出版社所編《列寧論文化與藝術(shù)》收甲乙二文更進一步說明“藝術(shù)的階級性與黨性”。
a、“出版物”這一術(shù)語,義有廣狹,凡形成文字的東西(含文學(xué)藝術(shù)著作)均在所指之列,斯文一點稱為“文獻”,德文Literatur,見于《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三章標題就譯:社會主義的和共產(chǎn)主義的文獻。
列寧丙文所談首重政治性出版物,而非文學(xué)藝術(shù)。此詞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而見于列寧其他著作,有時稱文獻、書刊、報刊、刊物,因具體情況而異,但總屬出版物,俄文并不就例外。
b、自然,文中個別句子也提到諸如美學(xué)藝術(shù),小說圖畫,舞臺藝術(shù),作家畫家和女演員等等。但畢竟不是列寧本文主旨。
c、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如指文學(xué)作品,習(xí)慣加限制性定語,寫成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即藝術(shù)性著作。列寧本人這樣使用,甲乙二文題注者亦如此。瞿秋白譯作“藝術(shù)的文學(xué)”。譯俄文者案頭常備八杉貞利所編《露和辭典》,日譯作文藝,莫非受其影響?
由此推斷,此間差別異同,當(dāng)年我譯者早有察覺。一般譯者總不致于全然不知。
看恩格斯《流亡者文獻》,德文Literatur與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因其同源自拉丁文literatura,大體一致。恩格斯指的僅是報紙刊物等。我國一度譯做《僑民文學(xué)》,后糾正。不知怎么,糾正之筆未延及于列寧此文。
d、偶爾也見徑直作“文學(xué)”者,讀《馬恩選集》能體會到編譯局對此術(shù)語頗為慎重,特意加了注,說明該處德文Literatur,“泛指科學(xué)藝術(shù)哲學(xué)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選集》1:276)。認真負責(zé)者當(dāng)如是。誠然,不該忘了偷火者普羅米修斯每每沒能優(yōu)游從容,設(shè)立編譯局不正是一番表白!
e、事有湊巧,當(dāng)其引進我國時,正值我人更新文學(xué)觀念。小說戲曲,以封建社會傳統(tǒng)偏見,不能登大雅之堂。清末民初,西風(fēng)所及,有識之士梁啟超、王國維,新文化運動領(lǐng)袖人物陳獨秀、胡適為其(連帶而及于民間藝術(shù))鳴不平,呼吁還“文學(xué)”為正身不遺余力。
4、后期曲解:認定為有關(guān)的經(jīng)典之作(五十年代)
可惜當(dāng)年蘇聯(lián)理論界如上所述,竟誤解出版物為文學(xué),張冠李戴,頭疼藥用來治腳,進而更于斯大林以后蘇聯(lián)所出版兩部書為甚。
1957年《列寧論文學(xué)與藝術(shù)》收丙文,長序說列寧這一著作“制定了文學(xué)的黨性這一重大的原則”,“規(guī)定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的新任務(wù)”(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0年上卷第11頁)。
1960年《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xué)原理》(1961年即有譯本)一書專節(jié)“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發(fā)展的列寧階段”所闡釋大抵同于前書(三聯(lián)書店,上冊第210~212頁)。
5、影響我國:文本入境(建國前)
文本經(jīng)這樣理解,步步引申,經(jīng)過權(quán)威的部門一再發(fā)表,屢次鄭重介紹,逐漸流傳開來,又恰當(dāng)國際理論界熱切誠懇向蘇聯(lián)請教,文本原文譯文自然均為大家所樂于學(xué)習(xí)研究探討推敲輾轉(zhuǎn)引用。
初入境正好因應(yīng)中共內(nèi)左傾路線占統(tǒng)治地位之大環(huán)境,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因此接受誤引又是可想而知的。
甲乙二文(含題注長文)和丙文很快進入我國,途徑大致如下:
一、甲乙二文:
1933年瞿秋白譯:《海上述林》(1936年出版)
1943年蕭三譯:《列寧論文化與藝術(shù)》(邊區(qū)版)
二、丙文:
1926年一聲節(jié)譯:《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xué)》
1930年成文英(馮雪峰)譯:《論新興文學(xué)》
陳雪帆譯:《伊里基論文學(xué)》
1933年瞿秋白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xué)》
節(jié)譯,見《海上述林》)
1943年延安《解放日報》譯載《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xué)》
1944年戈寶權(quán)譯:《列寧論黨的文學(xué)問題》
6、入境:文本及其他(建國后)
1951年,周揚、曹葆華等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xué)》(見《馬恩列斯論文藝》)
本版丙文譯文甚至于第71頁有一句竟為“打倒非黨的文學(xué)家!”這十足關(guān)門主義宗派主義口號。
上文第4段業(yè)已指出1957年、1960年兩書移譯之速。
兩個階段,從在野到執(zhí)政,其誤導(dǎo)上升為政策歷數(shù)十年,最后為“四人幫”所趁,經(jīng)過這么三轉(zhuǎn)四轉(zhuǎn)毫厘千里觸目驚心惹犯眾怒,才終于從全面到局部認真檢查反思而得以糾正。
7、影響擴大
其間,毛澤東于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兩次引證,作《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xué)》。第一次說,列寧還在1905年就已經(jīng)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yīng)當(dāng)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服務(wù)。第二次說,無產(chǎn)階級的文學(xué)藝術(shù)是無產(chǎn)階級整個事業(yè)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從此,文藝政策上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wù),文藝從屬于政治。
8、開始糾正:盧卡奇反遭斥
這期間,五十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藝學(xué)家匈牙利盧卡奇指出,(丙文)列寧本文僅對1905年那個時代有意義,僅僅涉及黨的報刊工作中政論家的職責(zé)。
以盧卡奇當(dāng)時身份,人皆視為修正主義者,其糾正可想而知只能是幫倒忙。
9、修訂舊譯:發(fā)表新譯文
1981年,編譯局修訂列寧本文舊譯文,工作置于學(xué)術(shù)探討基礎(chǔ)上。
1982年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xué)》舊譯經(jīng)修訂改正,新標題作《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重新發(fā)表于《紅旗》雜志第22期。
10、正式糾正:中共中央調(diào)整文藝政策
1982年,毛澤東《講話》發(fā)表四十周年。6月25日,胡喬木在文聯(lián)四屆二次全委會閉會后的招待會上,就文藝與政治關(guān)系發(fā)表講話,提到中央考慮不再用“文藝為政治服務(wù)”、“文藝從屬于政治”這些提法,而改用“文藝為人民服務(wù),為社會主義服務(wù)”(《談文學(xué)藝術(shù)》第241頁)。
乙、說明——情況簡要介紹
大致羅列了過程,在此只能十分抽象地認識演變,推斷所可能產(chǎn)生消極后果。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國內(nèi)階級矛盾上升為民族矛盾,左聯(lián)的關(guān)門主義、宗派主義初步得到克服。建國后,這種關(guān)門主義、宗派主義在另一層面,更大范圍,作為國家政策再次延續(xù)乃至愈演愈烈,必至“文化大革命”才終于擦亮了大家眼睛,撥亂反正有幸走到今天。試看抗戰(zhàn)時期空前活躍的文藝,試看改革開放以來欣欣向榮的文學(xué)事業(yè),早日克服,這一切會早來十年二十年。
話說回來,這二十年來可也頗不容易呢。
首先,雖然總的形勢扭轉(zhuǎn)了,分支線具體操作仍是問題。毛澤東的《講話》是中國革命文藝的綱領(lǐng)性文獻,所引證列寧本文具有權(quán)威性。毛澤東援引列寧文字所作論述,所引和所論彼此扣得十分緊。校改《列寧全集》譯文和改動《毛澤東選集》相關(guān)文字并非一回事是顯而易見的。
從蘇聯(lián)誤導(dǎo)到我亦步亦趨,從權(quán)威論據(jù)到“左”的口號接踵而出,痕跡斑斑歷歷可尋,年表所記只是梗概。
去年讀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第2期文章:記一篇列寧著作舊譯文《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xué)》的修訂,作者丁世俊認真介紹了這件事所包含的歷史底蘊。胡喬木怎樣抓住時機,巧妙運作。他怎樣聯(lián)系編譯局重審術(shù)語,確定正誤。他怎樣審度誤釋列寧本文關(guān)鍵術(shù)語:引文誤釋經(jīng)我們轉(zhuǎn)為論據(jù),為文藝方面制定施行“左”指導(dǎo)思想提供理論根據(jù)。
說起來,1981年他是最恰當(dāng)人選,前此整理《講話》,建國后編輯《毛選》,這時領(lǐng)導(dǎo)《毛選》第2版工作。前因后果解鈴系鈴深悉內(nèi)情。他特別提到三點:
一、文學(xué)、黨性:文學(xué)是社會現(xiàn)象,不能用黨與非黨來劃分。
“文學(xué)”是多義詞,“黨性”也是多義詞,特別是中國流行的“黨性”的用法更具有嚴重的意義,包括對黨的組織性、紀律性等等的態(tài)度和立場。而究其本義,“黨性”沒有這么多的含義。中國的古語說,無黨無偏,或者群而不黨。
“黨性”實際就是“傾向性”,對是非要有一種觀點。“非黨文學(xué)家”的提法要改,“非黨性”也不要,只能講“無傾向性文學(xué)。”
二、“黨的文學(xué)”的提法使人誤以為文學(xué)這一社會文化現(xiàn)象是黨的附屬物,是黨的事業(y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三、由于文學(xué)基本上是個人創(chuàng)作,黨在文學(xué)中不能發(fā)號施令,只能提出號召和建議,做出評論,通過作協(xié)組織作家深入生活,并通過出版、制片等國家行政進行適當(dāng)調(diào)節(jié),但黨對自己的報刊言論和黨員個人的言論卻可以和應(yīng)該實行一定的控制,因為那是真正的黨的事業(yè)的“齒輪和螺絲釘”。
簡單扼要幾句話,澄清了多年理論上和實踐上曾引起混亂和爭論的術(shù)語。固然,這還僅是抽象幾句,或者,還需如韋君宜這樣的政策執(zhí)行者,以切身感受對那消極作為所危害于文學(xué)事業(yè)的情況,進行現(xiàn)身說法。韋君宜得以從干校調(diào)回,形式上重任原職實質(zhì)上只能更其馴服。接到稿件,并奉命使用階級斗爭添加劑,到頭來進退失據(jù),作者不同意,稿子不成樣,讀者受欺騙,書成即是廢品。正是這樣正反難得的體驗,才有她深切的痛感與洞識,其強烈以至于身雖殘而非留下感受不可,也因而觸動我們許多人,令我們的意識深受震撼。
其實,韋君宜不過小小執(zhí)行者,《思痛錄》也僅記一二。若有深悉政策制定執(zhí)行施者受者來描述整個流程,如病理學(xué)者留下較詳細記錄可查,案例的數(shù)據(jù)切片就能更富有啟示意義和警示作用。
另一方面看,文學(xué)既是社會現(xiàn)象,人所身感,均能描述一二。既提到世界文豪高爾基,本文作者至今猶憶早年執(zhí)教小學(xué),中學(xué)教師同鄉(xiāng)陳白澄以所譯高爾基《一個賣藝的孩子》見贈。書中的六個短篇,講的是意大利熱那亞兒童故事。為什么高爾基一段時間離開蘇聯(lián)?多年來雖細讀其傳記仍留下疑竇。至近年始得知列寧斯大林對他的態(tài)度截然不同。文豪欣欣然迎接社會主義,而其后來的個人創(chuàng)作、文學(xué)命運,令我轉(zhuǎn)而移思茅盾、曹禺、老舍、巴金、丁玲。蘇聯(lián)作協(xié)曾討論偉大時代與偉大作品關(guān)系,愛倫堡認為時間短尚不足醞釀作品成熟。以今日流行話說,只產(chǎn)生泡沫“杰作”。而列寧較為謹慎可取的文學(xué)觀遭到曲解,恐怕也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原因。
邊區(qū)政府時代向文學(xué)(家)提出急迫要求,國難當(dāng)頭匹夫有責(zé)。文學(xué)家一身抱負進邊區(qū),寫傳單詩標語口號也令人富有使命感。這時間、地點、條件是必須考慮的。以今日回顧,環(huán)境條件優(yōu)越了,文學(xué)事業(yè)自然享受到應(yīng)得的待遇。細想,惟有際此國家存亡,擔(dān)當(dāng)救國大任者敢如此號召,惟有際此生死關(guān)頭,奔赴前線者愿如此獻身。時至今日,正確領(lǐng)會術(shù)語,糾正理解,鬼蜮伎倆無所施其計。誠也時代所幸,行行業(yè)業(yè)再無須為左一運動右一運動而不專于本身任務(wù),一生襟抱可盡開。
進入人民政府時代,兩次書荒,拒世界名篇于千里之外,先是建國初,用政治標準批文學(xué)著作,文學(xué)精品只有譯自蘇聯(lián)寥寥幾部。踐踏一地的西方世界名著,被逐于人類文明之外。待到向科學(xué)進軍,二十年翻譯規(guī)劃開始逐本開禁,眼前一番新境界。后是八部戲走馬燈更甚之,書殃結(jié)果連文學(xué)理論術(shù)語也剩干巴巴幾個車轱轆轉(zhuǎn),這才苦盡甘來。然而,從禁中脫身那些世界文學(xué)名著,新譯舊譯就這樣于此刻讓“牛鬼蛇神”從冷灰余燼中耙出,從記憶深處涌出,而讀者靈魂正經(jīng)此熬煎暗渡彼岸,文學(xué)以此證明自身價值——無用之用。
退一步說,文學(xué)事業(yè)有其自身不可抗拒的生命力,文藝電影藝術(shù)的成績雖在當(dāng)時又是自有輝煌一面,令世人振奮激動而向往新理想。窮山溝怎富有引力(茅盾、丁玲),破窯洞何來生生靈感(洗星海、賀綠汀、光未然),這是不待論的。卻也倒過來證明糾正之必要,如今術(shù)語再不犯貧乏癥,卻愁繁多文學(xué)現(xiàn)象無名目。
作者附字:本篇部分內(nèi)容根據(jù)丁世俊文整理,特別是年表部分。不敢掠美,特此聲明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