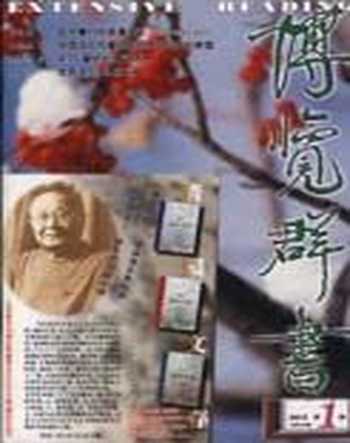洋詞擇漢,繡球落誰家?
陳兆福
Understanding這名詞從動(dòng)詞understand來,早在小學(xué)就聽老師講過,誰也無須不恥下問。我們當(dāng)然也不至于貿(mào)然發(fā)問。但,這是哲學(xué)術(shù)語,當(dāng)別論。說起來,固然"同居長(zhǎng)干里"(李白),"姐妹同里巷"(白居易),但她戶口早遷走了呀!高升了--從日常用語提煉為哲學(xué)術(shù)語,義項(xiàng)業(yè)已深化。不怪1946年,西南聯(lián)大陳修齋。王太慶兩人盤查起它,你提一問我提一問。
原來,十七世紀(jì),當(dāng)時(shí)歐洲人多還以為腦子里一些想法,不是與生俱來還能從哪兒來!誰心中都有上帝,皇帝坐龍廷,從來如此。法國(guó)笛卡爾多疑,心思精細(xì),詳予論述,說天賦觀念,理性本身所固有的,既清楚又明白,無庸懷疑。英國(guó)老百姓偏掙脫了老規(guī)矩的束縛,持新觀念,敢為天下先,1649年把查理一世推上了斷頭臺(tái),刀起頭落。從此,護(hù)(祖宗)法護(hù)國(guó)爭(zhēng)論不休,護(hù)國(guó)公(Protector)克倫威爾忙開了。
1671年,英國(guó)洛克邀約五六友人討論諸如道德和天啟宗教原則一類熱門話題,誰料幾位好學(xué)深思之士談不下去。他們認(rèn)為錯(cuò)了,應(yīng)先考察理智能力。結(jié)果,推他執(zhí)筆先寫出。歷經(jīng)二十年,寫成60萬言巨著
[英]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
[法]Essai sur l'entendement humain,1700
[德]Versuch u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1757
[俄]Опыт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разуме
新作還沒出版(1690),法文摘要就披露于荷蘭(1688)。法譯本(1700)拉丁文本(1701)接踵上市。
洛克挺身而出,實(shí)際上前前后后寫出了許多"辯護(hù)詞",泛及同胞所纏繞不開的哲學(xué)政治經(jīng)濟(jì)教育問題。馬克思贊他為"一切形式的新興資產(chǎn)階級(jí)的代表"。
話說回來,思想界冒出這么位經(jīng)驗(yàn)論者,理性論派驚詫不置。同胞學(xué)者斥責(zé)和辯護(hù)當(dāng)即鬧成一團(tuán),作者抓緊再版增補(bǔ)。大陸德國(guó)一位大忙人萊布尼茨披讀法譯本,即在《每月摘要》上批駁起觀念聯(lián)結(jié)和狂信。五十八歲時(shí),猶期待與作者逐一對(duì)質(zhì),但洛氏卻于72歲上去世了(1705),萊氏不忍心打啞仗,把
[英]New Essay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德]Neue Abhandlungen u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
[法]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俄]новые опыты о челавеческом разуме?jǐn)R下了。該書體裁所采取就是兩人對(duì)話,針鋒相對(duì)。表面溫文爾雅禮讓有加,實(shí)則唇槍舌劍步步進(jìn)逼刨根追究。45萬言,連篇幅也顯出要爭(zhēng)個(gè)高低。多虧1765年有人整理出版,大家有幸看到西方哲學(xué)史上這場(chǎng)重頭戲。馬克思卻并不把這當(dāng)"戲",而當(dāng)"宴",說洛著"像位久盼的客人受到熱烈歡迎"。(一)2:20,有心人面對(duì)不經(jīng)意者
兩世紀(jì)后(1934年),四川人鄧均吾譯出洛著。萊著則由西南聯(lián)大的陳修齋于1982年譯出。其實(shí),兩書名在我們文獻(xiàn)上早就不新鮮。什么不新鮮,"亂"得不新鮮。(注:下表書名,據(jù)語素分欄:第1欄同為"悟性"者;第2欄是以"理"為前位同素族者;第3欄是以"知"為前位或后位同素族者;第4欄是以"力"為同素族者;附星號(hào)者為譯本名;書名后為年分,取后二數(shù),黑體字表示臺(tái)灣出版;右下年柱,年分旁為書名譯者,附澓耪呶譯本譯者):
就關(guān)鍵詞[英] Understanding /[法] entendement 而言,寫者隨手,他不經(jīng)意。聽者有心,他作難了。不是他,是他倆。1994年,后死者王太慶追悼上年夏謝世摯友陳修齋,回憶共剪西窗燭,提到了這件事。
我們很自然這么想,書名就幾個(gè)字還不好辦嗎。請(qǐng)看右下那人梯年柱,跨度八十年呢!那年分,長(zhǎng);那人名,赫赫;那譯名,雜多。長(zhǎng)令人嘆,赫赫令人訝,雜多作難人,讓人思維混亂無所適從。真是一詞之立百費(fèi)思,難道就這么費(fèi)時(shí)費(fèi)人費(fèi)神下去。
批判,奧伏赫變,人道主義,異化嘛,題外工夫多于為題本身所經(jīng)歷的折騰。歷經(jīng)之長(zhǎng),三軍過后盡開顏。可是,這里并沒那些題外干擾,為什么還那么費(fèi)時(shí),而且更長(zhǎng)。難道另有什么玄機(jī)。
說起來,就事論事,不知一書,不譯一名。陳王倆人讀過洛萊二書,自然能 "發(fā)現(xiàn)問題"。然而,洛著不是有譯本了嗎。兩種譯本呢!可惜,這不是簡(jiǎn)單的機(jī)械推算問題。民族思維整體非個(gè)體可比,發(fā)展學(xué)術(shù)文化需要種種推動(dòng)力。智力。社會(huì)力。臭皮匠二缺一。您看,天公(自然,萬國(guó)語文他無所不通)敲人腦袋,王太慶在悼文上說到他們倆把問題歸結(jié)于對(duì)該書兩譯者均"缺少研究"。
事情常這樣,有視而不見,有見而不及,有未能及見。沒那耳朵,不知那是曲子。知其為曲子,感受有深淺。就是有那耳朵沒那福氣也不行。說是不理解,說是不充分理解,說是理解沒找上它來......
理解詞語,需從單詞入手,先須明其諸義項(xiàng)。次及詞組,弄清所構(gòu)各詞孰義項(xiàng)可彼此相搭配。其為封閉性者,搭配關(guān)系穩(wěn)定,選其譯語,沿習(xí)慣選配就是。詞組單純,義項(xiàng)有限,意義固定,變化穩(wěn)定,詞典多備錄,一查即知。其為開放性者則本身義項(xiàng)復(fù)雜,靈活多變,詞組經(jīng)搭配成,圈定了意義場(chǎng),猶須視其所處語境又最后予以調(diào)整。這三字經(jīng)四字文人所共知。(二)溯源探流
二書名,詞組并不復(fù)雜,不過,即系書名,意義就多一層限定,譯名要求貼切,就須多斟酌。上有源宜追溯,下有流應(yīng)探知。結(jié)合西方哲學(xué)史古典原著翻譯史,這里不妨聯(lián)系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談?wù)劇?/p>
往上追究,可想到經(jīng)院哲學(xué)常見的intellectus。斯賓諾莎對(duì)神的理智的愛(amor Dei intellectualis)是眾所周知的。1661年,他寫過[拉丁]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英]Treatise on the Correc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法]Traite de la reforme de l'entendement[德] Abhandlung uber die Lauterung 焩erbesserung燿es Verstandes[俄]Трактат об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разума未完篇。陳王二位盤查時(shí),此書已有兩譯本上市:
賀麟《致知篇》,1942;《知性改進(jìn)論》,1960。
劉榮竣《論知性之改進(jìn)》,1943。
理智改進(jìn)論,1980。
Intellctus這拉丁詞當(dāng)著拉丁語朝地中海西北,向西歐推進(jìn),各國(guó)引進(jìn),爭(zhēng)相以語音字母先模寫為intellectNIntellekt∥intellect Nинтеллект
后來民族語日趨完備,構(gòu)詞又轉(zhuǎn)而側(cè)重取義,寫為understanding NVerstand∥entendementNразум
向下探流,1977年龐景仁送康德《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xué)出現(xiàn)的未來形而上學(xué)導(dǎo)論》譯稿來,談起哲學(xué)術(shù)語譯名混亂就感慨,對(duì)德文Verstand的譯名該清理清理。這譯本也算浩劫中所出,那年月,一大攤子急待收拾,忽然網(wǎng)開一面,指示讀幾本哲學(xué)史。熆閃,哲學(xué)君,總算想到您牐犖頤怯φ俅癰尚8匣,揮舞尚方寶劍,抓緊出書。書后照例都附了術(shù)語對(duì)照,而且既是索引又是多語種:英N德∥法N俄N日(因書而異),譯名還有另譯異譯。這年(說準(zhǔn)確些,1976年)商務(wù)印書館讀者看到書后譯名對(duì)照表,比當(dāng)初1958年無疑更要興奮百倍。
洪謙聞名苛刻,收到寄去的譯名校樣請(qǐng)他斟酌,喜不自禁,急邀說要提提意見。賀麟。朱光潛。周輔成。王太慶(時(shí)猶遠(yuǎn)在寧夏)為檢查。校核。推敲。審定術(shù)語譯名更是著著實(shí)實(shí)都忙好一陣。知識(shí)分子書荒年月見書如見親人。
龐景仁于譯后記聯(lián)系到康德的貢獻(xiàn),介紹康所提出"認(rèn)識(shí)能力"三階段,其對(duì)應(yīng)詞是:
sensibilityNSinnlichkeit∥sensibiliteNсенсбельность understandingNVerstand∥entendementNрассуок
reasonNVernunft∥raisonNразум (三)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先行官
這些重要術(shù)語都和書名有關(guān),本應(yīng)有目錄學(xué)家把書名全部整理一番才是。對(duì)于中國(guó)哲學(xué)史籍,馮友蘭正是持這種眼光,專門系統(tǒng)講過資料,他隨手完成的這項(xiàng)基本建設(shè)工程無疑促進(jìn)了學(xué)科發(fā)展。而哪學(xué)科缺乏這種眼光,未有這樣有心人下這方面工夫,哪學(xué)科的學(xué)子對(duì)基本術(shù)語就終不免總是這么不經(jīng)意下去,得過且過。王太慶畢生致力于外國(guó)哲學(xué)古典原著翻譯,晚年要提他們年輕時(shí)那段舊事,特別說"那時(shí)我們還不到三十歲,滿心愛智,沒有雜念"(《陳修齋先生紀(jì)念文集》第107頁,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想來不是無因--"滿心愛智,沒有雜念",想的可能就簡(jiǎn)單。率真。急切,然而也就有沖勁。老天真這時(shí)大概眼看又過了半個(gè)世紀(jì),區(qū)區(qū)一名亂猶未弭,這一名還拖后腿影響另一名,一猶如此,全何以堪,他不能無動(dòng)于衷!--兩書譯名之立雖可謂略有進(jìn)展,洛書再無人稱為《人類悟性論》,卻仍以《人類理解論》《人類理智論》并行。
這就不能不想到術(shù)語受題外著力者因"禍"得福。但是,余下待整理的術(shù)語還這么多。讓人無從高枕忘憂。記得1982年哲學(xué)界哲學(xué)術(shù)語密云討論會(huì)上,對(duì)于處理譯名,主持人汝信打比方說,對(duì)人地名,不妨采用"專政"辦法,認(rèn)真討論后大家遵行就是,犯不著再浪費(fèi)時(shí)間。至于術(shù)語,涉及辨明義項(xiàng),明確其在哲學(xué)體系中作用,理解的深度,譯名的審定,若個(gè)人的判斷一時(shí)未能說服大家者,宜盡量爭(zhēng)鳴,容許保留意見,別勉強(qiáng)統(tǒng)一。這話黑格爾專家楊一之沒聽到。他聽說開過會(huì),立即來信表示譯名千萬別強(qiáng)求統(tǒng)一,他舉黑格爾"生成"一詞為例說明爭(zhēng)譯名絕非爭(zhēng)意氣(略)。大家看到,黑格爾兩部邏輯學(xué),賀譯楊譯各譯各,各管各,譯名并不一致。本來,出版社就從未想過勉強(qiáng)統(tǒng)一--總編輯陳翰伯入主商務(wù)所立下規(guī)矩。楊函經(jīng)高崧轉(zhuǎn)呈去,他看到,特囑務(wù)必復(fù)函令楊放心。這時(shí),離他1979年說"胡耀邦同志講的‘文責(zé)自負(fù)‘是很新鮮的"正好三年。
說起來,誠(chéng)然,還不是誰講的問題,畢竟就有個(gè)尊重著譯者的傳統(tǒng),令那些存心壓制抹煞者時(shí)刻咬牙切齒,傳統(tǒng)無形,他們這些人卻總見到傳統(tǒng)無處不在。陳翰伯對(duì)他們采取毫不含糊的對(duì)策。1962年,武漢韋卓民送來三大部譯稿,對(duì)康德術(shù)語表示自己見解,所提譯名"跡先。出現(xiàn)。驗(yàn)前"等都與常見譯法大有徑庭,而且顯然構(gòu)詞特別,頗刺眼。陳決定不予強(qiáng)改,同時(shí)將韋函發(fā)表于新創(chuàng)內(nèi)部通訊《譯書消息》,實(shí)際通報(bào)學(xué)術(shù)界予以考慮。同時(shí),韋譯就一部一部上市流通。韋氏游離于當(dāng)時(shí)哲學(xué)界,說他治康德,并沒多少人知道。陳不聲不響予以支持,需要膽子。
綜觀人文學(xué)科,從術(shù)語一個(gè)角度看,學(xué)術(shù)上有人關(guān)注與否,肯大力推動(dòng)與否,大有關(guān)系。看近年,西方哲學(xué)史書目,外國(guó)哲學(xué)術(shù)語,對(duì)照,詮釋,或?qū)5浠蚋戒?出版不少,報(bào)刊常發(fā)表議論術(shù)語的文字。加入了世貿(mào)組織,但愿眾學(xué)科能聚成股股合力,加快這項(xiàng)基本建設(shè),直到最后整合成功。術(shù)語工作盡力擺脫不經(jīng)意狀態(tài)似在望。
且容下篇以u(píng)nderstanding八十年經(jīng)歷為例,繼續(xù)探討。
作者聲明:本文曾提到過的汝信所作比喻分為兩截,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術(shù)語多探討,容許保留譯法,不強(qiáng)求統(tǒng)一。與會(huì)學(xué)者正確理解這比喻,欣然歡迎他這表態(tài)。即是比喻,難免有欠缺。強(qiáng)調(diào)了后者(術(shù)語),對(duì)前者(人地名)就顯出重視不夠。當(dāng)時(shí)并不討論人地名,誰也不屑于費(fèi)心思考對(duì)人地名應(yīng)如何這問題。本文這里仍以當(dāng)時(shí)背景引用。
看近幾個(gè)月,9·11涉嫌者人名雙包案未了,媒體上本·拉丹/拉登雙行。又出現(xiàn) Al Qaida / Quaida /Qaeda,地名雙包案和 Muhammad H.Heikal,人名雙包案。
前者,新華社據(jù)阿文讀音規(guī)則,阿漢譯音規(guī)則確定譯名為"本·拉丹"。《參考消息》《人民日?qǐng)?bào)》采用至今。多數(shù)媒體未接受這公認(rèn)的譯名準(zhǔn)則,而愿隨俗誤讀,從英語本位將錯(cuò)就錯(cuò),堅(jiān)持各自原所用譯名"本·拉登"。《參考消息》對(duì)此三次答讀者予以說明解惑。肯定新華社譯名準(zhǔn)確外,對(duì)于譯名不統(tǒng)一事,除介紹《人民日?qǐng)?bào)》接受所作說明,糾正了譯名之外,未多議論。
由此看來,社會(huì)上如今對(duì)人地名態(tài)度,采取了1982年汝信所提出對(duì)術(shù)語的態(tài)度。這樣,大家可從長(zhǎng)計(jì)議,非常好。二十年后,眼光遠(yuǎn)了,思慮深了,肚量大了,可喜可賀犝飫鏌作聲明者,以今論昔,如果有讀者指責(zé)汝信當(dāng)年不應(yīng)那樣對(duì)待人地名,于理而言,所據(jù)不可謂不當(dāng),于情而論,所言則顯然不宜。退一步說,這雖可看作可喜的誤會(huì),畢竟此一時(shí)彼一時(shí),而誤解之起則應(yīng)怪本文事先未征詢他意見。
話說回來,《博覽群書》2001年第12期(10。12頁)出現(xiàn)將新華社意譯為"基地"者,音譯為"阿爾·卡耶達(dá)"。此事,歡迎讀者表示意見,以推進(jìn)譯名討論。此等事,不強(qiáng)求統(tǒng)一固然好,不推進(jìn)統(tǒng)一則未必妥。這也就是本文所建議的擺脫不經(jīng)意狀態(tài)。讀者以為如何!
埃及記者海卡爾(1923--。)在12期文中譯作默罕默德·赫卡耶爾,這里宜尊重通譯。作者的行文習(xí)慣與我們本就不同,人地名雙包徒增閱讀障礙,造成混亂。終歸一句話,術(shù)語工作是基礎(chǔ)性質(zhì),糧草應(yīng)先行早動(dòng),總是坐而論道,原地踏步,必成廢物,術(shù)語社會(huì)學(xué)每邁一步,所關(guān)非小,歡迎讀者監(jiān)督推動(dò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