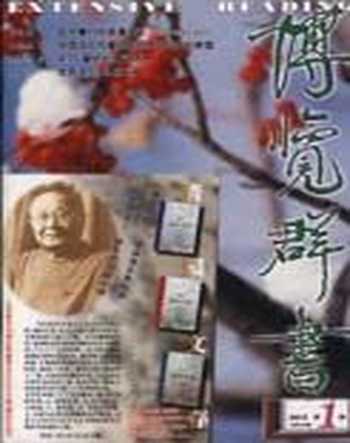開卷有益 掩卷有味
夏一鳴
聞一多先生說過,四個古老民族差不多同時開始唱歌:印度人和希臘人是在歌中講著故事,而《舊約》里的"希伯來詩篇"和中國人的"三百篇"則是抒情詩。中國從《詩經》。《楚辭》到唐詩,有熱衷于寫抒情詩的詩學傳統,而講故事。演戲是比較晚出現的,小說。戲劇要到宋以后才繁榮起來。
聞一多先生還說,中國文學在元代才算是"故事興趣的醒覺"。他推斷,按文學的世界化趨勢,詩歌將不可避免地退隱到歷史的一角,而"故事"將主宰整個文學史。
應該說,后來的文學實踐證明,聞先生對文學發展的宏觀把握是比較正確的,但是他對故事在歷史上的形態則沒有看得很清楚。中國故事實際上來源于兩個系統,一個是它的文本系統,另一個就是它的世俗系統。前者掩藏于中國早期的諸子百家學術中,而后者的原生態雖說我們今天仍無法鉤沉,但它們肯定是大量地存在著。
有專家作過統計,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國積累的民間故事書面資料就已達十多萬篇。八十年代以來,在文化部統一部署下,為編纂出版十大民族文藝集成和志書,開展了大規模民間文學的采風活動,記錄到各地民間故事一百八十多萬篇。就此數量而言,這是其他任何一種文體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到了今天,隨著人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傳播信息渠道的多元化,故事的文本系統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我們看到這兩個系統有時會結合起來,形成故事的"第三條道路"。比如,不少學者教授演講時,不再像以前那樣引經據典。大掉書袋了,而是不時地插"科"打"諢"熓抵噬鮮切」適攏牎K們這個小故事可能是自己的心得,也可能是從別的地方借鑒而來的,但是我們看到那些故事在未來的日子里就以不同的版本形式在民間到處流傳。
早幾年前,《故事會》編輯部同仁就醞釀著一個理想主義的夢,那就是在故事的旗幟下好好地編它幾本故事書。它要以"故事"為視點,以"大故事"為視野考察故事本體。它遠可以是五千年流傳不絕的傳統民間故事,近可以是我們身邊發生的點點滴滴;左可以是學者作家的清談雅謔,右也可以是老百姓的油鹽醬醋茶;上可以是都市流行的新傳說,下也可以是充滿鄉土味的龍門陣......總之,我們的原則是大凡有意趣。有意義。有意味者,統統可以收羅到我們這個系列中來。
當然,它們必須是同一類別中的精品,是已經接受了讀者的檢驗,并將經受時間的檢驗的。且以民間故事為例,據悉印度古代有三部故事集,其中有一部就叫《故事海》。我們認為這既是一種形象的稱謂,但道出的卻也是實際。說它是海,其意不但在它的壯觀,而且也在于它的量多。中國的民間故事數量之多,是不在印度之下的。現在要把它搞成一個選本,那就不但要有全本的視野,還要有定本的手段。可以告慰讀者的是,這個選本目前應當說是中國的惟一的民間故事代表作。"故事精品系列"中的其他幾本圖書,也莫不如此。
它們除了提供密集性的信息之外,還將保證這些信息的有效性。有一個作家曾把人生經歷劃分為五個時段:圖畫。故事。小說。哲學和宗教。青少年讀者即對應"故事"這一時段。因此,可以說我們編輯的這套書主要是為青少年服務的。我們編輯的宗旨是,青少年讀者要把讀書當作一次愉快的精神旅游。大家可能還記得,在一年前的一次高考中,有個考生把《故事會》上的故事"搬"到了作文中得了個滿分。事后人們對于這個行為的評價見仁見智。但人們卻沒有進一步地想:這個學生在閱讀故事時基本上是無意識的,為什么他會對這個故事記憶猶新。用前面的話來說,這是文本系統對世俗系統的作用。也是故事的秘密之所在。
編輯部誠希望這套書能合于兩個方面的要求,這就是"藏"與"顯"。所謂藏者,就是把它們放在柜子里五十年,拿出來還鮮活亂跳,通體散發出一種文化的生命力,而不是靜靜地站在書架上忍受著塵灰的侵蝕。而所謂顯者,就是相信它成為一種"行走的文學",能活在讀者的眼睛里,活在讀者的口頭上,合著讀者的生命節奏一起躍動。
"故事精品系列"包括《青春讀本》。《滴水藏海》。《名家特稿》。《智慧寶典》和《另類故事》五種,上海文藝出版200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