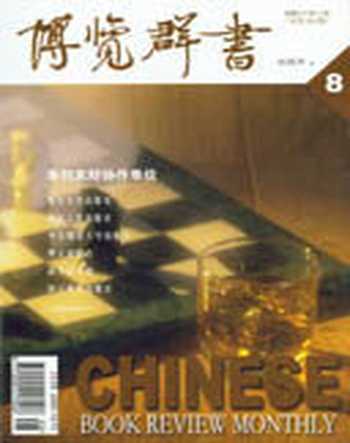遠從硅谷望江南
葉子南
案頭放著一本主題是江南的臺歷,是一位朋友來家中作客時送的。這位朋友原在硅谷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任職,現在杭州附近辦了一家公司,為此不得不來往于硅谷和江南之間。那天夜里,這位古道熱腸的企業家帶來了一些江南的特產,有遠從杭州買的小核桃,有太太親手包的肉粽子,加上我自備的女兒紅,菜肴算不上豐盛,但把酒舉杯之間,坯是想起了“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的句子。一夜風雨,幾位故人,一壺濁酒,便把我從硅谷帶回了遙遠的江南。
一
我是在冰天雪地的北國長大的南方人。六十年代中期,我隨同父母從東北回到老家紹興。第一天從鄉下坐船進城,便領略了孩提時母親常常提到的江南水鄉。天還沒有亮,客船便已經出發。一路上,搖搖擺擺的埠船或行于兩岸的青山間,或走在寬闊的河道上,長空上幾顆孤星,江河中幾艘孤舟,船艙內幾個孤客,如詩般的江南就這么如畫般呈現在我的面前。同行的船客都被柔和的櫓聲帶人了夢鄉。我坐在小船中,輕輕推開艙棚,注視著船外朦朧的景致。客船駛入中途的小鎮,依稀可見早起的農家姑娘已在河邊汲水,沒多久,小舟駛出村落,伺首但見村莊內兩三農舍上已飄出縷縷炊煙。櫓不停地搖,水不停地流,船不停地行,我們的小船已經離古城紹興不遠了。河中的船只越來越多,岸上的人群越來越密。天已經蒙蒙亮,隱約可以聽到不遠處集市里的吆喝聲。我突然意識到,原來自己已遠離了那個度過童年歲月的工業城市‘來到了生活步調緩慢的江南水鄉。』、鎮的一天即將開始,而我的人生也馬上要重新啟程了。
這以后,身臨其境,我對江南的風土人情有了更深的體驗。登府山,同學對我說,山上有宋代的樓臺;游鑒湖,親戚告訴我,湖水是名酒的來源。對古城略微熟悉后,我常一人在城內漫游,找到了陸游的故居,拜訪了秋瑾的庭院,攀登城中的應天塔,遠望城外的秦皇山,古城內外似乎每一處都有一個歷史故事。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城中默默無聞的小巷和彎彎曲曲的河道。在我看來,這一條條巷,一道道水,要比那大名鼎鼎的名人遺址來得重要,因為它們是小鎮風貌的點睛之處。我常常在小巷深處徘徊,在石板橋上獨立。這些對當地人來說并不引入注意的景觀,對我卻十分重要,成為我性格形成過程中的塊塊基石。二
江南的與眾不同不只因為它獨特的景觀,更是那里的文化。江南人都會自豪地歷數曾在這片土地上留下足跡的文人雅士。白居易一聲《憶江南》,寥寥數筆,皴染出最能代表江南的兩個景觀;余光中筆下那乾隆皇帝的江南,酒旗招展,也令我們魂牽夢繞。我們有說不完的魯迅的故事,吟不斷的陸游的詩行,唱不絕的秋瑾的悲歌。但在我看來,江南文化的靈魂卻并不全在這些詩文中。詩文固然偉麗,但那畢竟只是一部分人興之所至而吟唱的陽春白雪,尚未滲透到蕓蕓眾生的靈魂深處。文人雅士營造江南的高雅文化,而普通的江南人卻編織出江南的大眾文化;江南的靈魂逡巡于蕓蕓眾生中。,
不信,你去看清晨江南小鎮中的菜場。青翠碧綠的蔬菜,活蹦亂跳的魚蝦固然讓你確信身在魚米之鄉,但更能體現江南風情的是菜場里的人。我最喜歡看集市中買賣雙方討價還價的場面。那是今日商場如戰場的談判桌上見不封的充滿人間氣息的協商,進退得如此意外,成交得如此大方。為了幾毛錢,買賣雙方據理力爭,買方聲言集市中龜攤不少,并非只此一家;賣方則宜稱菜場中攤位無數,可論質量,無人可以與他相比。一個堅決不買,一個硬是不讓。買主無奈轉頭離去,看樣子這筆交易已經告吹,卻不料在買主快要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時,賣魚的小販突然追上前去,一把抓住買主,口中念念有詞:“算我今天倒霉,拿去吧!就照你的價拿去!我老婆還等我這幾個錢去買雙布鞋呢。”隨后,他竟不厭其煩地向買主傳授起烹調鮮魚的訣竅。買主也不含糊,幾分錢的找頭也不要了,還不停地保證下次一定再來他的攤位買魚。
有一首寫江南的歌,記不得是誰寫的,大意是:江南人留客不說話,只聽小雨細細下。在南方水鄉作客確實別有韻味,留客的是江南的雨,也是江南的人。有一次到一戶農家轉告一件事,本打算馬上就走,卻被主人挽留,幾番推辭后,主人居然說,如果這次不在他家吃飯,那么以后就再也不要來往了,一面說著,一面用手緊緊地抓住我的衣服,他的幾個孩子竟抱住了我的腿不讓離去。如此盛情之下,你怎能掙脫那雙溫暖的手竟自離去?頃刻間,一桌熱騰騰的飯菜,一壺香噴噴的米酒已擺在你的面前。待你的碗中堆出了魚蝦的小山丘,主人在一旁微笑了。正是這一個個普普通通的江南人,釀造了市井文化的醇酒。春江水暖時岸邊洗衣的姑娘閑話各自的情郎,春雨蒙蒙中屋內養蠶的少婦訴說心中的惆悵,農人豐收后的歡笑,店主年關前的苦惱,舊岸殘橋邊緩緩而行的老翁,閑庭舊院中紡紗織布的老婦”…它們是越調紹劇的源泉,評彈說唱的依靠,離開了這些江南文化的風景線,江南這幅畫也就黯然失色了。 獨特的江南風貌以秀麗的山水為背景,普普通通的民眾為依托,加上文人雅士用詩文推波助瀾而構成。華夏大地,秀麗山川并非江南所專美,文人雅士也不是江浙獨有,古道熱腸的民眾更是比比皆是,但這三者在江南結合得恰到好處,使江南文化獨具一格,殊難臨摹。
三
江南獨在何處,特在哪里呢?在我看來,江南的特色是小和慢。江南文化從不以大和快為衡量的規矩。以雄偉作標準,用浩瀚為尺度,江南的水江南的山只能敬陪末座。可是江南的青山卻在蒙蒙細雨中釀造翠綠的生機,江南的綠水在舟楫小橋間流出悠閑的韻味。溫和的自然環境最容易孕育一種緩慢的生活節奏,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中,江南人才能吟出了“卻借烏篷舟‘葉,飄然臥聽水流聲”的句子。而即便是在爭吵打斗時,江南人也顯得溫文爾雅。”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乎”的英雄豪杰,大都在大漠孤煙之處,白山黑水之間。江南文化以小慢陰柔為特征,比較適合在細處晶鑒,卻不宜從大處觀賞。這樣的文化從根本上看,是一種陰性文化,任何具有大快陽剛特質的人與物在江南文化里都可能破壞江南的意境,顯得格格不入。
四但是,江南文化目前正面臨一種前所未見的陽剛文化的沖擊,這就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現代化以快為節奏,全球化以大為楷模,人們用商業作為媒介,乘因特網的“小舟”,在電子“高速公路”上暢通無阻。這幅二十一世紀的時代縮影和傳統的江南意境顯得極不協調。不錯,江南的山依舊翠綠;但高聳的建筑卻遮斷了江南人的視線江南的水照樣柔和,但機器的噪音卻驅散了河上的寧靜。青石板的小街被柏油造的馬路取代,慢悠悠的埠船讓位給了急匆匆的汽車,街頭熙熙攘攘的集市不得不與樓內次序井然的超市爭奪顧客。魚攤上殺價賣魚的小販正苦苦地等著當年的顧客,他的舊買主也許正在超市中挑選魚蝦瓜果,免除了討價還價的麻煩。一種更認同速度,更注重方便,更器重實用,更講究表面的文化正在掠獲人心。江南人怎能不變?和江南的老鄉交談,言談間聽不到“哪里,哪里”的寒喧之語,取而代之的是“謝謝,謝謝”。從“哪里”轉到“謝謝”,語言的功能依舊,語言使用者的視角卻變了。你與朋友的千金聊天,豆蔻年華的少女,侃侃而談未來致富的夢想,毫不掩飾地告訴你,希望嫁個有錢的郎君,惹得朋友哈哈大笑。你也跟著笑起來,知道那是孩子的戲言,但心中卻若有所失。那位硬要留客吃飯的江南人此刻正忙著一筆生意,你去拜訪,他熱情如舊,但卻無暇再請你品嘗自家釀造的米酒,要請你去豪華的酒店,用“人頭馬”讓你一醉方休;你略加推辭,也就主從客便了,市井文化變了,高雅文化焉能不變。現在還有多少江南人熱衷于前輩們寫下的詩文?
為了文化的傳承,人們修復殘舊的古跡、名人的故居,煞費苦心。心中惦記的與世貿如何接軌,和世界怎樣溝通的江南人,偶爾飲一杯薄酒,也許確能消除疲勞,但畢竟澆不出滿腔的水鄉情懷;傳統意義上的江南只是夢中畫墮的仙境,與紅塵決然隔世。江南文化的核心其實已不復存在,,我們實際已經失去了傳統的江南。
五
正是在這個文化語境中,:西方現代社會學有關“懷鄉嚴情結的研究便可以拿來當作他山之石。Nostalgia(懷鄉)這個詞是西方學者用來描寫現代化環境中人們的懷舊情結的。正如哈佛大學教授斯瓦特拉娜·波依姆在她《懷鄉的朱來》(TheFuture ofNostalgia by svetnala Boym ,2001)中所說:“懷鄉是對已不存在,或者說根本沒有存在過的家園的一種懷念。懷鄉是一種若有所失、流落他鄉的情感,但它也是充滿遐想的浪漫情懷。”我曾百思不解,為什么家園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我明明經歷過那個小橋流水的江南,為什么說它并沒有存在過?我初識江南時,正是中國歷史上動蕩的年代,那場運動對國家的破壞當然很大,但它對傳統江南文化的破壞,我看卻遠不及現代化或全球化。廟宇是被搗毀了,遺址也被拆掉,詩文古董被付之一炬。但青山依舊,綠水如常,市民仍舊在集市討價還價,船夫還在水上搖櫓推槳,不少人反倒是在那個時期讀了大量的古代詩文。江南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其陰性文化的特征并未從根底上動搖,因為那場運動的本質仍然是中國式的。那么怎么理解江南并未存在過這種說法呢?我在《懷鄉的未來》中似乎找到了答案。作者說“初一看,懷鄉是對一個地方的向往,但實際上,它是對不同時代的懷念,對童年、對夢中更為緩慢的節奏的懷念。”換句話說,懷鄉是對現代的反抗,是對進步的示威,因此懷鄉者不必鎖定某一特定的空間作為懷念的對象,因為真正的故鄉其實并不存在。六十年代經歷的江南是我懷念的故鄉,但它也許正是我的父輩感到昨是今非的地方,因為在他們夢中看到的是一個更純正的江南。
或問:你怎么一下要將自己全盤否定?其實這并不是此是彼非的否定,因為舊江南和新江南之間的吊詭正是懷鄉和進步之間的矛盾。用波依姆的話說:“懷鄉與進步就像《化身博士》中的杰克爾與海德一樣”。把懷鄉與進步看成勢不兩立的對壘,還不如把它們當作是陰陽共存的互補。由于懷鄉不僅是若有所失的悠悠情思,它更是充滿遐想的浪漫情懷,所以不妨從懷鄉中汲取生命的能量,讓它成為繁忙工作后供精神休閑的“涼亭”,把它當作日夜兼程中時時歇腳的“驛站”。我們不妨再聽聽波依姆的看法。
六波依姆認為懷鄉可以大致分為兩類:返歸性懷鄉和反思性懷鄉(RestorativeNostalgia and Reflective Nostalgia)。返歸性懷鄉強調過往家園的重建。返歸者要把過去的價值當成現時的圭臬。在他們眼里,過去不是一段可以解構的時間,而是定格在照片中的完美畫面,畫中的一切都不會褪色,永遠鮮艷。返歸者生活在并不存在的完美之中,熱衷于宏觀的象征,卻不顧微觀的細節,在返歸的途中高高舉起反現代的大旗。可是,反思的懷鄉者卻緩和得多。他們能靈活地詮釋過去,不耿耿于機械地恢復過往。反思者認識到,過去并非絕對正確,反思意在沉思,沉思則應注重個人的回憶,因而不主張象征性的總體返歸。反思者在懷鄉道上居然能與現代化相敬如賓。
在辨析返歸和反思的過程中,我們無可奈何地承認了一個現實,傳統的“樂園”不可能失而復得。在全球化的今天,原封不動地返歸傳統的江南文化只能是緣木求魚。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只能在現代化的潮流中隨波逐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量保護江南文化的遺產當然應該提倡,但不必對這類杯水車薪式的努力寄予過大的希望。力挽狂瀾式的返歸從來就沒有在人類的歷史上真正發生過,因為那樣做的代價是犧牲所有進步的成果,而人類是不愿意放棄這些成果的。不過,我們應該能在反思的過程中,在若有所失的淡淡憂思中,汲取向前走的力量,在我們經歷精神沙漠的時候,行囊中那一壺傳統的水也許能夠解救我們,帶我們走出不毛之地。從這個意義上說,懷鄉的目的不是著眼過去,而是章在未來。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江南文化實際并不一定在江浙那塊土地上。假如懷鄉是對過往的眷戀,那么身在江南的人也能感到遠寓故鄉,假如懷鄉是對未來的憧憬,那么遠在天邊的人也不會覺得流落異鄉,因為在每一次回憶中,在每一次閱讀中,在每一次交談中,我們都能神游那個夢中的故鄉,因為在我們心中的江南與我們形影不離。
那么就讓我們在遠離扛南的地方,沏一壺江南的龍井,打開一本江南的畫冊,讀幾句江南的詩吧;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
注:哈佛大學教授斯瓦特拉娜,波依姆所著《懷鄉的未來》一書原文是:The Fu-tureOf NostalgiabY Svcmala Boym(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