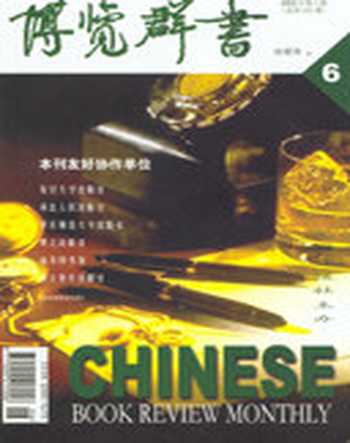未了的心愿
何家棟
意想不到的打擊是最沉重的,沒有預感,沒有征兆,災難說來就來了。哲人其萎,朋友們無不感到震驚、愕然,繼而是深深的悲痛。慎之已經走了七天,我仍然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見面都有“相見恨晚”之意,我倆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長幾個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人救亡運動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陽謀”。我們都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才發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門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氣象,他比我幸運的是受過完好的正規教育,厚積薄發,而我卻是掃盲把我掃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堆里的,實際上只是“脫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后約我見面,談話時他就給我出了好多作文題目,我趕快聲明:我不是做學問的人,幾十年來都是給別人編文章,改文字。寫的文章也不過清通而已。他說清通就不簡單啊,有些自命大學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說:寫的那些東西不過是要表明一種立場,在我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能邊做邊學,請一些中青年朋友給我上課。有些文章實際上就是“集體創作”。大概慎之也理解這不是過謙之詞,因此,第一次見面之后,就給我寄來了一些材料。慎之最后一次命題是詹明信上海講話招來一場圍攻,要我就此事寫個評論,并且請人送來相關資料。文章發表后(載于《博覽群書》刪2年12期),意猶未盡,又另寫了一篇雜感,但慎之已經看不到了。
慎之認為比四個現代化更重要的問題是“人的現代化”,一直為此大聲疾呼,“公民教育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還說:“如果一個人真的還有下一輩子的話,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輩子當一輩子的中學公民教員。”他的想法得到廣泛的贊同,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還拿著《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等文章去訪問他。我對慎之說:“既然是刻不容緩,何必等下一輩子呢?咱們不妨現在就干起來。”他問我有什么辦法,這倒把我問住了,我不過是受他的啟發和激勵,感到應該有所作為,哪有什么辦法。回來我就找幾個中青年朋友商量,請李先生來主持,完成《公民課本》這一有歷史意義的大工程。大家聽說李先生可以“出山”,都表示愿意效力,起草了一個“研究大綱”,還制訂了一個“課題計劃書”,以三年為期,第一年完成《中國歷史上的公民教育》、《世界各國公民教育的比較研究》;第二年制定寫作大綱,寫出公民課本初稿,共12冊,初中、高中各六冊;第三年,定稿,推廣。由幾位中青年學者組成編委會,由慎之總其成。我對公民教育的認識也隨著工作的展開而加深。中國教育體制、教育內容的弊病,我是有體會的,一切指向分數、指向工具塑造,忘記了教育的宗旨應是培養具有時代精神、為社會延續、增進文明的常人,也就是具有獨立自主精神與人文關懷,懂-得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合格的現代公民。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現象:對兒童進行成人教育——“胸懷全球,放眼世界”;對成人進行兒童教育——“要學會說謝謝、對不起”;“不隨地吐痰,上車排隊”……所以,我以為“啟蒙運動”不能老停留在知識分子的議論中,而應在民間扎根。如果以公民教育為切入點,面向全社會,我們就會取得全民共識,形成合力,推動文明進步。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從美國歸來,詢問公民教育進展情況,并且給我寫了封信:“……知道先生已著手開始公民教材的準備工作,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夠成立‘公民教育研究會,那就是可以千秋萬代的工作,我們這一生就可算有一個目標,也有一個歸宿了(對我們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雖然很低調,但興奮之情溢于言表。他還把許多支持者的信轉給我,要我同他們聯系,有的信還批上:“又是一個公民教育的積極分子!”
但是,工作卻越來越難以為繼了,后來種種壓力迫使我們的工作陷于停頓了。
這一切似乎都在慎之的意料之中,他寫信勸勉我說:“……我又想了一想,教科書固然編不出來,但是寫一本《現代公民試行教程》似乎還有可能。……法國革命以前有‘百科全書派對啟群覺悟起了重大作用,中國當然主客觀都無此條件,但是幾萬字的一本《公民教程》也許能起到‘統一思想,喚起民眾的作用(照民主國家的原理,任何人都無權、‘統一思想,《公民》正要告訴人們這一點。但是我偏偏想不出別的詞兒,姑且借用,也許可以證明我中毒極深,已脫不出過去的框框了)……如果我們能編出一本公民教程來,對政府與人民,中央與地方,立法與行政,行政與司法,立法與司法的關系……都有順應世界潮合乎文明原則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樣的英雄好漢敢來挑戰。當然目前似無出版的可能,但是要有一部稿子在那,我看是隨時都可以有用的。說到統一思想,我想也好乘此機會把主張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人彼此弄清楚,也許能得到更多的朋友。”我立即回應說:百科全書不敢想,一科全書尚可行。“公民教育會”若成形,未必有人敢說“不”。開始時并不是沒有想到經濟實力不足以支持我們的研究,但我總認為行動起來,條件會發生變化。可是,只見人錦上添花,卻不見人雪中送炭,我們雖一退再退,但從不言放棄。直到去年年終,慎之還在約人參加編寫《公民課本》,可見慎之在這個問題上始終沒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說:“頑強奮戰后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這不過一次小小的挫折,我們永遠也不會接受失敗。我相信慎之設計的《公民課本》或《公民試行教程》是一定能編成的。慎之的第二個心愿是“重新啟蒙”。他認為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五四運動是夭折了,先是救亡壓倒啟蒙,繼而革命壓倒民主,最后是穩定壓倒自由。所以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啟蒙。”它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才應該是被中國定為國家目標的‘現代化的出發點與目的地”。“中國人民必須從在自卑與自大之間失去平衡的阿Q轉變成為能自尊自律的現代公民”。
八十年代,王元化人等就提出“新啟蒙”的主張,他們編輯的《新啟蒙叢刊》,曾經產生廣泛的影響。現在,“回到五四,重新啟蒙”再次提了出來,應和者寥寥。我覺得必須說明新啟蒙和老啟蒙不同的地方,老啟蒙是要破壞一個舊世界,新啟蒙是要建設一個新世界。這一點不講清楚,就會招致誤解。慎之對于“重新啟蒙”的貢獻不只限于文化層面,而是全方位地投入社會變革,推動公民社會的形成。
回到五四,還要超越五四。慎之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還是要感謝歷史的發展到二十世紀最后結束的時候,中國舞臺上各種可能有的思想總算已經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進行戰斗,‘敵我友的關系(還是要借用毛澤東的話)可以比較明確,再不致被拖人一場混戰了。我的看法是,當面的敵人就是一個,就是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兩百年的專制主義,雖然它已因自身的腐爛而日趨軟化,但極權的本性未變。要救治專制主義,只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以至個人主義,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四)
慎之的第三個愿望是“把顧準的民主啟蒙的思想推向更廣更深”。因為“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潮本來就不旺,它是在滅絕三十年之后經由顧準這點火種才又開始重燃起來的”。顧準是在看到權力發生異化,革命理想主義轉變為專制主義之后,才毅然走上經驗主義之路的;李慎之在“割肉還母,剔骨還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義。我們對“告別革命論”都不能理解,這是對過去的悔恨還是對未來的輸誠?如果是過去,我們需要懺悔的可以是任何事情,惟獨不是革命;如果是未來,那由不得我們。我們想告別革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別我們?民主是消解革命準一的手段。如果社會矛盾沒有緩解機制,那就會像恩格斯說的那樣:“最小的沖突也要引起嚴重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517頁)。
”
慎之說過,他是戰戰兢兢提出自由主義的。它成為一個歷史事件,不在于他對自由主義的理論有什么新發展,而在于歷史條件把他推到時代的潮頭上。他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學問家看重著作等身,精雕細刻;思想家要求振聾發聵,星火燎原。一個以書齋為發祥地,一個以社會為實驗場。李慎之努力為自由主義爭得合法地位。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這件事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我才提出要重新確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承前啟卮的新道統,其主鏈應是梁啟超——胡適——顧準——李慎之。
,
顧準、李慎之對于我們有什么價值?他們講的也許不過是常識,其社會意義遠遠大于它的學術貢獻,其思想價值遠遠大于學術價值占在我看來,慎之最大的價值還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為,他的身教,他的榜樣作用。喻希來曾寫過,在群情激奮時,要強調知識階層的冷靜和清醒;在“萬·馬齊喑”、“百念俱灰”的時候,要呼吁知識階層的熱忱和忠諫。知識階層應當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求得某種平衡,,把進取精神和慎重態度有機地結合起來。知識階層能否堅持穩健、公允、平實、持久的思想路線和政治態度,而不為任何風吹浪打所動搖,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一個關鍵。慎之的特殊意義就在于,在知識階層的思想再次發生動搖的時候發出了:堅持現代化導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將自由民主確立為全球價值的時代的最強音。對于慎之來說,這種忠諫的對象是自己的祖國與人民。兩年前我曾說過:“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義大旗,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國思想史上卻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歷史將會證明,顧準和李慎之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慎之對一些“在美國喝過洋墨水的新左派”,似乎懷有一點戒心,但對于不同意見表現出的寬容精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為一次全國性學術評獎提名,選了一本他并不喜歡的著作,他說:“不能以個人好惡為標準”。這部著作雖然落選,但他仍堅持自己沒有看錯,說:“它確實自成一格,雖然我不喜歡它。”連反對他的人都不能不贊賞慎之的公正。慎之的這種寬容與公正,很好地體現了自由主義的風范。
慎之是思想者,又是組織者,他是在立功之后才立言的,那些有影響的文章是他在去職后寫出來的。說他的文風屬于“新華體”,不如說他更接近“啟超體”,議論恢宏,酣暢淋漓。慎之似乎一直保持苕,“新華作風”,看到他認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問題,或有獨到見解,都一一復印出來,以饗同好。·慎之學問功底深厚;博聞強記;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在聚會時。常見他議論風生,滔滔不絕;使我感到他內心也許有一種“時間不多了”的緊迫感,他有那么多問題,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傾囊倒篋而出,形成文字。“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滿腔熱血,一片赤誠”,如果不見他行走略有不便,誰也不會想到他得過輕度中風,但上樓下樓都是拄著手杖,緩緩移步,不愿別人扶持。
誠然,顧準、李慎之在中國思想史上都是過渡人物。任何一個思想開拓者,對于后人來說都是過渡人物。只有自認為掌握了終極真理的人,才會看不起過渡人物。能夠讓匆匆離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繼者已經形成隊伍,繼續攀登思想高峰,還有浩浩蕩蕩更年輕的一代。“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慎之,你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