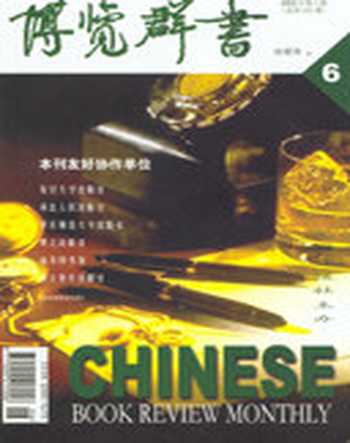尋找歷史的責任者
薛建華
百年近代中國,簡而言之,即是一個被迫置身于世界大家庭之中,遭受一連串的創傷以后,痛苦地自我反視,失落自信又重樹自信的過程。自然,人的天性中,包含承受挫折的耐力,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長久地浸泡在災難中的民族,似乎應該能夠承受得起,能夠崛起自強;但,鴉片戰爭以來的沖擊是異乎尋常的駭人的沖擊,傳統的權威的政治系統被沖垮了,悠久的引為自豪的文化根基也同時動搖了。這樣的局面,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另一個民族遭遇過。我們二十世紀所遇到的并力圖解決的問題,也許是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數百年間所遇問題的總和,而且是在世界政治、經濟發展最快、變化最大的背景之下。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正是一部尋求救國之道的著作,全書充滿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
蔣廷黻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留美博士,著名外交家,他的史學觀深受其導師、哥倫比亞大學史學教授海斯的影響,持西方的實證史論,即“科學史學”的方法論。該書寫于1938年,正是中華民族再次面對存亡的歷史時刻。作者擅長于把中國的近代史實放之于錯綜復雜的世界大氣候之下,作全面而宏觀的透視,筆調極冷峻又極熱忱‘。其熱忱處,一字一句間,無不浸透了作者強烈的愛國心,那種渴望祖國強盛的赤子情懷直欲催人淚下;其冷峻處,剖析民族不得發展、國家不思進取的緣由,痛悼由此喪失了發展的時間,致使古老的文明之邦與西方新興國家之間拉開了越來越大的距離。
在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前,中國與西方沒有外交,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作匈奴人、琉球人看待,我們是“天朝”,他們是“蠻夷”;英國使者兩次蒞京要求以和談的方式展開外交,均被視為狂妄,橫遭拒絕;那時,甚至還禁止西方的商人買中國書、學中國文字——大概以為他們不配吧!物換星移,我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依然是中古時代的,而西方的近代文明一天天發達起來,也漸漸地讀懂了“天朝”,不過如黔之驢,大則大矣,其技已窮。他們毫無顧忌地向中國傾銷鴉片,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而無效果;嘉慶初年,輸入竟加十倍,嘉慶下令禁止人口,但“因為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困難”,繼續增加;道光十五年,加到了每年三萬箱。全國上下都認為這是國計民生的大患。然而,要禁煙卻十分困難,一方面境內的情況就極為復雜;另一方面,鴉片是當時英國財政的大宗收入,他們絕不愿我們禁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林則徐被道光任命為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查辦煙禁”。當時的人心世態是怎樣看待這件事的呢?蔣著中說,“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煙的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我國士大夫階級大毛病之一。”林文忠公畢竟是士大夫中的杰出者,他辦事認真,聲望很好,同時也是真正具有自信的人。外國人不知林則徐的品格,以為他不過是一個普通官僚,當英國的商業監督義律向林交出二萬多箱鴉片時,他們想,林則徐這下要發大財了。不意這兩萬余箱鴉片悉數化為灰燼,燒了23天,西人前來觀看者,也不得不深贊欽差大臣的坦然無私。當時全國都很樂觀,皇上以為至此平安無事,要調林則徐去做兩江總督,但林不肯,他還想把事情辦得徹底一些。。而英國方面接到義律的報告后,就派全權代表懿律率海陸軍隊來華;不但索要鴉片賠款、軍費賠款,而且要求一掃舊日所有通商限制和不平等條約。大兵壓境,昏庸的朝廷一下子慌了,先是上諭罵林則徐,并革了他的職,用投降派琦善接替林的職位;后來又將琦善革職鎖拿。朝廷在主戰與主和之間搖擺一陣之后,方調兵遣將,與英人交火。但“軍器不如人,自不待說,紀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諱言”,屢戰屢敗,英軍直逼南京之際,朝廷沒有辦法再抵抗,只得接受英國的要求,簽定《南京條約》,次年又簽定《虎門條約》(割讓香港即是其中之一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人提出香港時,北京方面還不知道香港在哪里)。
蔣著對鴉片戰爭前后的中西關系有精辟扼要的對比:“鴉片戰爭以前是我們不給人家平等,鴉片戰爭以后是人家不給我們平等。”
令人欲哭無淚的是,在民族遭受如此慘重的劫難之后,絕大多數的人并未因此而警醒,“戰前與戰后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他們一是堅信并非中國的“古法”不行,而是琦善收了英人的賄賂,趕走了林則徐,奸臣誤國;二是不服輸,他們堅信林則徐是會百戰百勝的,可惜他沒有機會與英國比武而已。于是乎,便雨過忘雷,絕口不提。所以蔣廷黻總結這段歷史時沉痛地寫道:“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的致命傷。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而且,在“眾人皆醉”之中并非沒有“獨醒者”,主戰與主和兩派中皆有人看清失敗的緣由。投降派代表琦善,就曾派人對英國的“軍器”作了一番研究,知道其船堅炮利遠在我國之上,“知彼知己”之后,他嚇趴了,腿軟了,所以決意投降退讓;主戰派的林則徐也看清了,可惜他受舊文化浸染太深,“述而不作”,思與行嚴重分裂。
,
正如蔣著中說,“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世人心目中的堅決抗敵的民族英雄,一個是慢慢覺悟了的清醒者。當初的林則徐,心目中也不無輕敵的念頭,未抵廣東之前,他說“本大臣家居閩海,于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還說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后來他發現并正視差距了,在廣東之際,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還派人翻譯外國的刊物。謫戍伊犁的時候,他與友人函中提出“剿匪”的八字要訣:“器良技熟,膽壯心齊”。他還收集了大量的外國資料,并將它們寄給友人魏默深。魏默深后來把這些資料編人著名的《海國圖志》一書,提倡“以夷制夷,以夷器制夷”。后來日本人把此書譯過去,促進了日本的維新。令人扼腕的是,林則徐將真實的自我包裹得很緊,他請他的朋友不要將他的信給別人看。道光二十七年,廣東巡撫徐廣縉上任時,向林則徐請教“馭夷之法”,林卻高調地回答;“民心可用”,豈不知用民心對外國人的炮火何異于自殺?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所依賴的民心終究未能阻止英法的節節進攻,反連總督巡撫都被俘虜了。
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進北京,朝野才敢于公開提出非學西洋不可!“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
誰擔當得起時代的責任?當民族國家危急存亡需要棟梁支撐的時候,偏偏是卑劣者“有所為”,而碩德者“有所不為”!是歷史誤人,還是人誤歷史?春秋責備賢者。琦善們在強敵面前奴顏婢膝,他們注定只能成為民族的敗類,誰也沒有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而林則徐們是能開風氣之先的,他們的思想與品德及社會地位巳夠火候,但他們偏偏沒有站出來!是怕背上“清議”或“偏激”的罪名,還是“崇洋”或”二心”的罪名?總之,他們不愿打破既定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名譽和社會的格局。蔣廷黻無情地批判道:“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含知識分子與官僚階層——由于歷史的原因,后一個群體大多來自前一個群體,二而一,一而二的,引者注)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
,
歷史最終成全了林則徐,道光死后,咸豐下令再度起用林則徐的時候,他已病重,不久去世,仍然沒有“與英人比武的機會”,名譽也因此得以保全了。
從辛亥革命前后到新文化運動,乃至更長的時間,眾多的知識分子僅僅把批判的筆鋒指向“國民性”,紛紛吶喊“喚醒國民”,并以此為己任。相比之下,蔣廷黻對中國士大夫的缺失與弱點的文化批判,獨具慧眼,更進一籌,顯得格外深沉而有力。
今天,我們的祖國正值邁向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重溫那段歷史,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