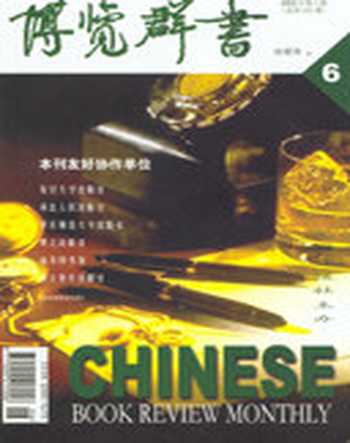走出中世紀·中國中心觀·權勢轉移
張仲民
在戰后《賬的一段時間,研究近代中國史的美國學者中間基本存在三種研究模式:“沖擊—回應”、“傳統—現代”與“帝國主義”,根本上,這三種模式都認為近代中國變革的動力來源于西方,是由于接受西方的刺激而引發的,鑒于此,實際上我們可以把這三種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書寫概括為一種模式:即“沖擊—回應”模式。后來美國史家柯文(Paul A.Cohen)在1970年代后期對戰后美國近代中國史研究中的這三種模式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以“中國中心觀”為主導范式來研究中國歷史,注重從中國社會內部來考察,把中國社會進行或縱或橫的分解,并借用社會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作為對三種以西方為中心模式來考察中國近代史的“反動”,柯文的“中國中心觀”能看到以往研究者沒有能注意到的許多面相,,并注意把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按層次和地域區分,這自然是很可貴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國甚至海外漢學界研究中國歷史的新動向,“這無疑是美國漢學界的新進步,當然是很不錯的,”(羅志田語)。另外,作為對“文化帝國主義”和現代性的反思,這種趨向也反映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如大約與比柯文此著略早的薩義德(Edward W.Said)就據出東方主義;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而日本學者則提倡“在亞洲思考”和“作為方法的中國“,稍后的弗蘭克(Frank,C)引起較大爭議的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n The AsianAge(該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推出劉北成翻譯的中譯本,改名為《白銀資本》)一書,更是明確鼓吹十九世紀之前的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其實弗氏論調并不新穎,我國臺灣史家全漢升早就提出過類似論點(參看其著《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系》,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冊,1957年,及其隨后的許多相關論著),有意思的是,全先生的研究遠比弗氏高明和扎實,可并不為太多人所知;弗氏《白銀資本》一書立論牽強處太多,但經過一批新進學者的鼓吹竟然在大陸學界非常走紅,一中一西兩學者研究成果的遭遇,正可見西方“沖擊”的效力和“中國中心”的疲軟。
實際上,遠在柯文之前,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名家孔飛力(Philipa.Kuhn)在其1970年出版的Rebellion and/0 Enemiesin Late lmperial China一書中,已經對“沖擊—回應”說提出了質疑,認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應該以舊秩序的衰落——傳統國家制度的毀滅與地方軍事化為著眼點,認為在西方大規模沖擊中國前,中國社會內部已經出現危機,新的力量已經在開始削騎中國傳統社會,如人口增長的過劇、通貨膨脹、鑄幣發行大量增加以及農村社會日益劇烈的競爭等,因此他認為以地方軍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可能比1840年酌鴉片戰爭更為合適。隨后,一批力圖打破“沖擊—回應”、“傳統-近代”、“帝國主義”三種模式書寫中國歷史的書籍也出現了不少,如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1974)、法國漢學家魏丕倍(Pierre-Etienne Will)的《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改》(1980)、王國斌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性》(1997)等,而且許多著作都越來越注重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從中國社會內部來考察中國近代史。
,,而比較早注意從中國思想界、學術界自身“內在理路”的演化人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國內學人是朱維錚先生,他在1987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紀》一書集中體現了他在這方面的思考。作為對《走出中世紀》一書的補充和發展,朱先生在1990年代初又關注晚清社會的“自改革”思潮,主張以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帝國士人開始呼喚的“自改革”來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朱先生的工作和努力無疑為我們了解中國近代史提供了新的視角,也增加了我們對近代中國諸多面相的認識和理解,其合理性很值得我們后來者在研究中給予重視和考慮。
相比于朱先生更多關注對中國社會內部變化的研究,中國學界近百年來尤其是前八十年則是把關注中心更多放在“西方”一方上,而對中國思想界、學術界自身“內在理路”的演化注意不夠,這個始經梁啟超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揭出的依據在西方沖擊基礎上的著名論斷:近代中國思想的演化由器物層面,然后是政治層面,再到文化思想層面,曾長期被許多中國近代史研究者所認可就是很好的明證。然而,就事實上中國社會的變化來說,很可能剛好與梁氏立論相反,實際上在西方大規模沖擊之前的五十年間,即十八世紀末,中國傳統思想與學術的危機已經出現和加劇,思想文化層面上的改弦易轍已經開始——長期占據學界主流話語地位的漢學的分化和衰落,今文經學異軍漸起、漢宋調和說也應運而生;堵子學、佛學的復興等等;同時;.由十七世紀天算之學導引而來的西學也正日益受帝國學人的青睞和推崇;。而且中西交流的傳統就是在清政府禁關時間也沒有中斷,而其中漢學者對程朱理學的挑戰和宋學家、今文經學家對漢學的“兄弟鬩墻”尤為劇烈,但這些變化更多應該歸因于學術思,想的內在理路支配而非外來的干涉和沖擊,而且也“并沒有真正動搖傳統的思想世界,除了少數敏感的精英之外,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仿佛依然故我”、“中國思想世界還是處在自我完足的‘天下中”《葛兆光語)。同樣,這個現象的發生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很可能一個人與其同代人在其有限的生命內都很難感覺到這種變化,在知識世界沒有發生大變化之前,在沒有足夠多的思想資源出現的情況下,先前已廣被人們所接受的規范和解釋并不會完全崩潰和失效,普遍的“不確定性”——終極關懷的失落也不會立即出現,而器物層面的變化卻很容易被察覺與感受,這就給了我們一種錯覺,認為近代中國的變革歷程真如梁氏所言。
然而這種內部的改變能否促使中國“走出中世紀”呢?能否替代西力沖擊的作用呢?或者說造成近代中國“權勢轉移”的動力在哪里?柯文的‘中國中心觀”有沒有夸大中國內部因素的作用而縮小西方沖擊的影響從而陷人中國中心的困局呢?其實西力的沖擊本來就是一個由少到多、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作為整體的中國不可能整體上同步都受到西方的沖擊;同樣,,作為整體的西方也不可能同時作用于中國,影響于中國的也只可能是于雙方最先接觸的或最為契合的或最為緊要的。同樣,受西力沖擊的效果也是‘個由中,Jb(指經濟、文化中心)到邊緣逐步遞減的過程,而且還存在抵制與抗拒的現象,晚清時期的反西化言論與“西學中源”說在士大夫中間的盛行(參看全漢升。《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見《嶺南學報》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1936年;又參看全漢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載《嶺南學報》第四卷第二期1935年),也可說明西力沖擊的影響或許并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么強烈,張灝先生根據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的研究,就說“十九世紀末中國的一些重要思想人物,如陳澧、朱次琦、朱一新和王閶運的思想,很少顯示出西方影響的跡象。對于這些人來說,如同1840年之后五十年里的大部分士紳一樣,核心關切的仍然是那些有關儒家學說的傳統問題。”這也正好可以作為柯文“中國中心觀”的注腳。
問題在于,如羅志田先生所說;“用一個典范去囊括一切固然不可取;但因為這一典范被用得太濫就轉而以為它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當。特別是在‘西潮已成‘中國之一部以后,所謂近代中國的內在發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則近代中國士人對許多‘中國內在問題(且不說西潮造成的中國問題)的反應多少也可說是對‘西潮沖擊的某種‘中國回應。無論如何,研究典范的合用與否是可以辯論的,‘西方沖擊——中國反應這一重要歷史現象的存在卻是不容置疑韻,,而且是近代中國歷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題;如果因為某種研究典范的擱置而使人忽略通常為其所涵蓋的重要歷史現象,則無異于西人所說的倒洗澡水而連嬰兒一起棄置。”實際上,將近代中國帶入“近王千年來有之次變局”的是西力的沖擊,而非中國發,展的內在理路的作用廠這也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歷次的中國中世紀王朝的晚期都會存在諸如柯文等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內部的分化與危機,但這些分化、危機等問題并沒有使中國發展出可以否定自己舊日傳統的異己的新思想資源,使中國擺脫出王朝循環的怪圈和老路,走上近代化;而只有在西方大量入侵后,才SI起“一系列文化、思想、經濟、政治以及軍事的大變化”,實現了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權勢轉移”,中國有了對傳統深刻反思和對西方新思想資源的承受,也才使中國有了可能擺脫歷代王朝循環的怪圈,盡管這其中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甚至是唾棄傳統的代價。
其實,晚清士人主張的“自改革”無非是傳統“通經致用”思想的反映和延續、其所依賴的思想資源依然是傳統的東西,其向往也往往是上古三代之治,但努力結果最后一樣是無疾而終,誠如后來尚比較守舊的勞乃宜所說:“今日全球交通,西學東漸,篤守舊聞不足以應當世之務”,時代已經需要新思想資源的出現和應用。·而從知識社會學或者思想史角度來看:“一個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體的傳統沒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這種傳統的習慣思想方式的制約,以至把在其他群體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羿的、錯誤的、模糊不清的,甚至異己的。人們暫時既不懷疑他自己的思想傳統的正確性,也不懷疑在思想總體上的統—牲和一致性。……只有當橫向運動伴隨有強化的縱向運動:亦即在社會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義上的階層之間的迅速變動時,人們對于自己的思維方式的普遍的永恒偽有效性的信念才會動搖。”(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也就是說人必須被他所存在的社會環境、思維方式和思想傳統等思想所依賴的資源,所限定,即使他對此不滿,也逃避和遮擋不了,好的例證之一也許是一個晚清著名經世學者;輿地學家的江寧人汪士鐸(1802-1889),他曾經有濃厚的反孔盂和反宋代理學的思想,并且對西方新知識也有相當的認知—?他曾幫助魏源刊刻過《海國圖志》,且為《海國圖志》寫過跋,很推崇該書和《瀛寰志略》等經世書籍;他甚至還要工人“兼習泰西之法”,進而認為:“不用禮義則中國可謂之夷,用禮義則英吉利、米利堅亦不可謂之夷”(汪士鐸《乙丙日記》)等,這些觀念在當時不可謂不先進,但遺憾的是這些并沒有內化為汪士鐸思考和應對現實的思想資源,一旦面對太平軍之難這樣的危機時,汪士鐸卻是向古代法家學說中尋找救世靈丹,因此,臺灣學者王沉森先生說汪“雖然激昂憤慨,他的思想中雖然醞釀著巨大變化,但他的藥方并不太新,想來想去,仍然不脫舊的思想資源。當儒家不足以應世時,仍然只能訴諸另一個選項,即先秦諸子,換來換去還是那一套。洋務運動并未為他提供多少新的思想資源”、“在整個制度的規劃或政治思想上并沒有什么新的出路”、“在‘思想資源大變之前,人們還是盤旋在老路上”、“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新的思想資源,(中國)顯然也很難有‘自生近代性可言”(王沉森《汪悔翁(士鐸)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這實在是見道之論。在這種沒有足夠多的新思想資源刺激的情況下,僅靠清帝國內部的“自改革”和“反求諸己”的舉動,顯然不能足以顛覆當時舊的主流話語的地位,使中國“走出中世紀”。揆諸以往的歷史事實,我們也可以知道晚清那幫精英所提倡的借用傳統思想資源—尸“藥方只販古時丹”宋進行的“自改,革”——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hetradition)并沒能引導中國實現“自強”、“求富”,反倒是在西方“堅船炮利”和多次對外作戰失敗酌刺激下,發生工“知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crisis),士人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開始處于“失序”(Anomie)狀態——“五經束之高閣,子史懸為厲禁”(宋恕語)、“覺世間惟有此種(指看西書)是真實事業,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住、萬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國明民之道,皆合之莫由”(嚴復語)、“綜觀中外情形,敢斷言曰中國不亡,必無天理”(葉爾愷語),產生了傳統能否有效經世致用的問題,如希爾斯所說:如果傳統給繼承它的人帶來了明顯的和普遍的不幸后果,那么它就不能長久地維持下去了;一個傳統要延續下來的話,就必須“發揮作用”。一個傳統反復帶來災難,或反復被證明明顯不靈,那就行將滅亡了(《論傳統》)。傳統思想資源既然在中西“學戰”中失敗,而內憂外患又紛至沓來,士人面臨“國勢之衰頹”、“中國人辦中國事,反不如洋人辦中國事之忠心,真可嘆也”(汪大燮語)、“惟有多用客卿或可有自存之日”(黃中慧語)這樣尷尬的現象,不得已,“因欲舉一世之法而悉變之”(勞乃宣語),士大夫開始轉步移身向壓迫他們的西方帝國主義身上尋找醫己的良方,變革的取徑也轉向了在傳統之外變(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
隨著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權勢轉移”逐漸完成,近代中國開始被“尊西趨新”的趨勢所主導,“若禁中國譯西書,則生命已絕,將萬世為奴矣”(王國維語),漸漸,西學開始成為支配人們行動的主要憑借,中國士大夫們在不知不覺中被改變了思維方式,開始了對傳統的新定位,結果也就導致時人眼中的傳統地位大大下降,就連“國粹派”的劉師培、鄧實等人也以“國粹”為“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直以中國文化史上與西方現代文化價值相符合的成份為中國的‘國粹”(余英時語),以致出現了“尊西籍若神圣,視西人若帝天”等情況,反過來要清算傳統,要“沖決網羅”——把“傳統送進‘博物館,從‘現代里驅除‘古代”<羅志田語),形成了“反傳統的傳統”(Antitraditional,.tradition),西方長期沖擊的效果終于凸顯,中國根本逐漸喪失,“嗟!嗟!舊學幾將掃地,祖國前途曷堪設想廣知“新”而不再求溫“故”,只有破“舊”才能立“新”,,近代中國社會在付出極大代價后終于開始“走出中世紀?!(朱維錚《走出中世紀》,上海人民出版杜1987;羅志田《權勢轉移》,湖北人民出版杜1999 3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