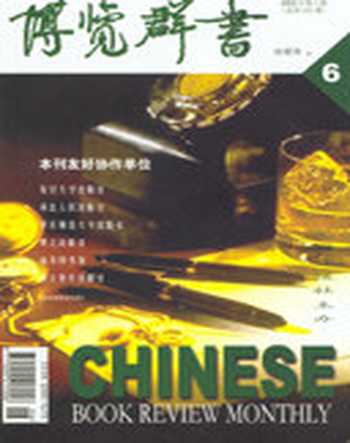《政治和命運》中譯本絮語
任東染
《政治和命運》(Politics and Fate)尸書的作者安德魯,甘布爾(Andrw Gamble)是英回的著名學者,現為謝菲爾德大學(theUniversity of Sheffield)政治學教授和該校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主任。甘布爾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學理論和當代英國政治;他先后撰寫過十余種學術著作,比較有名的有:<當代社會和政治思潮》(!ntroduc·tiontoModem,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t,1981);《自由經濟和強大政府:撒切爾主義的政治學》(The Free Economyand the Strong State:The Politics OfThatcherism,1994);《海耶克:自由的鐵籠》(Hayek:The lron Cage;Of Liberty,1g96)b此外,他還和其他學者一起編輯過十余種學術著作,比如《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Marxism and,Social Science,1999);《撒切爾的法律》(Thatcher%Law,1989);《英國的政黨制度和經濟政策》(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and,Economic Policy,1945”1983:Studiesin Adversary Politics,1990),等等。《政治和命運》一書懸他最新的一本著作,作為《21世紀主題》(Themes for the21st Century)叢書之一在2000年由政治出版社(Polity Press)出版。這本著作實際上是二個有影響的政治學家為非政治學者、但關心政治和人類命運的知識分子讀者所撰寫的普及性著作。出版后大受讀者歡迎,截止到2003年4月7日,僅在亞馬遜網上書店就賣出了612611冊。
政治一向被認為是人類控制其命運的一種活動。但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政治給人類所帶來的巨大災難,以及所謂自由民主制(1iberal democra-‘y)在處理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無能為力和自私自利,使人們開始懷疑政治、甚至鄙視政治,一些解構主義者和后現代信奉者甚至提出要消解和消滅政治,政治終結的論調隨著歷史終結論的出現而甚囂塵上,并且進一步擴展為民族國家的終結、權威的終結和公共領域的終結,一時間,國際學術界形成了被作者稱為終結論(endism)的強大思潮。
,
終結論者對人類能否控制自己的命運充滿了懷疑,對人類的前途也深感悲觀。他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全球化和現代技術發展必然釋放出種種非人力量(impersonalforces),這些力量所創造出來的現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束縛人類進一步發展和創造的鐵籠子。這個社會既是反政治(如abti-Po-litieal),也是非政治的(unpolitical),它沒有希望,也缺少能夠做出其他選擇所需要的手段,因此,它也沒有前途。這種徹底的悲觀主義情緒反映了人們對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的破滅,以及對近代以來占思想界主導地位的以理性和進步觀念為核心的啟蒙主義、甚至是現代性本身的深深失望。
面對這些世紀末的悲觀論調,甘布爾重新舉起啟蒙主義的旗幟,剖析并批駁了各種終結論的理論前提和歷史論據,用邏輯和歷史的方法,闡述了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強調政治的形式可能改變,但政治的本質——作為人類社會命運主宰——卻不會改變。雖然政治和人類命運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張力,但是,人類應該、也有可能控制它所創造出來的種種力量。甘布爾似乎相信,人類的命運并不是由非人力量所決定,而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治所決定。至于這種政治能否實現了人類的目標,則取決于人類能否從過去的成敗榮辱中汲取經驗。
政治作為一門學術,在西方一般都是追溯到古希臘的哲人亞里士多德那里。他在其傳世名著《政治學》中對政治的定義——“人是政治的動物”——至今仍被人們廣為接受,現今林林總總的政治定義不過是亞里士多德定義的擴充和深化而已。這一定義的重要性就在于政治是界定人類和非人類的一個標識。由此可見,政治在人類社會組織和生活中的重要性。
人類的形成和發展幾乎與政治難舍難分。在人類的早期,因為自然環境的殘酷,個體如果不與群體合作便無法生存,于是就有了群體合作,有了氏族社會,有公共空間,有了公共權力以管理公與私的關系,也就有了政治最重要的含義——權力b有了不同的氏族,人類不僅面臨來自自然的挑戰,而且還有來自同類的挑戰。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人類之間就出現了仇殺,于是就有了“我們”和“他們”的身份確定,“我們”可能從氏族發展為部落及部落聯盟,最后成為國家。他們也可能遵循同樣的途徑成為另一個國家,于是政治便有了另一種含義——確定和建構身份。國家只是個人最后的身份,而在國家內部,因出身、血緣、地域、職業和地位不同有著不同的人群,而有限的公共資源不可能得到平等均分,即便是弱肉強食;也還是需要某種秩序,于是,政治便有了第三種含義,秩序的政治。雖然這主種具體的政治概念是甘布爾提出的,但它的歷史解說卻是我這個歷史學者加上去的。談論這三種具體政治時,甘布爾用的是the poiitical(政治衍生物:,政治要素),它們在一起構成了polities‘(政治)。這樣細微的差別有時在中文中很難轉譯出來,只好一股腦地翻譯為“政治”。narratives(敘事,敘述)也是作者常用的一個概念,并且進一步發展為meta-narratives,grandnarrafives,historicalnana-,fives。我只好根據上下文把它們分別譯為元或根本敘事、宏大敘事和歷史敘事。為什么一些后現代作者喜歡用“敘事“這一概念,來代替傳統的“歷史”這一類似的概念呢?我想,關鍵可能在于他們想顛覆歷史這一概念中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而敘事則可以是完全主觀的,因敘事者的不同而異,沒有多少、甚至可能根本沒有什么客觀性和真實可言。
甘布爾把二十世紀后期學界各種大談特談歷史終結、政治終結、意識形態終結的思潮和論調稱之為endism,考慮到這些作者大都是后現代的信奉者,也就是那些最討厭各種“主義”的人,故用“終結論”來譯之。與此相關的、便是postmodernlism和,post-modernity。顯然,把沒有信仰、拋棄歷史、拒絕政治、無所謂未來的這些后現代觀念概括并稱為“后現代主義”是非常不恰當的,因為這些觀念容不得任何信仰和政治,遑論主義。所以只好簡單地用后現代[狀態]和后現代特性來意譯。而postmodernist也就只好稱之為后現代分子或后現代信奉者。
‘Accountability是一個越來越被廣泛使用的政治概念,甘布爾的著述也不例外。中文世界一般把它譯為問責制。其含義大概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掌權者,不論是民選官員,還是任命官員(公務員、官僚;行政人員或文官)都有義務回應公民(選民、公眾)的要求和質問;二是公眾,不論是公民還是社會群體,都有權利通過一定的途徑獲得各種必要的信息。
除了一些常用的政治概念外,作者還自造了一些詞。比如11yperglobalist,它是指那些極度熱衷于全球化的那些人,因此譯為…;全球化熱衷分子”;擴展型國家(ex·tended state)是甘布爾常用的另一 個概念,主要是指由于社會福利等一系列社會責任的擴大而造成的國家權力和政府機構的不斷擴大。另外,在自由派(Uberals)這一概念外,作者還用了libertarians這一表述。它在哲學上是指自由意志論者,但在政治學上,通常是指一味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認為民眾應該對其思想和行動有充分的自由,反對受制于政府的權威,這里只好譯為“極端自由派”。在最近政治學的著述中,從政府(gov-em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轉變已經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甘布爾在本書中對此也有不少的論述。本來,治理的概念來自企業的管理,它在政治學上的廣泛應用可能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即在全球化的時代,社會中的網絡結構發展迅猛,傳統金宇塔式的政府管理已不再適用于新的現實,而且,政府的管理日益受到全球化的沖擊和腐蝕。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和問題需要更多的政府以外的管理:于是,政治學家們便越來越多地用治理這一概念來描述這些既有政府也有非政府的管理。雖然這是一本普及性讀物,但作者喜歡咬文嚼字,典型的句型是一個從句套著一個從句,嚴謹有余,流暢不足,理解和翻譯起來相當麻煩。承擔本書翻譯工作的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四位世界史研究生,我對全部譯文作了逐字逐句的校訂。但由于英語水平和專業知識的限制,譯校者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但肯定還會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錯誤,敬請方家不吝指教。
(《政治和命運》,安德魯·甘布爾著,胡曉進、羅珊珍等譯,任東來校:訌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