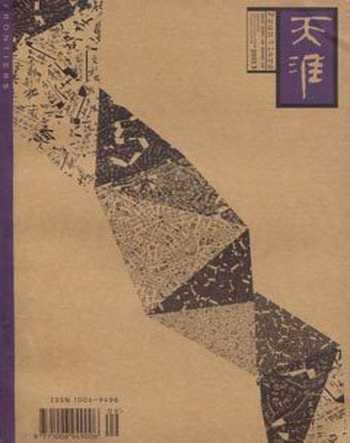音樂反戰:從烏托邦到異托邦
2003-04-29 13:17:04顏峻
天涯
2003年5期
關鍵詞:音樂
顏 峻
藝術家通常不大喜歡社會的既成規則。雖說忙著創作和享受人生,沒有工夫帶頭跟權威作對,可是一旦事情變得熱鬧嚴重,激發起了責任感和激情,那么平時隨心所欲,蔑視主流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習慣,就會爆發出來變成社會行動、政治事件。音樂家反戰,就是這樣的一個傳統。
當然音樂家還要看是什么樣的音樂家,古典音樂家是主流社會的一部分,從政府那里得了好處,再說跳到街上去又會弄臟了燕尾服;流行歌手通常沒心沒肺,以娛樂大眾為己任,怒火太盛、觀點太多,會壞了甜蜜無知的好形象;最后剩下的,就是青少年亞文化里面不安分守己的那部分,搖滾樂、爵士樂什么的。是的,爵士樂也很猛,美國民權運動那時候,黑人薩克斯手Archie Shepp這樣解釋自由爵士的突飛猛進:“這是一場全國性的戰爭。全國都在為消除非正義和卑鄙而戰……炸飛了三個孩子和一所教堂,必然要在某種文化藝術的形式中有所反映……我們當中死的人太多了。”
先是民權運動,然后是反戰。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美國夠熱鬧的。1960年代末,全世界的學生都在街上游行,法國五月風暴,巴基斯坦全國罷工——四個月推翻了軍事獨裁政府……通過激烈的政治表達,年輕人和大范圍的民眾找到了一種自我形象,反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項外化。這個文化的核心,要從反戰的另一面來看——當觀眾往大門樂隊的舞臺上扔的大麻足夠淹沒腳面;當吉米·亨德里克斯為提莫西·利瑞演奏貝司,讓這位哈佛教授一邊傳播LSD和精神旅行法,一邊吟頌詩歌和競選加州州長的聲明;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瘋狂英語·新悅讀(2022年8期)2022-09-20 01:32:1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20年3期)2020-12-16 02:56:12
文苑(2020年6期)2020-06-22 08:41:40
海峽姐妹(2019年6期)2019-06-26 00:52:50
電影(2018年8期)2018-09-21 08:00:00
藝術啟蒙(2018年7期)2018-08-23 09:14:16
兒童繪本(2017年24期)2018-01-07 15:51:37
華人時刊(2017年13期)2017-11-09 05:39:13
西部大開發(2017年8期)2017-06-26 03:16:14
東方藝術·大家(2016年6期)2016-09-05 07:3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