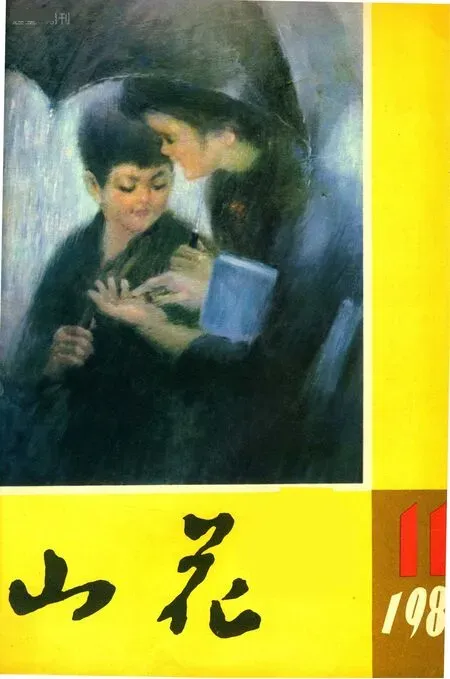他們就這樣度過一生(六首)
馬永波
朋友的妻子
朋友的妻子她對我小心翼翼
她知道我不會到他們家里去
一起喝酒三個人
朋友的妻子
開始關心我的個人問題
這是個幸福的日子
他們一起回到了鄉下
第二天早上我在路邊采了一束倭瓜花
吹著口哨
他們就要走了
那樣朋友會幸福
這一天我分明感到過去也變了許多
這是一個幸福的日子
朋友的妻子
走在后面
晨光中我的黑衣服上
沾滿花粉
草泥馬
你站在雨后的院子里
一部分已經還原
露出黑暗的腹腔
和繡色的稻草
圓圓的眼睛一直望著我們
哥哥又在跑來問我
“用草和泥做一個馬叫什么馬?”
我不回答
不知道媽媽為什么打他
我哭了,望著你的圓眼睛
你同我一起長大
你的名字被人們重復得丟了
老年你在路邊等我
空蕩蕩的嘴里咬著樹葉和謠曲
我們碰碰鼻子,一起去樹陰喝水
再沒有人提起我們
再沒有人被母親痛打
為一首沒有寫出的詩辯護
有些東西你不能去碰它,它會粉碎你
你一生都在逃避你所熱愛的東西
你的沖動扼止在半空,化成了怪物
沒有形式的東西,卻沒有讓
阿佛洛狄忒,腳踩海浪凝成的貝殼
在荷葉、鮮花、清風之中
從存在的幽暗中升起。這首詩寫下了
它自己的生長。一個人只有被大風
平地拔起,才有可能讓視野
超過他周圍的事物,超過玻璃幕墻
增殖和復制的速度,找到最原始的
基因,把它像分裂膨脹的孢子
從發炎的視網膜上拔除。這首詩
寫下了一個人的渺小,當萬物
將他包圍,當遠方在他面前
像玻璃幕墻豎起,越來越高
在外省
有些事說著容易,比如依靠常識活著
他的飽嗝使田野更加空曠了
對于生活,他有一顆流星對天空的歉意
有被畫花臉的戲子那樣的激情
他躺在四面透風的樹下
把遠方鏡子一樣舉到眼前
陽光開始漫過午后的斜坡
他說,老,是一個嚼不動的詞
正如鏡子是一個不發光但很亮的詞
有時,干懶著也是一道風景
偏僻土路上的馬糞還原成了干草
對于這樣一個過于寂靜的省份
歌唱是多余的。他偶爾抬頭
看看莊稼越來越密的田野
感到舌頭底下空蕩蕩的
他繼續躺著說:大雪
是從莊稼茬里涌出來的
跑冰排
報上說昨天江上有特大的冰排
有船塢那么大,灰色的,緩慢的運動
報紙總是說昨天和昨天,就像詩歌
記錄的都是回憶,即使詩中人
用了許多的現在和此刻
比如說我吧。去年這個時候
陪大春在松花江邊蹲著
看冰排,看灰塵撒到水里
(也撒在眼睛里,今年
還沒有隨淚水排出來)
后來他在詩中把冰排寫成一群女囚
鏜著嘩啦啦響的腳鐐
別的我就記不清了。那首詩
好像是兩行一節的,和一塊塊
冰排差不多,只是更為整齊
似乎可以在上面跳躍
提前到下游去。冰排一邊出現
一邊消失,加寬著江面
流了一天,到傍晚江里只剩下水
和岸邊潮濕的黑土。后來
看拍的片子,冰和水都是純藍的
風還在吹著,我坐在屋子里
也能感覺到,它旋轉著一個塑料袋
讓它有靜電一樣糊在行人的后腦勺上
或者在樹梢偽裝成風箏
冰排肯定過去了。到現在
和大春約好的《跑冰排》的同題詩
還沒有完成。說到底
冰排不是為這首詩存在的
甚至不是為去年的我們
他們就這樣度過一生
他們打算就這樣度過一生
他們在一個小城安頓下來
陽光很好,鄰居的犬吠聲很好
夜雨后的星星安寧閃亮
他們要用倒敘把故事講完
偶爾也會有雨季的霉斑
從屋頂一角剝落下來
落在橘紅色的沙發套上
他們就默默地收起來
偶爾有朋友從螞蟻河與萬佛山而來
帶來一陣忙亂和過后的空茫
垂釣時或許有詩句
如細小的影子從水底浮上來,盯著他
他們就這樣過了,這很好
正如山上的石頭
牢牢嵌在自家的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