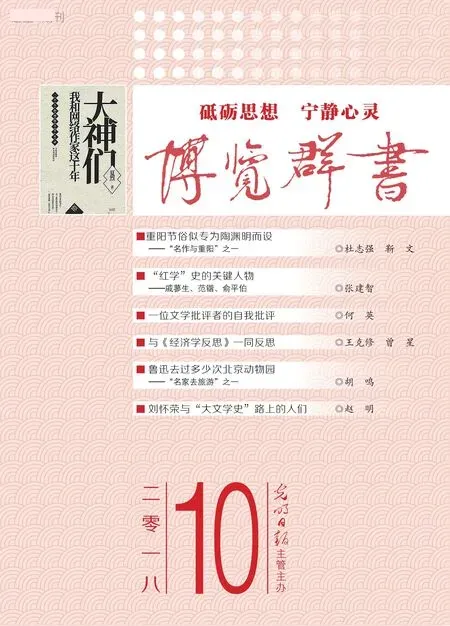“忠實、通順”的豐碩成果
范明生
以尋求智慧為根本目標的希臘哲學在整個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處于初始階段。希臘哲學家的作品具有原創性,而哲學大師柏拉圖,的著作則是希臘哲學庫藏中的瑰寶。繼苗力田師主持翻譯的《亞里士多德全集》出版之后,由清華大學教授王曉朝翻譯的四卷本《柏拉圖全集》于2002~200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西方哲學研究領域的一件盛事,值得慶賀!
我和王曉朝認識已久。他二十余年甘于寂寞,潛心學習,研究希臘哲學,對柏拉圖哲學尤其熱衷。在1982至1984年期間,他作為碩士研究生,拜在我國老一輩希臘哲學史家嚴群先生門下,學習希臘語和希臘哲學。我記得,在由汪子嵩老師主持的答辯會上,他的碩士學位論文《論柏拉圖的辯證法》獲得與會者的一致好評,不久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外國哲學》上刊載。接著在前杭州大學長期任教,,并于1993~1996年期間,遠赴英國利茲大學攻讀并獲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當即由世界著名荷蘭萊登的E.J.Brill學術出版社出版,期間還隨Barbara Spensley博士專門攻讀古希臘語。這些都為其立志全譯柏拉圖著作,以實現其恩師嚴群先生的未完成全譯柏拉圖全集的宿愿,打下了扎實而深厚的基礎。
就本人已經讀過的《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斐德羅篇》、《會飲篇》和《巴門尼德篇》而言,以下幾點印象和理解還是比較深刻的。
第一,《柏拉圖全集》是中國新的文化背景下取得的新成果。古老的、體現出不同原創文化精華韻典籍之所以要不斷地重新詮釋和翻譯,不僅取決于對原文的理解,還取決于譯著處在不斷變化的文化背景之中。正因為這樣,經典著作不僅須常讀常析,而且對不同語種的經典著作的譯解,也將持續不斷地進行下去。就柏拉圖著作的英譯而言,直到1804年才出現T.Taylor的五卷全譯版,接著是Cary和Davis等的Bohn叢書版六卷全譯版,但直到1871年B.Jowett的四卷版時才被普遍接受,至今仍然受到重視。至于著名的洛布古典叢書版的十二卷本,則是由好幾個學者分別譯出的。不同譯者的英譯版至今仍在不斷出版。除了希臘語原版,翻譯時參考較多的美國的漢密爾頓(H.Hamilton)等編輯的普林斯頓版一卷本,就是將現有較好的諸家不同英譯本匯編的一卷本《柏拉圖對話全集,附信札》(1963年初版)。法譯版,較早的是由庫贊(V.Cousin)于1825-1840年編譯的十三卷本;但也是直到羅斑等在二十世紀初至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布德學會版的版本,才獲享權威及榮譽;可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批中青年學者的翻譯本仍在不斷問世。德譯版同樣也不斷出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施萊馬赫譯的1804-1810年柏林版的六卷本,然而,直到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在前人譯本基礎上,新的德譯研究版才出版。其他如意大利文版等也同樣如此,數百年來不斷有新的譯本出來。就英、德、法、意等語言來講,它們與希臘語同屬印歐語系,它們的主流文化又都源于希臘原創文化,期間的翻譯也是需要持續不斷地進行。對于分屬不同語系和異質的不同文化的中國和希臘,“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譯經典實質上是一種不包括語言翻譯在內的文化翻譯,既涉及語言的變化與轉換,也涉及思維方式的變革。”(王曉朝《文化翻譯及其對傳統的影響》,見《世界哲學》2002年增刊)因為,翻譯同時也是不同思維方式的轉換。如果說以希臘為代表的西方以分析見長,中國的特征則是綜合,彼此之間的轉換和翻譯是非常困難的,需要不斷持續地進行。隨著時代的變遷,跨文化領域中的經典,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的著作,尤其有重新翻譯和詮釋的必要。首先,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語本身不斷發生變化;其次;文化環境發生劇烈的變化,變化中的文化背景產生重新翻譯其他民族傳統文化經典的需要。其次,在其他民族強勢文化(如當今的西方文化)的影響下,本民族的傳統存在斷裂的危險,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傳統并促進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須對外來經典和本民族經典,進行新的詮釋。王曉朝一方面認識到,翻譯和詮釋有助于我們把握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規律,它是文化交流與融合工作的關鍵。另一面又認識到,外來強勢文化的滲入,有可能造成華夏傳統文化的斷裂。王曉朝正是抱著這種認識和使命感,在當今新的文化背景下,從事翻譯柏拉圖對話這項艱辛的工作,所謂借它山之石以攻玉。
第二,廣泛吸收國內外研究古希臘哲學的成果。中國學術界對以希臘為代表的原創文化的傳播,早在四百年前就開始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明末西洋傳教士利瑪竇同徐光啟一起合譯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接著是由李之藻和傳教士合譯的介紹亞里士多德物理學思想的《寰有詮》,以及介紹其邏輯思想的《明理探》,但直到民國初年,才由郭斌和、張東蓀等陸續開始翻譯出版柏拉圖的對話篇,以及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等。嚴群則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撰寫和發表了研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倫理思想》等。標志性的成果應該說是陳康先生四十年代發表的研究性譯著《巴曼尼得斯篇》(1944年,已收入汪子嵩師等編的《陳康:論希臘哲學》)。1949年后,在希臘哲學著作翻譯方面是有成績的,如由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的《古希臘羅馬哲學》,吳壽彭譯的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朱光潛先生譯的《柏拉圖文藝對話集》,嚴群先生譯的多篇柏拉圖對話,特別要稱道的是苗力田老師主持翻譯的《亞里士多德全集》。
改革開放以來,與國外交流的渠道大大擴展,希臘哲學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治理哲學史,除了深厚的理論修養、掌握大量原始資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精深地掌握語言文字外,方法問題同樣也是至關重要的。陳康先生在講到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時,強調指出:
每一結論,無論肯定與否定,皆從
論證推來。論證皆循步驟,不做跳躍式
的進行。分析務必求其精詳,以免混淆
和遺漏。無論分析、推論或下結論,皆
以其對象為依歸,各有它的客觀基礎。
不做廣泛空洞的斷語,更避免玄虛到
使人不能琢磨其意義的冥想來“飾智
驚愚”。研究前人思想時,一切皆以此
人著作為依據,不以其與事理或有不
符,加以曲解(不混邏輯與歷史為一
談)。(汪子嵩、王太慶編《陳康:論希臘
哲學》,第III頁)
汪子嵩老師在其主持的四卷本《希臘哲學史》的寫作過程中,比較有意識地、自覺地運用了這種嚴密的方法,在盡可能忠實地顯示出古希臘哲學的原貌上做出了努力。王曉朝本人雖未直接執筆參與具體寫作,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并對此做出了貢獻。他曾多次參與了有關的討論,應邀通讀過第一卷的全部原稿,并特地為它編訂了人,、地、神名譯名對照表。他已發表的學術著作,如《希臘宗教概論》、《基督教與帝國文化:關于希臘羅馬護教論與中國護教論的比較研究》、《神秘與理性的交融》、《教父學研究》,等等,都顯示出這種方法的精神。陳先生的這種方法,實質上體現了西方文化精神的邏輯——分析方法,它最初由巴門尼德和芝諾提出,經由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發展和豐富,到亞里士多德那里集大成,具體地體現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因此,只有掌握和熟悉了這種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詮釋他們的著作。應該說,王曉朝多年來是在這種方法的熏陶、影響、應用、推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其次,翻譯必須忠實于原義的精神。正像陳康先生在他評注的柏拉圖《巴曼尼德斯篇》中強調指出的那樣,翻譯哲學著作的目的是傳達一個本土所未有的思想。但一種文字中習慣的詞句,只能用來表示那些在這種文字中產生了的思想,如果要求翻譯者極力滿足“信”的條件,完全用習慣的詞句來傳達本土從未產生過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不犧牲文辭,必犧牲義理;不犧牲義理,必犧牲文辭。他力主將柏拉圖在《巴曼尼德斯篇》中的Idea或eidos譯為“相”,而反對譯為“理念”;estin譯為“是”而反對譯為“存在”。但要真正理解和貫徹陳先生的觀點談何容易。如在《希臘哲學史》第一卷中,出于“約定俗成”的考慮,依然將idea和eidos譯為“理念”;將巴門尼德殘篇中的estin譯為“存在”。陳先生在美國讀到該卷時,在回信中認為不妥當。到《希臘哲學史》第二卷時,由于意識到“約定俗成”實質上是“約定錯成”,才毅然決然改譯為“相”。但在討論到《巴門尼德篇》時,雖已指出estin是動詞eimi(相當于英語的be)的現在陳述式第三人稱單數(相當于英語的ia),可以譯為“是”、“有”和“存在”;但是為了讀者容易理解仍都譯為“存在”。直到四五十年以后,他的兩個親炙弟子,王太慶和汪子嵩師,才深刻地意識到將estin和on等譯為“存在”是一種必須消除的誤解。他們在合寫的重要長篇論文《關于“存在”和“是”》(《復旦學報》2000年第1期)中強調,只有將on、estin、einai這些詞譯成“是”才比較合乎原義,:能比較好地理解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以及理解整個西方哲學;“是”是西方哲學的核心范疇,所以西方哲學重視分析,重視分辨真和假,從而促進邏輯和科學的發展。關于on和ontology的討論,這幾年來正在學術界熱烈地展開討論,其意義是重大而深遠的,“是”的問題決不是一個譯名問題;而是關系到能否進入到西方哲學精義的問題。(《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詞典》,布寧和余紀元主編,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曉朝不僅積極參加而且還推進了這場關于“是”的大討論。其觀點和成果體現在這部《全集》的翻譯中,顯示出他對包括柏拉圖在內的希臘哲學乃至這個西方哲學最中心的特征的深刻理解。,
第三,實事求是,盡力做到“忠實、通順”。王曉朝清醒地意識到全譯柏拉圖著作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前輩學者們由于種種原因都未能竟全功而留下終身的遺憾。他意識到全譯柏拉圖至少需要以下這些方面的準備:古希臘原創文化及其歷史(尤其是作為哲學前史的神話、宗教知識)方面的素養、關于古希臘語和漢語以及這兩種語言間的歧異的知識以及對整部古希臘哲學史的發展歷程(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on和ontology)的精當的理解,再加上工作過程中的堅忍不拔、心無旁騖的精神狀態。綜觀他近年來的學術成果,‘這些已經基本上具備或者是在工作過程中逐步具備了。他為自己提出的具體標準或目的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忠實、通順”。在翻譯的進行過程中,以希臘語原文為基準,盡可能吸收西方學者和國內已有譯本的積極成果;也就是說;是在主要依據希臘語原文的同時,廣泛吸收的人努力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但它決不是已有的漢語譯本再加上若干補譯的對話的匯編,而是全部重譯并編制的一個全集本。王曉朝認為,之所以這樣做是由于漢語和中國的教育制度在二十世紀中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的中青年讀者如無文言功底,對出自老一輩翻譯家之手的柏拉圖對話已經讀不懂了;加之,已有譯本出自多人之手,專有名詞和重要哲學術語的譯名很不統一,因此需要全部重譯。他坦言,目前仍未能達到拋開辭典和已有的各種西文譯本,僅依據希臘語原文進行翻譯的水準;而是以希臘語原文為基準,版本根據婁卜叢書中的《柏拉圖文集》,翻譯中參考了學術界公認的權威新譯文。而且,鑒于自己的學術興趣主要屬于哲學方面,無法兼顧到文采,惟力求真實的表達文本的原意,所以在翻譯中以“忠實、通順”為原則。這里所講的“忠實”,是針對所翻譯的希臘語原文而言的;所講的“通順”,則主要是面對讀者受眾而對譯者提出來的一個質量標準。、王曉朝說,自《柏拉圖全集》第一卷出版以后,收到了許多信件、電子郵件、電話,贊揚者稱“功德無量”,批評者稱“與某某譯本相比不夠好”等等。譯者希望同行們不要將注意力放在《柏拉圖全集》與其他已有對話譯本的優劣評判上,而是放在對已出版的《柏拉圖全集》的糾錯上。根據通讀第一卷全文和第二卷中《斐德羅篇》、《會飲篇》和《巴門尼德篇》的譯文的體會,并參照公認的權威的英譯文,我們認為,王曉朝的這項工作是進行得嚴肅認真的,基本上已接近他所提出的標準:“忠實、通順”。不但令一般讀者可以據以了解柏拉圖的哲學,就是專業讀者也可以從中獲得啟發。
對西方原典譯文做出全面準確的評價并非易事。例如,大家公認的朱光潛先生的《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是優秀的譯本,長期以來受到廣泛的好評和歡迎。朱光潛先生自謙不懂希臘語并深以為憾,《柏拉圖文藝對話集》主要是依據法譯本轉譯的。我有幸讀到過已故王太慶師的部分柏拉圖對話篇的譯文的手稿,他精通古希臘語和英、德、法、俄等文字。但比較兩位大師所譯的《會飲篇》和《斐德羅篇》,王太慶老師的譯文,柏拉圖的思想是偏于理性主義的,而朱先生的譯文,柏拉圖的思想是偏于非理性主義的。但是,并不能率而斷定太慶師由于精通古希臘語及其哲學,又吸收了舉世公認的施萊爾馬赫的德譯本的長處,譯文就一定優于朱先生。因為實際品評起來問題遠為復雜得多,所以我們建議王曉朝應該歡迎各方面、各層次、各領域人士的批評和建議。
接著我提兩個建議。第一個是根本性的。全譯柏拉圖確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前輩學者們對此夢寐以求,結果都抱憾終身;王曉朝以近五十之齡竟然畢其功于一役,可以說是生平一大快事或幸事。但事情也正像古人所說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但愿王曉朝以此為始點,不斷精益求精,深化對柏拉圖的理解和不斷提高譯文的質量。王曉朝也有此意識,今后他還要與幾位年青學者一起,對柏拉圖的重要對話進行詮釋性的研究。這是一項世代相繼永無終結的工作。西方諸國與古希臘文化血緣相通,他們詮譯和研究柏拉圖有一個時代相繼的龐大隊伍,至今仍孜孜以求;我們可以說剛剛起步,今后還有漫長的路要走。第二個建議是具體而細微的:(1)提要。王曉朝據普林斯頓一卷版譯出H.漢密爾頓列在每篇對話前面的“提要”雖然是很有必要,但漢密爾頓有的提要寫得很草率。例如,漢密爾頓對《巴門尼德篇》這篇極端重要的對話的精義不去認真分析介紹,卻寫下毫無意義的話語:“普通人讀來會感到它毫無意義。整篇論證好像有點意思,但卻無法在讀者心中留下任何痕跡。”(《柏白拉圖全集》第二卷第754頁)這種提要,只會將讀者引入歧途。《國家篇》更是寫得文不對題。所以我們建議,以后有機會和可能的話,重寫全部提要,并且希望比現在版本的略為詳細具體些。(2)索引。作者根據普林斯頓一卷版,譯出全部詳備的索引,這是相當必要的,既有利于一般讀者,也有益于專業讀者。但這里將本來編在一起的索引一分為二(以人、神、地名為準的“名目索引”,以概念范疇為主的“事項索引”),讀者使用起來反而不方便。建議以后仍然“合二為一”。(3)索引排列。索引是按中譯音序排列,建議附上莢漢譯名對照表。一則,,目前譯名遠未統一,二則,不少讀者不熟悉漢語拼音。(4)索引條目。索引中的條目,除了附有英譯名外,最好另附上用拉丁字母拼寫的原希臘語,這對于專業讀者來講是極其重要的。
最后,再提一個期望。希望王曉朝今后能有機會彌補他在譯者導言中留下的遺憾:“有許多地方無法兼顧到文采”。的確在翻譯中,除了考證功夫外,在“義理”、“文章”兩方面都能達到高度統一是極其困難的。就我們所知,在西文方面,水平最高的就數施萊爾馬赫的德譯本。就英譯本而言,B,喬伊特(B.Jowett)的譯文文筆優美流暢;譯文本身幾乎可以作為英文范文來讀;但在澤以“義理”見長的對話時,就顯得不足,因此普林斯頓版一卷本在酌定挑選以義理見長的對話《巴門尼德篇》、《智者篇》、《泰阿泰德篇》時,就采用了P.M.康福德的譯本。當然,今后既要提升古希臘語的修養,又要同時提升漢語的美文方面的修養,的確是雙重的辛勞;但需知,柏拉圖既是西方古今以來偉大的哲學家,又是希臘“散文作家中的最偉大的作家。”(德國浪漫派代表人物F.希勒格爾語)作為一個癡迷柏拉圖對話的讀者,希望能看到“義理”、“文章”和“考證”三者相統一的完美的漢語譯文。這是我們深切寄予的厚望。
(《柏拉圖全集》(四卷),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出版,15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