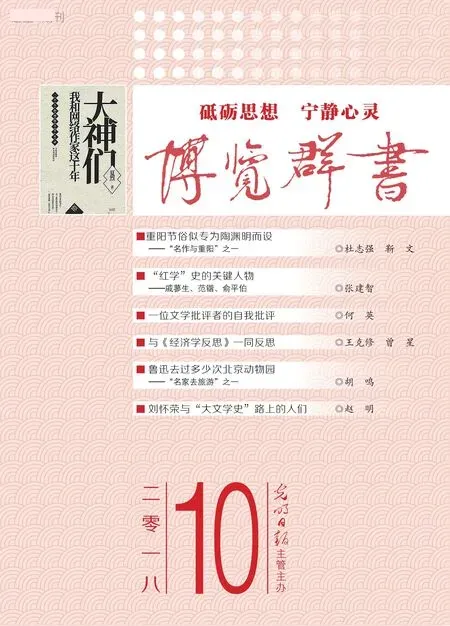關于拙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
楊夭石
我研究中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史三十余年,在努力完成國家科研重大項目的同時,堅持進行有關蔣介石的專題研究,陸續發表相關成果。其中一部分,收入《近代中國史事鉤沉——海外訪史錄》一書,作為《近史探幽系列》之一,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2002年2月,我又將另一部分論文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作為《近史探幽系列》之二,仍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我在序言中特別表示,“本書的是是非非,都靜候讀者的指教。”這話旨在表明,我將本書交給讀者去評論,留給歷史去檢查,各種各樣的意見都在歡迎之列。此書出版后,頗蒙海內外學界關注。然而,今年海外出現的一篇嚴重歪曲拙著的“書評”和其后引起的風波,促使我改變這種一切“歡迎”態度,決定對該“書評”進行駁斥。
先是臺灣《傳記文學》4月號發表段干木先生的“書評”,評論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以下簡稱拙著)。該文題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于不顧——大陸一流學者為蔣介石翻案》,此后,美國《黃花崗雜志》第5期又發表《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署名香港朱有道,而內容則與臺灣《傳記文學》所刊完全相同。由于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斷章取義,強人就己,并且借題發揮,進行政治攻擊,已經超出了“書評”的范圍,并且嚴重歪曲了我的著作,其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對我進行惡意誣陷,我必須據理駁斥,以正視聽。“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茲依歷史事件先后,從幾個方面揭示“書評”的歪曲,同時說明拙著的真相。
一、關于中山艦事件。拙著旨在還原歷史真相,澄清各種謬誤不實之詞,揭露此次事件雖發端于西山會議派的挑撥離間,但蔣介石的所作所為有其必然性。
中山艦事件發生于1926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當年3月18日深夜,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聲稱,“奉蔣校長命令”調艦。共產黨員、時任海軍局代局長的李之龍即派中山艦及寶璧艦應調。但是,當兩艦由廣州開到黃埔軍校后,卻發現并無凋艦之事。20日晨,蔣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五十余人,占領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監視蘇聯顧問。此后,蔣介石在許多場合,即聲稱中山艦的調動,系李之龍“矯令”,目的是將他強行綁架到莫斯科,屬于共產黨和蘇聯方面的陰謀,而1949年以來大陸歷史學家則普遍認為,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個謎團。
拙著根據大量扎實、可靠的資料指出:1、中山艦駛往黃埔并非李之龍“矯令”,它與汪精衛(當時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季山嘉(蘇聯顧問)無關,也與中共無關。多年來,蔣介石和國民黨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傳的所謂“陰謀”說顯然不能成立。2、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因此,所謂蔣介石下令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3、中途加碼,“矯”蔣介石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拙著115-116頁,以下僅注頁碼)。其原因在于國民黨右派想“拆散”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團結局面,挑撥國共關系,“使共產黨和蔣分家”(121頁)。拙著特別著重指出:就蔣介石誤信右派謠言來說,中山艦事件有其偶然性;就當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斗爭和蔣介石的思想來說,又有其必然性(127頁)。“蔣介石和左派力量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必不可免,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遲早也會制造出另一個事件來的。”(129頁)
拙著關于中山艦事件的論述大體如上。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中,卻專門寫了一段“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為拙著為蔣介石“翻案”的有力證據之一。這是嚴肅的科學態度嗎?
二、拙著批判蔣介石“專制、獨裁成性”,批判國民黨由“一黨專政進一步發展為個人獨裁”,而“書評”卻聲稱,拙著肯定蔣介石“是在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
1931年2月,蔣介石與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在制訂約法問題上發生分歧。蔣主張制訂約法,而胡則反對制訂約法。28日,蔣介石悍然將胡漢民軟禁于南京湯山。關于此事,拙著評論說:“蔣介石雖然早年就參加辛亥革命,但始終并無多少民主思想。”(293頁)“他此際之所以重視約法,主要是中原大戰和北平擴大會議的刺激。”“中原大戰是國民黨統治中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它不僅造成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也嚴重威脅著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接過政敵的口號來,力圖以此爭取人心,剝奪反對派的借口,從而穩固自己的統治。”(同上頁)在這一論述的前提下,我曾根據蔣介石日記提出,他有過某些“刷新”政治的念頭。拙著寫道:“盡管蔣介石的目的是‘閼絕亂源,鞏固統治,但是赦免軍事、政治犯,制定約法,自由選舉,自由提案,議案公開,等等,畢竟是在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他在‘江電中重提曾作為國共合作基礎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也頗有耐人尋味之處,無奈蔣介石專制獨裁成性,一遇到反對意見,他就又用起老套路來了。”(294頁)拙著還分析說:“蔣是個獨裁主義者,追求、神往的是大權在握,個人專斷的‘總統集權制,豈能容得別人的批評、牽制和反對呢!”拙著又說:“軟禁胡漢民事件是中國三十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進一步發展為個人獨裁。自此,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僅存的一點民主氣氛掃地以盡。”(299頁)文章結尾,我特別指出,蔣“用粗暴的辦法踐踏了現代民主的原則”。類似的嚴厲批判還有,不能一一列舉。但是,這些,段干木(朱有道)先生都不引,主觀;武斷地聲稱:“楊天石認為蔣介石前述舉措‘是在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也作為拙著為蔣介石翻案的例證之二。斷章取義的做法還有比這更突出的嗎?
三、拙著指出,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仍以妥協、退讓為特征;但“書評”卻將它當作“中共喉舌”的言論,引用拙著來加以批判,利用本人反對本人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有一段妙文,照錄如下:“中共喉舌一向認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以妥協與退讓為特征。但楊天石教授以大量史實證明,暫時的妥協包含了‘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它是—種政策;也是一種謀略。”經過“書評”的這一處理,楊天石就成了反對“中共喉舌”的勇士。事實是否如此呢?
拙著原文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中,中國軍隊未作任何抵抗就丟掉了東北大片江山,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國人最嚴厲的批評和指責。此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有所改變,其表現是:在淞滬地區和長城各口抗擊來犯日軍;在談判桌上,也進行過若干抗爭。但是,就其總體考察,這一時期,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仍以妥協和退讓為特征;”(403頁)兩相比較,“書評”只刪去了上引拙著中最后一句的“仍”字,就將這一觀點定性為“中共喉舌”的語言。那末,敝人到底是“中共喉舌”呢?還是“中共喉舌”的反對者呢?
我在認定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弊焚“仍以妥協和退讓為特征”的基礎上,對此進行進認真、嚴肅的科學考察。抽著指出;蔣之所以如此,一由于他的“興奮中心在剿共”(381頁)。拙著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蔣介石認為內憂重于外患,視中共為頭號敵人。”(397頁)對此,拙著嚴厲批判說:“當時的國民黨和中共之間有巨大的政治分歧旭無論如何,總是‘兄弟閱于墻,在民族敵人面前屬于內部矛盾。蔣介石視中共為‘心腹大患,視日本侵華為‘皮膚小病,將中共看成遠比日本軍國主義者更為危險的敵人,這就顛倒了內外矛盾之間的關系,違背于國人團結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錯誤也就由此產生了。”(397~398頁)
拙著指出,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實行對日妥協和退讓政策的第二個原因在于“蔣介石對日本的軍事實力估計過高。他認為:日本已是現代化國家,日軍武器精良,技術高明,中國在短時期絕對無法彌補這兩大缺點。因此,在他看來,中國軍隊‘有敗無勝,自在意中。他甚至估計,日軍在三天內就可以占領中國沿扛、沿海的要害地區,切斷軍事、交通、金融等各項命脈,從而滅亡中國。”(381~382‘頁)對此,拙著分析說:“中日間的差距是事實,戰爭需要準備也是事實,蔣介石主張進行不斷的、有后續力的持久戰斗也是正確的;但是,蔣介石對日軍實力估計過高,對戰爭中武器、技術的作用也估計過高,相反,對中國的抗戰力量則估計過低。他戰略、戰術呆板,只知道打陣地戰、固守戰,不懂得集中優勢兵力攻敵一點的戰略戰術,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戰爭和敵后戰爭,這是他長期畏戰、避戰的原因。”(384頁)
拙著還指出,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實行對日妥協和退讓政策的第三個原因是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某些影響。拙著說:“蔣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發憤圖強、終午滅亡吳國的故事。”(384頁)拙著還指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的“欲取先予”、“以退為進”、“以柔克剛等思想對蔣介石也有影響(385頁);這些,拙著都有扎實的資料為據,并非虛構。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對蔣介石當年的妥協、退讓進行了批判,拙著說:“應該指出,勾踐的忍辱是在抵抗失敗,國家滅亡之后,而蔣介石的忍辱是在國家尚在,事猶可為的時候。蔣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敵人面前的軟弱一面,其結果是使國家權益一再受到損害。”(386頁)又說:“蔣介石實行這一政策,有其錯誤的、應予批評、譴責的方面。”(403頁)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我才表示:戰爭需要多方面的準備,蔣介石在一段時間內的妥協、退讓,其中“也有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它是一種政笨,也是二種謀略”。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中,我的上述分析和批判都不見了,我的書就完完全全被說成為蔣介石“辨誣”、“翻案”之作了。
四、拙著肯定胡漢民、陳銘樞、李濟深、馮玉祥、張學良等反蔣愛國人士,而“書評”卻一律否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于蔣介石對日妥協退讓,因此激起國民黨黨內部分愛國人士的強烈反對,先后有胡漢民組織“新國民黨”,組成“西南派”,陳銘樞、李濟深等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馮玉祥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等事件。對此,我在抽著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例如,拙著稱:“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日益為國人所不滿,胡漢民由于主張抗戰,逐漸爭得國民黨內部抗戰派的柵護。”(312頁)但是,“書評”卻說:“以上種種陰謀活動表明,胡漢民絕對不是‘相當正派的政治人物。”又說:“胡漢民策動了抗戰前中央與地方連綿不絕的戰事,導致內耗嚴重,于是日寇乘虛入侵。”還說:“張學良是個投機游移分子。”凡此,都和拙著的觀點完全對立。
五、拙著對蔣介石的抗日作了適當肯定,同時,也對其軟弱、動搖作了揭示和批判,但“書評”卻全面捧場,美化其為“民族英雄”。盡管蔣介石長期實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但是,在日寇侵略危機自益加深的情況下,他不得不從事抗日準備;一方面,他仍然堅持“剿共(政策,但同時;又企圖迷惑日本人,以對“紅軍”的追剿掩護其在四川、云南、貴州建立長期抗日基地的行為。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終于決心抗戰,和中共再度合作。抗戰八年中,他一面指揮國民黨部隊對日作戰,但同時又和日-本人多渠道地秘密談判。在拙著中,我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蔣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長知之間的曖昧關系。抽著分析說;“抗戰前期;蔣介石腳踩兩頭船。他一面進行對日作戰,同時又維持談判,準備妥協。當日軍大舉進攻,國民黨軍作戰不利時,這種動搖、妥協的傾向表現得尤其突出。蔣介石之所以最終沒有接受日方誘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有關,也和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國民黨內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關。蔣介石充分懂得,只要他接受日方條件,甚至只要他和日方談判的消息透露,他就會遭到人民和一切愛國力量的強烈反對,從而導致垮臺。”(428頁)拙著還以大量獨家發現的資料探討孔祥熙與日本人之間的秘密關系。拙著指出:“孔祥熙的議和活動應該看作蔣介石全盤對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蔣介石的內心矛盾和兩手策略。蔣介石長期認為中國實力不如日本,與日本作戰,中國必敗。從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蔣介石終于走上了抗戰的道路,但是,蔣介石思想上的恐日癥并未消除,因此,他采取的是一面作戰,一面和談的兩手政策,根據不同形勢,交互為用,以便進可以戰,退可以和,左右逢源。”但是,段干木(朱有道)先生對我的上述分析和論述都視而不見,過度稱譽蔣在八年抗戰中的表現。《傳記文學》的標題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于度外》,《黃花崗雜志》的標題是《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請問,這符合拙著的原意嗎?能從拙著找到“民族英雄”這四個字嗎?值得提醒的是,由于個人精力和篇幅的限制,拙著中沒有一篇研究蔣介石如何指揮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這是應該加以研究的),相反,僅有上述兩篇討論蔣和日本方面秘密談判的文章。這是在“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嗎?
應該指出,抗日戰爭中蔣介石集團和日方的秘密談判,次數頻繁,過程復雜,有多方面的作用。拙著對此已有所敘述,但是,還大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筆者也還在進一步研究中。
六、結語。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斷章取義,自取所需,強人就已,無中生有,嚴重歪曲了拙著的面貌。其各種觀點,均系“書評”作者的觀點,與拙著無關。“書評”還有一部分政治攻擊的內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書評”作者某種情緒的發泄,與拙著更沒有任何關系。拙著是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讀者如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討論以至撰文公開批評,這是有利于學術發展的正常現象。但是,連拙著都沒有瀆,就惡意誣陷,借端煽動,就不能認為是正常的了。
蔣介石已經去世近三十年,早已成了歷史人物。他一身經歷復雜。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中年,和共產黨有過北伐與抗日兩次合作,但又兩次發動反共內戰;晚年,退據臺灣,夢想反攻大陸,但堅持一個中國,堅決反對臺獨。因此,如何按照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研究蔣介石,分析他一生中的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方面,研究其發展、變化以致最終為中共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打倒的歷程,給予全面、準確、辯證的科學評價,當肯定者肯定,當否定者否定,是擺在中國歷史學家面前的重要工作。這個題目做好了,有助于寫好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和中華民國史,更大有助于爭取臺灣回歸、和平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這一問題上,我衷心歡迎海峽兩岸和世界各國的歷史學家共同爭鳴,但是,堅決反對“書評”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惡劣的學風和文風。
(《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楊天石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杜20p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