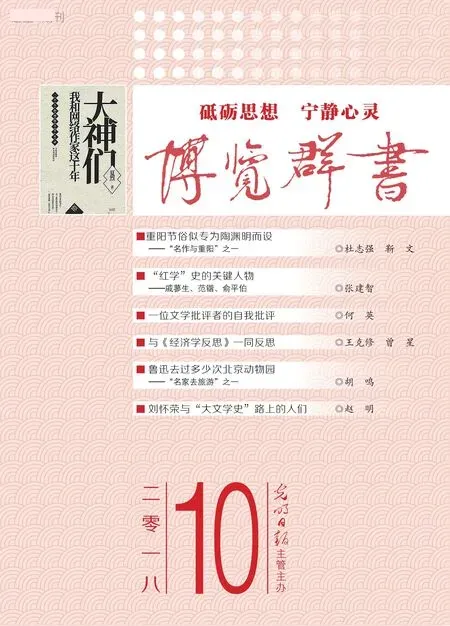歷史語境中的“社會關懷”
趙泉民
近代中國既是一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社會,亦為一種歷史行程被高度擠壓的“非常態”社會。如此,社會經濟變遷過程中,因社會結構或環境失調而萌發的大量社會問題也就成為困擾中國人或近代政府的一個“雜癥”。特別是在民元之后,此種“社會轉型病”又在諸種自然災害與戰事人禍的交相煎逼下,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這其中的一個主要表征就是因上述的幾種原因而從主流社會中逸出的由難民、災民、失業者、鰥寡孤獨殘疾者、不幸婦女及其他貧困者等人員組成的“弱勢群體”隊伍的逐漸膨脹。客觀地說,此種現象在新中國成立后,尤為是在二十世紀結束前的最后二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經歷了大的變革后,已或多或少地有所改觀。但同時隨著城鄉經濟體制的轉軌、市場化程度的深入及農村收入的減少,也由此造成了大量因失業、下崗或能力低弱而難以為生的“新型弱勢群體”(與前所提及的近代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兩者可稱之為“類似現象”)。就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無論是“從現在出發理解過去”,還是“在過去的基礎上理解現在”都是極為必要的。
也正是在上述這種大的宏觀背景下,蔡勤禹博士以一個學人的責任感與使命感而注目于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選擇了民國時期的社會救濟為研究對象,最終完成了一部二十余萬言的富有開拓性的“專題性”論著《國家、社會與弱勢群體——民國時期的社會救濟(1927-1949)》。該著以豐殷的史料為依托,在客觀總結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理論,拓展視野,更新方法,分專章論述了傳統社會的社會救濟思想及措施;現代社會的救濟思想;行政體制演變;立法與設施;國民政府的社會救濟(包括災民、難民、城鎮失業、不幸婦女、安老恤殘與救濟特殊兒童等);民間社會的互助共濟;最后在此基礎之上對民國社會救濟的影響、特點進行了反思,并總結出經驗教訓,以鑒示未來。通覽全書,至少有三大特點令人矚目:
一、思想性分析與實證性研究的有機契合
正如該書的作者所言,弱勢群體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內涵也在變化。簡而言之,就是弱勢群體是隨著社會的存在而存在的。基于此種認識,作者背倚紛繁沉重的歷史事實,條分縷析地解剖了傳統社會和近代社會的弱勢群體的構成;并以之為基礎,在大文化的視野下,通過對社會救濟之文化本質的洞察和感悟,把握其思想內涵的緣起、發展及指向。在不斷挖掘其內外意義的同時,把救濟文化的生命流程與歷史的內省世界融為一體,并對此做出精心的梳理,反饋給讀者一個救濟思想從傳統向現代嬗變的清晰脈絡。書中揭示出:以“天命主義”、“仁”及“功利思想”為理論基礎,以“養”為形式、人們被動承載救濟的傳統社會救濟思想是中國數千年來農業文明的產物;相反,在西方社會思想的沖擊與影響下形成的“以教代養”的近代社會積極救濟理念,是工業文明之結果,體現了國家對民眾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可見,社會救助觀念的變革,也是,個社會經濟及文明進步的表達方式。
與此同時,為避免學理探討過程中出現那種“借用現在既成的理論模式或概念去套用、解釋歷史現象”之傾向,該書作者在考察國家(政府)、社會的救濟措施和實行情況,以及兩者之間互動關系時,并沒有提出所謂的理論框架;也未采用嘩眾取寵的模式,而是從平實質樸的語言、嚴密的邏輯推理和認真細致的考證中,尋求對歷史的“質”的合理解釋。而且眾所周知,研究中華民國時期的歷史,最棘手的莫過于厘清各種制度措置與事實結構、社會績效之間的差異,否則結論與實際的情形很可能會是南轅北轍的。故為避免空發議論和扭曲歷史,作者在以檔案材料為據對歷史事件描述的基礎上,又進行了“量”的分析。據粗略統計,書中繪制的統計圖表達15處之多,除此之外,許多地方還列舉了大量有據可尋的統計數字。“量”與“質”的結合,自然增加了論證的可信度與說服力,最終使人們對歷史現象的認知更加貼近其真實之情形。
二、多向度的立體研究
雖然作者具有歷史學的學術背景,但由于弱勢群體和社會救濟作為一種過去、現在乃至將來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而且涉及到政府、社會的各個方面,決定了研究的多元性,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該書與其說是一部有關民國時期社會救濟的史書,毋寧說是作者以“社會救濟”為切人點并對之進行多向度立體研究而生產出的一個“混血兒”,其折射出的乃是民國時期國家、社會的諸多方面。
就研究對象來看,“弱勢群體”作為近代中國社會存在的一種現象,其內涵覆蓋著社會的不同階層。而且,對其救濟的施行,既有國家出于安撫社會之責任的“政府行為”,也富有民間基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理念的“自發行為”。故此,作者不僅站在近代國家職能“擴展與分化”的層次上,以政治學和社會學交叉的視角,探討了民國時期政府的“制度安排”,包括救濟行政體制及演變、社會救濟立法等項內容,乃至這些措置的成敗得失;而且還從“社會自組織”的角度,將歷史學與社會學融為一爐,揭示了政府之外的民間社會久沿長存的各種救濟設施,如:家族血緣組織的救助,會館、公所與幫口等地緣組織的互助共濟,鄉村草根社會廣泛存在的合會組織;剖析近代慈善團體之救濟的興起,以及都市中的以共濟會、同鄉會、益友社為首的“擬血緣、地緣組織”和消費合作社等“近代型”救濟組織或設施。這些社會力量所具有的救助功能之延續、衍化與興盛,與官方的行政救濟系統形成一種“膠合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實際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國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規定的缺陷”。同時也奠定了民國時期中國的社會救濟迥異于西方社會那種“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甚至二元對立模式”。這就是作者立足于邊緣性和交叉性對救濟設施的多樣性分析后得出的可信論斷。從研究的路徑上看,全書始終貫穿著一條清晰的思路:即橫向上,以救濟興辦的兩個主體千—國家與社會為研究基點,通過共時態的方式,對救濟中政府和社會在“制度”、“實踐”兩個層面的行為進行了全方位透視,并由此引申出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關系。縱向上,則將“弱勢群體”和社會救濟置放于歷史的長河當中,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以歷時態的形式向人們昭示了社會救濟行為從傳統向近代的嬗變歷程。故從廣度上看,既有對社會救濟的溯古及其向近代進化的動態考察,亦有對政府某項具體政策、某一社會團體或民間某一互助組織救濟的案剖析。就深度而論,既有救濟的制度層面之蠡測,也有對救濟思想或基層社會互助習俗的文化窺探,更有對各項救濟在實際執行中所帶來的業績、社會效應和水平的分析。
總之,縱向“板塊”切割與橫向條分縷析的交織,使得全書給人以立體而非平面、豐滿而不臃腫、凝重而不呆板的感覺。
三、歷史性與現實性的統一
學術與國策之間本未有鴻溝。非但經濟、法律研究如此,歷史研究也復如此。因為歷史科學本身就具有:資治通鑒”的社會功能。就此而言,該書以距今最近的民國時期社會救濟為研究對象(作者認為:民國時期社會救濟已具備了現代社會救濟的性質和形態),顯然是“基于現實的觸動”,其終極指向是在對歷史上與今天類似的“現象”的解釋中,為現代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尋求借鑒之道。
作者在考察了民國社會救濟及其內部存在的問題諸如瀆職、貪污、舞弊等事件后,得出的結論認為:社會問題應由國家和社會各自發揮力量,共同解決,這是社會良性發展的上佳選擇。為此,除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健全法律及各項規章制度外,還應鼓勵社會中間組織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應當變革或完善各種社會機制,將社會培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提供資源和機會的源泉。由于近代中國所處的特殊外在環境與內在國情,決定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不同于歐洲的制衡與對抗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合作、互補、互利及相互制約,而且更多的是社會對國家的依賴和受制于國家。因此,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對社會采取何種政策。此種“強國家、弱社會”的社會體制,不僅成為調動各種社會資源、構筑一道全面、合理、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之障礙,而且也因二者之間缺少真正的制度化的溝通渠道,造成國家對民眾反應的遲鈍性,以及民眾對國家要求的凝聚、明確化和表達的困難性。進而使本已屬薄弱的社會保障體系之效用的發揮,也大打折扣。從這一側面上認識,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狀況是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前提,在這個意義上將該著稱之為社會體制(國家、社會關系狀況)與保障體系運作的現代啟示錄,似乎并不過分。正如蔡少卿教授在該書的序中所言:“它不僅拓寬了民國社會史研究的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而且對于當今的社會救濟事業,對構筑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當然,作為一部“拓荒性”的學術論著,本書也存在著有待改進之處。如在界定“弱勢群體”概念時,作者似乎有點失之籠統,認為“貧困性”是弱勢群體的根本特征,而對“貧困性”的內涵則缺少量的規定。從整體上看,“貧困性”是近代中國社會帶有普遍性的二般特征,若按此理解,村落中“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貧農、佃農也應成為弱勢群體的組成,并非只包括作者所列舉的幾種人群。再如,在“森林與樹木”的相互關系上,作者雖已有所顧及和把握,但有關某一社團的具體救助活動的內容則多是淺嘗輒止、語焉未詳。好在作者正以此書為基礎,以民國時期社會影響較著的慈善團體一華洋義賑救災總會為個案,做深入地研究,我們期待著這部作品早日問世。
(《國家、社會與弱勢群體——民國時期的社會救濟(1927~1949)》,蔡勤禹著,天津人民出版社“社會史叢書”之一,2003年1月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