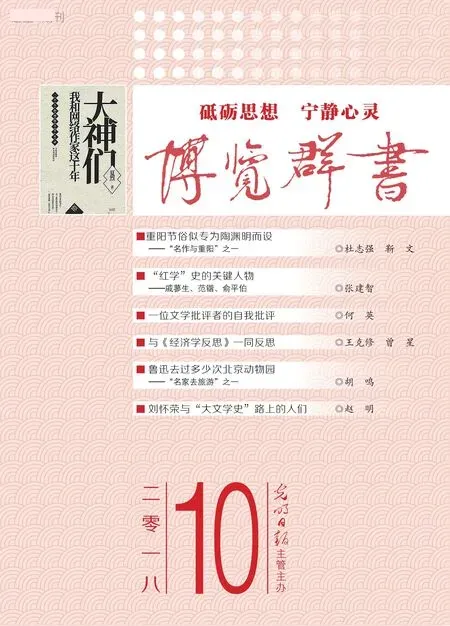傳統禮儀制度對現代的啟示
韓 雷
唐代學者孔穎達在解釋《左傳》時指出:“中國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如果說,在古代漢語中,“中國”更多地屬于一個地域的概念,“華夏”則更傾向于代表一個文化共同體,而維系這個共同體并引導它繁榮、進步的價值基礎,是“禮義”。二千年來,“禮義之邦”(又叫“禮儀之邦”)是中國無數仁人志士、圣君賢相所崇慕和追求的社會理想,同時,也是經由他們長期努力和奮斗而為中國贏得的譽稱。中國禮文化綿延數千年,舉世無匹,它對人類所作出的貢獻,有目共睹。明清以后,禮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桎梏作用日益顯露,與此相伴,反禮教的呼聲也逐漸增高。經過歷史巨變、歲月滄桑,古老的禮文化已漸與現代人遠逝而去。但是,傳統文化的某些精神、氣質、內蘊等等,卻并未在現代社會全然消逝;傳統與現代化在深層次上的種種關聯和糾葛,還有待作進一步的探究、辨析。
楊志剛在《中國禮儀制度研究》中坦言,研究中國禮儀制度,“一是希望廓清歷史的真相,探明那些已經鮮為人知的細節,或在矛盾的歷史陳述中清理出事物的來龍去脈,澄清其意義、價值;二是在此基礎上,深入認識、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發展、演變,把握其特點和特質,進而能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有所助益。”“有所助益”是在對傳統禮儀制度真切理解的基礎上獲得的。前者是后者的升華。關于“真了解”,陳寅恪曾有過親切而精辟的論述,它是“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例如作者在辨析禮之起源時,就是憑著“真了解”去疑存真的。先仔細辨析了風俗說、人情說、祭禮說和禮儀說等說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然后在大體認同楊寬之禮儀說的基礎上,用自己略有補充的文字如是表述:禮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禮儀活動。當然,這也不是最后的說法,比如,原始民族的禮儀又是如何來的呢?當然,任何問題都可以永遠追問下去而沒有盡頭。不過,在我看來,這里牽涉到禮儀活動與民俗的內在聯系及先后淵源關系。往前溯源,即從禮到禮儀活動,再到民俗活動,本鏈條之最后一環畢竟處在較重要的地位。欲求得對禮之深切理解和同情,與先民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從而征顯同一性的民俗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形形色色的禮儀活動在歷代或多或少被統治者利用,用以穩定社會秩序,有關“周禮”制定者的爭論即是一顯例,有學者認為是王莽托人偽作,又有人認為是王莽自己所為。楊志剛回避了這一有爭論的歷史懸案,直奔主題。禮儀活動雖然一般不會產生實際效果,卻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試圖改變和駕馭未被認識的自然力量的精神依托,并且通過禮儀活動,促進了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溝通與合作。這種作用即禮儀內在所涵化的同一性要求。而民俗在先民的實際生活中就起到同一性的作用。禮儀活動是民俗活動的一部分,且起源沒有后者早。劉姥姥兩進大觀園之所以極具喜劇性,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兩種禮俗生活的沖突,其精神上的同一性因社會情境的變化而同大觀園的公子小姐們有所差異。本來么,看者與被看者因地位相異而心態亦不同,作為看者的賈府諸人通過被看者鄉下老太而宣泄平時不能公開釋放的情感,人類與生俱來的頑劣本性在此也得到形象化描摹。
禮與俗的分離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結果,乃至前者漸行漸遠,幾成吾國文化傳統中為人詬詈的對象,而一些淳樸的民俗也無可挽回地被新的民俗或時尚所替代。我們要想在新世紀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又離不開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而只有“真了解”,才能除舊開新和推陳出新。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因此日顯其緊迫性和重要性。從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上講,禮象征了社會的文化規范,俗代表的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國古人對禮俗關系的認識和把握,其實是對于如何調解、處置文化規范與生物本性之間的矛盾,在歷史的過程中作出的選擇。文化是人類生存的精神依托,禮俗所代表的文化在一定層次上調控著人類的精神生活,不能像物質金錢那樣立竿見影。現代一般人對宗教和一切其他的精神力量都看得很淡,而對于具體有形的東西則加以重視,例如錢或權力。有錢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有權更可以直截了當地為所欲為。余英時在《錢穆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深感當代是信仰普遍衰微的時代。此乃時代情境使然。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回憶自己如何走上治史之路后,語重心長地說,“此后治學,似當先于國家民族文化大體有所認識,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尋委,由本達末,于各項學問有入門,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轉向于文化學之研究。”錢穆學術之轉向實“亦自國內之潮流有以啟之也”。我們已可從中窺探到當時研治文化之濃厚氛圍,同“五四”以來的潮流是一致的。根深才能葉茂。欲除舊開新或推陳出新,以對當代文化之建構有所裨益,“舊”的即傳統我們必須“有所認識,有所把捉”,有“真了解”。楊志剛無疑通過他對中國禮儀制度的扎實研究,為我們別開一吸取借鑒傳統文化的新天地;其著作對不止于“真了解”傳統的讀者諸君的啟示想必會更多。
(《中國禮儀制度研究》,楊志剛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