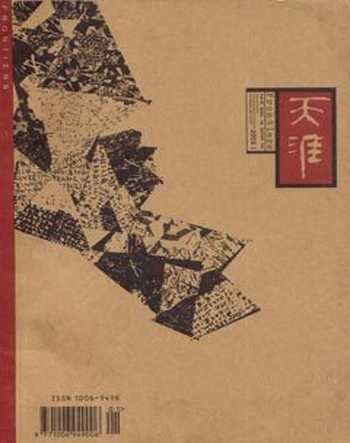文化研究的陷阱
2003-04-29 00:44:03薛毅
天涯
2003年1期
薛 毅
曠新年先生一向嘴辣。他的批判似乎總是無法用一種和緩的、毛毛雨下個不停的方式進行,而總是那樣惡聲惡氣,尖厲刻薄,似乎非要把對象趕盡殺絕不可。我曾對他戲言說,他是被網上的許多人吊起來打的人。至少,很多人一說起曠新年,就會產生一個紅頭發綠眼睛的魔鬼形象。不過,也正如魯迅所說的:“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這種“惡聲”在中國文壇并不多,像曠新年這樣單槍匹馬橫沖直撞地搗亂一下,也不至于引起名人所擔心的“地震”吧。
不過,這回曠新年似乎有點過分了。他閱讀一位大學生所寫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吊帶衫》,而戲仿此文,敷衍了一篇把文化研究“惡毒攻擊”為吊帶衫的文章。這不免讓人誤會他是向這個學生發難。雜文筆法擅長借題發揮,擅長擊鼓罵曹,有時也難免傷及無辜。即便偉大如魯迅的雜文,也頗有“不講道理”之處,以至于到現在還被很多人抓住不放,更何況曠新年輩。曠新年這篇文章可以從兩個角度來閱讀,第一個角度是結合《視界》第七輯的幾篇大學生的論文一起考慮,第二個角度是從文化研究的一種趨向和陷阱來看。我要表達的意思是,從前者來看,曠文問題頗多,從后者來看,曠文的棒喝并非無益。
結合大學生論文來考慮問題,并不是要說明曠新年故意和大學生糾纏不清,而是要考慮當下的文化研究的具體狀況。……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德育(2022年12期)2022-08-22 06:16:18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2022年3期)2022-05-23 13:46:54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金橋(2022年1期)2022-02-12 01:37:04
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21年3期)2021-08-13 08:32:18
遼金歷史與考古(2021年0期)2021-07-29 01:06:54
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54
民用飛機設計與研究(2019年4期)2019-05-21 07:21:2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