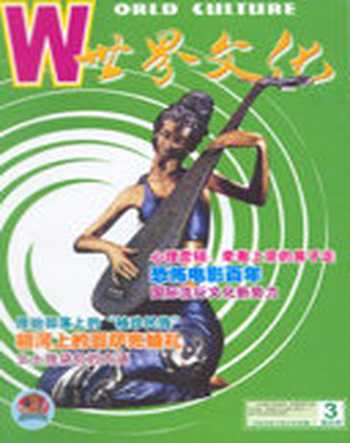夢里的飛翔與不是夢里的飛翔
索拉里
劇情介紹:
早晨,年近40歲的工程師謝爾蓋一邊系鞋帶一邊若有所思,他夢游般地走進廚房,在餐桌上給遠在外地的母親寫信,不過,他寫了半天卻都不滿意,信紙廢了不少,妻子過來關心地問:“你怎么了,在干嘛?”
“玩雜技。”謝爾蓋隨口答道……
像每個80年代的蘇聯人一樣,盡管不知道是為什么,但還總得上班,謝爾蓋一進辦公室就向領導請假稱要去車站接母親,沒等對方回答,這家伙就拿起同事的車鑰匙飛奔而去。
謝爾蓋開著車到馬路上,在一個攤上買了束鮮花,返回車里,卻看到妻子坐在里面,她以為這花是送給她的,但此時,又來了一個女孩,自稱是阿麗莎,任何人都能看出她與謝爾蓋關系暖昧。兩個女人都上了車,謝爾蓋當著她們的面像是在自言自語:“兩個女人都不錯,可是,其中一個,除了盡義務,我和她沒有任何關系;另一個卻是除了義務,別的關系全有,叫我該怎么辦呢?她們我都愛,可我到底該和誰在一起呢?”
他剛說到這兒,阿麗莎揮手給了他一耳光,氣憤地推開車門跑了,妻子則默默卻斬釘截鐵地奪過謝爾蓋手中的家里鑰匙揚長而去。盡管大家不歡而散,但謝爾蓋并不以為然,他回到單位,把花分給同室的女孩們。有人問他怎么沒接來母親?他只好承認自己根本沒去接母親,而是和情人約會去了。主管考勤的上司尼古拉雖然是謝爾蓋的同學卻狠狠地批了他一頓,不留情面,甚至聲稱要他辭職。謝爾蓋立即寫了辭職書,但并沒上交,反倒責問尼古拉和自己過去的女友拉麗絲去哪玩了。
風情萬種的阿麗絲其實依然深愛著謝爾蓋,因此那天得知他被妻子趕出家門,阿麗絲熱情地接待了他……
謝爾蓋終于決定去接母親了。在火車站,他發現幾個人在一個車廂上偷東西,急忙大喊來人,想嚇走這伙人。謝爾蓋看一直沒人來,只好奮勇向前與歹徒搏斗,結果自然是寡不敵眾被打倒在鐵軌上。多虧一位女工將他救起。狼狽的謝爾蓋成了英雄,稍微清醒之后,他顧不上聽掌聲急沖沖地給阿麗莎打電話,故意模仿她叔叔的聲音逗她,阿麗莎看到窗外瑟瑟發抖的謝爾蓋無奈地笑了。
謝爾蓋又在街上遇見了自己的老同學,這位老兄居然是去參加女兒的婚禮,看到這情形,謝爾蓋笑了笑,迅速離開這熱鬧的典禮,跑到大街上一會兒做出滑冰的動作,一會兒又學著飛翔。從車里出來看到孩子們在踢球,也不管人家的討厭對著球就是一腳。街上電影廠在拍片,他也去湊熱鬧,誰轟也轟不走,最后導演出面對他說:“難道非要讓警察來給你教訓嗎?天晚了,去休息吧朋友,明天你和大家一樣還要上班呢,該走了。”總算打發了這個討厭鬼。
某處正在舉辦藝術沙龍,拉麗絲和阿麗莎也在,不用問自然少不了謝爾蓋,大家在一起夸夸其談,從美術到文學,一直談到巴黎的現代藝術巡回展,仿佛這里已經是另一個天下,人們臉上洋溢著自由和自我陶醉。阿麗莎和一個小伙子跳舞,還不時地挑逗謝爾蓋讓他吃醋。謝爾蓋卻滿不在乎,還和那小伙子玩起了游戲,結果每次都是謝爾蓋輸,每次他都要鉆桌子,但仍面不改色,毫無羞愧之意。
天黑了,謝爾蓋饑腸轆轆地來到同學兼上司尼古拉的住處。倆人邊喝邊吃邊聊,尼古拉想開導他,卻又無從下口:“您病了,親愛的謝爾蓋……”不等他說完,謝爾蓋就打斷他:“行了,伙計你還不了解我嗎?”于是二人低吟著60年代他們青年時十分流行的歌曲《憂郁的電車》,唱得很投入,而且他們都對當年首唱者奧庫德日娃記憶猶新。
謝爾蓋的生日到了,阿麗莎和上次見過的年輕人以及他的同事們都來慶賀,大家帶著食品、餐具來到郊外河邊野營。尼古拉還為謝爾蓋的生日祝辭,但話里面有很多批評和領導式的期望。謝爾蓋聳著肩不以為然,大家在縱情起舞,他卻一個人來到河邊,抓起樹枝,蕩著秋千,沒料到樹枝折斷,他掉入河里,費了不少勁,他爬上岸,悄悄躲到樹叢中。大家突然發現謝爾蓋沒了,急忙四處尋找,有人說他掉入水中,拉麗絲急得奔向下游,尼古拉急忙脫衣準備下水,人們在高呼:“謝爾蓋,謝爾蓋……”就在此時,他竟不慌不忙地走出樹叢:“我在這里,你們可真有意思。”拉麗絲看了他一眼,二話沒說,扭頭便走,尼古拉則從牙縫里蹦出“混蛋”兩個字。大家不歡而散。剩下的謝爾蓋一個人,他靜了靜神,突然像上足了發條似的,在空曠的田埂上跑起來,追趕著騎自行車的孩子,最后疲憊不堪地倒在草垛上,頭朝草里鉆進去,大聲哭了起來……
簡評:
如果說《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讓我們看到了前蘇聯人拼搏的一面,那么《夢里的飛翔與不是夢里的飛翔》則讓我們領略了前蘇聯人頹廢的一面,前蘇聯人終未能在與命運進行英勇的抗爭中最終獲勝,前者是幻想,后者成為現實。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忍受痛苦,電影為我們極好地表達了這一主張,因此在電影發行20年之際,又有一群俄國藝術家聚在一起向布拉楊的這部《夢里的飛翔與不是夢里的飛翔》致敬。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電影藝術網上,有關帖子遠遠超過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影片。
每次我看到這部電影結尾,謝爾蓋鉆進草垛大哭的場面,總會想到戈達爾的《精疲力盡》,保羅·貝爾蒙多最后說了句:“真該死”,然后就死了,顯然布拉楊受到啟發,謝爾蓋鉆進草垛大哭表達了人從母體中來最終回歸母體的語意,看看謝爾蓋這一生是多么無足輕重,就像每個“60年代的人”一樣,經歷了那個動蕩、激揚、精彩、概念先行的偉大歲月,他們這一生也就沒什么可以指望的了。喜愛夢里飛翔的謝爾蓋才是蘇聯知識分子命運的真實寫照:優雅、內省、狂熱而迷茫,當一個社會里最先進階層的人出現了這一癥候時,整個社會也就發生變化了,不管她曾經多么輝煌,曾經讓多少人恐懼。但這還不是最令人沮喪的,當你意識到,在實際上謝爾蓋還是前蘇聯人當中被他人視為活得很不錯的少數時,你就會越發悲觀了。至少,他有不少情人,至少女同事們都愛他,甚至他還有自己的住房和可以隨時搞到小汽車的地方。問題只是在于這些表面上看去很有質量和誘惑力的小資情調已經不再屬于一個人了,它們服務的對象即將崩潰,而且是轟轟烈烈地崩潰。
因此,表達這樣一種“世紀末”含義的影片自然也處理得無比低調了。深秋暗淡的落日,陰冷潮濕的黎明,隱在霧中的街道、房屋,謝爾蓋局促的呼吸,狹窄的房間和沉悶的辦公室,總之一切低調美學的表征在電影中隨處可見。布拉楊也許是出于同情,他好在還讓謝爾蓋和尼古拉齊唱《憂郁的電車》時眼中多少閃動了一些光芒,不再是死魚般的呆板,但這絲毫的活力也僅屬于60年代,他們如今早已被建制化了,《夢里的飛翔與不是夢里的飛翔》用整個音畫為我們展現了曾經生于理想和神話中,而今成了“多余人”的那一代是如何輕易而無助地失去這美好時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