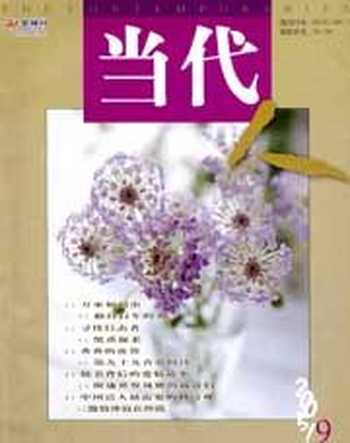頓悟在飛瀑懸寺
奚學瑤
張志春是個博學多才的學者型文人。
他自謂人生有三次選擇:棄仕途行政,返文學藝術;再由文藝入史哲,轉入王韜與易學研究。文人難入仕,情性使然;由文藝創作至學術研究,則緣于文化根基深固,師友熏陶所致。文藝的至高境界是真善美,故為文者需是性情中人。作為性情翻版的散文,常常能夠真實地反映作者的性靈與文學功力。有鑒于此,散文被稱作作家的通行證。同樣,散文又是重要的文化載體,承載著作者的文化素養,因此散文亦是學者的一種文化標識。作家需要學者化,學者亦同樣需要作家化,張志春二者兼通,在河北文壇可謂一種奇數。
張志春的散文數量不算多,其中亦羼雜一些近似宣傳廣告類文字。然而,當他一旦傾心投入時,便情溢書卷,悟透紙背,立意高遠,雋永繾綣。其中,《不死的靈魂》、《頓悟懸空寺》、《我,黃果樹瀑布》、《寄生蟹》、《童心蟹》①、《從“子不語怪力亂神”談起》、《堯舜的后代》②等文章堪稱上乘佳作,純正文字。文章是情性、素養、心境交匯之結晶,天時、地利、人和之最佳碰撞的火花,故為文者倘能于世留下數篇好文章,便足以告慰人生。張志春散文作品雖然不多,但有此數篇,即可以標識他的散文品位了。
《不死的靈魂》,是生命之作。“十年浩劫,心上人飲恨而亡”,思念化作精凝的文字,借她的“靈魂”訴說,寄托自己的悠悠情思。詩(絲)情將淚珠串作項練,縈繞在心頭,碧海青天,夙夜夢寐,青春戀情,少年心懷,如此纏綿多情,怎不讓有情讀者熱淚涕零?作者的真純情性,由此而吐露心曲。如此濃情血淚,是生命的傾心投入,豈是一般文字所可比擬?
《頓悟懸空寺》是張志春的代表作品,曾入多種選本,常為人所稱道。倘《不死的靈魂》是青春情懷,則此篇是中年肺腑,反映了他對人生與社會的成熟思考。作者有感于懸空寺的險峻奇絕,探尋古人“憤世俗之紛爭,厭人間之混濁”而遁入懸空險寺的心路歷程。作者凝注懸空寺中儒、道、佛三教始祖同塑一室的現象,明晰了這樣一個道理:儒、道、佛三家起初的“相互排斥、對立,到后來就逐漸相輔相成,互相補充融匯,統一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之中了”。作者不僅在思想上有所感悟,還進而從藝術上感悟懸空寺的“虛實結合、空靈雅致”的魅力,闡釋了中華傳統文化之中的虛靜空靈的意境之美。如此文思,使一般的觀景攬勝之文,升華為人生感悟與學術思考,將美感與理念融匯在一起。沒有文學修養,難以雕琢這等玲瓏寶塔;僅有文學修養而無學術積淀,便只有優美文字而無形而上的深邃思考。所謂“學者散文”、“文化散文”之說,此篇可作一個范例。
《我,黃果樹瀑布》,是一篇精巧的別具匠心的佳構。作者以第一人稱敘述,并將黃果樹瀑布賦予人格化,以自然流暢的自我道白,介紹了黃果樹瀑布的自然面貌與來龍去脈,中間又融匯了美麗而悲愴的神話故事,最后畫龍點睛般道出了對社會與人生的感悟:
為什么當我風平浪靜、在平坦的河道里緩緩流淌的時候,卻無人重視,無人欣賞;而當我生命的途中出現懸崖峭壁、坎坷不平、大起大落,生活逼得我不得不鋌而走險,寧可粉身碎骨、肝腦涂地,也要勇往直前的時候,卻招來如此眾多的仰慕和贊賞呢?
猶如白水河蜿蜒流淌,在黃果樹一頭扎下數十丈懸崖,濺起漫天飛雪。文章到此戛然而止,寧靜與激越,柔美與悲壯融為了一體,迸發出了壯麗的景象。容易寫成八股的游記,在張志春的筆下煥發了燦爛與清靈。如此將山水人格化、描繪藝術化的游記文章,殊為罕見,倘無高超的藝術修養和潛心構思,豈能鑄造如此佳構,讓人為之嘆絕!?
《堯舜的時代》,可以視為散文,亦可視為紀實小說;易言之,這是一篇具有小說特征的人物散文。文章有小說特有的跌宕情節與矛盾沖突,亦有小說常有的峰回路轉般的敘述,真實地展示了農村基層干部黎洛嵐的思想性格變化與命運變遷,一個忠實執行極左路線的專制霸道的基層干部,經歷了坎坷遭際之后,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老當益壯,成為領導全村人民奮發圖強、努力奔小康的帶頭人,重新贏得了村民的尊敬,在村民的“悲涼高亢”的哭聲中,畫上了人生輝煌的句號。文章以樸素的語言,真實的細節,自然的情感,須眉畢現地描繪了一個血肉飽滿、性氣剛強的農村基層干部形象。
此篇文章不同于傳統的人物散文。傳統人物散文往往是懷人之作,是作者對某個人物的回憶與思念。此文,作者本人時隱時現,有時寫了我與黎洛嵐的瓜葛,有時則通過旁人的敘述,介紹了他的人生際遇,從而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情節鏈條。傳統的懷人之作,往往淡化情節淡化矛盾,著重自我的憶念,而此篇則情節曲折,矛盾復雜,以客觀敘述,表達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因此,可以說,此文是以小說筆法來撰寫人物散文,在創作方法上突破了傳統的格局,有創意,有發展。其人物性格面貌,猶如浮雕般凸現,讓人銘記難忘。
《從“子不語怪力亂神”談起》則是一篇隨筆式的論文,因而可以將之歸入散文之列。中庸方正、溫柔敦厚是儒家的文藝審美觀,“子不語怪力亂神”是儒家的清規戒律,對文藝的發展起著束縛的作用。作者以“離經叛道”之精神,列舉中國自古至今大量文藝例證,指出中國文學史早就在實踐上否定了這個禁令,“怪力亂神”是文學發展的必然。新時期的言情、武打、通俗文學、影視作品等正是以“怪力亂神”之面貌,向“正統文學”發起全面進攻,從而出現了“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文學新局面。作者高屋建瓴,視通今古,從根本上觸及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中的保守思想,以犀利的言語和雄辯的論據,沖決著傳統觀念的羅網,在解放思想中起到發人深省的作用。論文的主題鮮明,隨筆式的表達方式,是其文章的特色,氣勢磅礴,情感強烈,較之那些坐而論道的論文,不可同日而語。如此書寫論文,值得提倡,只是倘無相當的散文功底,是難以寫出如此立論嚴謹而又汪洋恣肆、淋漓酣暢的好文章。
以上數篇文章,大致可以代表其行文特色。這些文章表明,他的學養與文學質素,頗有大家之風。只是,他在散文領域的成就與聲名,未能昭彰顯赫并傳而廣之。個中原因,竊以為有二:
其一,是其涉獵領域甚廣,文史哲幾乎無所不涉,僅文學而言,亦不止散文、小說,注釋翻譯均有成就。面鋪得寬了,便不易集中攻堅。“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創作與治學的運籌,似可借用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其二,成長環境、個性、時代的局限,意緒未能放浪,自我頗受壓抑,深沉謹重有余,瀟灑飄逸不足。傳統文化中儒家的溫柔敦厚、溫良恭儉,隨家園氛圍與學業積淀而俠骨入髓,其文學性靈塑造于文化專制年代,不能不受“左”風“左”雨的摧殘。雖然,他喜逢思想解放的時代新潮,使他的文化心理與思想開始解凍,旗幟鮮明地倡導“怪力亂神”,但理性的解放往往可以啟悟年輕人,而很難在感性上重塑已經成形的自我。往往在而立之后,人的思想行為易成定勢,容易在傳統的背影里規行矩步,很難使其心旌迎風飄動,作霓裳羽衣之舞,與春風春雨中滋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爭逐風流!張志春的散文個性與血性,在傳統文化心理與學術思維的包圍中,未能充分張揚,因而情性得不到充分的流露,氣韻也便少了些鮮活。
張志春是文人,是學者,是學者型的文人。他的才學、識見足以使他寫出更多上佳文章。學識是枝干,才情為花葉,兩者兼而有之者,是文壇喬木。廉頗未老,愿張志春在耳順之年,老而彌堅,不墜青云之志,以倡揚“怪力亂神”之勇氣,身體力行,寫出更多的奇文力作!
注:①以上五篇見張志春散文集《神州風采》,1990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
②以上兩篇見張志春散文集《三棲集》,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