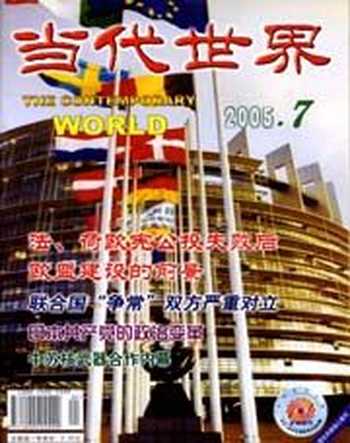歐盟的一次“政治地震”
吳興唐
法國全民公投結果,對《歐盟憲法條約》說“不”。荷蘭繼之。受此影響,本來對“一體化”半心半意的英國,乘機宣布擱置公投。這無疑是歐羅巴大陸的一次“政治地震”。這次“地震”是歐盟內外,政治、經濟、社會錯綜復雜矛盾的總暴露。
“政治一體化”觸礁《歐盟憲法條約》的提出,原本想在多極化、全球化的大勢下為歐盟“政治一體化”邁開重要的一步,體制上確定相對穩定的常任主席和外長,加強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一體化,加強歐盟成員國的防務合作,使“歐洲發出統一的政治聲音”。殊不知,這就觸動了“主權讓度”和“民族認同”問題,事情就變得復雜起來了。在全球化沖擊下,歐洲民眾有一種不穩定感。
經濟問題成堆 法國公眾多數對《歐盟憲法條約》說“不”,實質上并非完全是對歐盟憲法的否定,而是借機表達對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不滿和對未來前景的擔憂。
引發“模式之爭”同樣是市場經濟,歐洲與美國“模式”不完全相同。美國實行的是完全自由市場經濟(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歐洲是社會市場經濟(萊茵模式)。法國民眾擔心,歐盟在“一體化”過程中,打著“改革”的旗號,不斷擴大自由市場經濟,削減社會福利,降低企業稅,將加深“社會分化”。法國的否決,表明法國民眾不接受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擴大太快,消化不良2004年,歐盟從15國擴大到25國,把一些東歐國家納入其中。土耳其、烏克蘭等國入盟也在討論之中。這就造成歐盟成員國之間經濟水平和經濟發展的不協調。荷蘭公眾否決歐盟憲法,其中一條重要原因是,荷蘭付出多、回報少。
反思“精英政治”由于歐盟的發展和取得成就,歐盟及其成員國領導人以及主流政黨的領導人對通過《歐盟憲法條約》信心十足。但他們卻對歐洲國家普通百姓在想什么、訴求什么都不甚了了。于是出現了“民主赤字”問題。老百姓是現實的,他們最關心的是養老金、失業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有趣的是:巴黎的富人區多數投了贊成票,而法國北部的工礦城市和馬賽的窮人區則恰好相反。還有一點值得警惕的是:在歐洲一些國家主流政黨傾心于“精英政治”的時候,極右政黨和組織卻在乘虛而入,拉攏弱勢群體而增加這些極右勢力的政治資本。
“美國因素”在現代重大國際關系中,“美國因素”無所不在,歐盟一體化進程中也不例外。美國表面上說支持一個強大的歐洲,心里卻不然。“新歐洲”、“老歐洲”之說完全暴露了美國分化歐洲的意圖。美國對主張多邊主義的歐洲大國尤其不滿。《歐盟憲法條約》在法國、荷蘭相繼被否決,美國也難免有點幸災樂禍之心。
歐盟的這次“政治地震”給歐盟的發展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但是,歐盟從1951年的歐洲六國煤鋼聯營發展到現在的25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而且,歐盟一體化進程畢竟符合時代潮流。在經過憂慮、反思和辯論之后,歐盟經濟和政治一體化會更加穩步和健康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