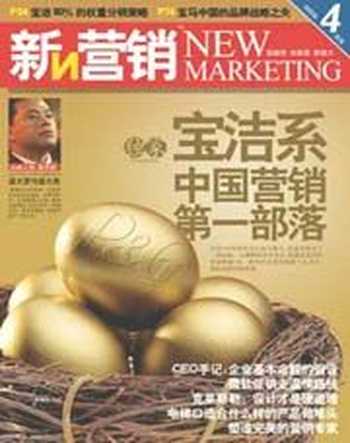吳建:和經銷商一起復制成功
方半山
寶潔常常為經銷商做培訓,指導他們如何做品類管理,讓產品擺放為整個品類的效率最大化做貢獻,而不單單指向寶潔的產品。所以說,寶潔其實是和經銷商攜起手來復制成功模式。
一開始,吳建不太愿意接受采訪,因為有寶潔中國公司Joanna Wang“黃埔二期”和崔廣福、孔雷等“黃埔三期”的“前輩”在,吳建覺得晚輩理當少說話,但是“寶潔系”的號召力使他最終沒有拒絕。事實上,盡管走出寶潔數年,前寶潔人的交往圈子仍然有很強的寶潔概念,就像吳建所說的:“大家從寶潔出來,以寶潔為驕傲,有一種集體榮譽感,對寶潔依然很認同。”
現擔任箭牌口香糖高級大區銷售經理的吳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寶潔做銷售,1999年離開寶潔加盟另一個小公司時也主管銷售。與他同時出現在記者面前的,卻是一位財務分析和計劃經理,吳偉翔,他們在寶潔時就是同事,現在到箭牌口香糖仍然是同事。吳建灑脫,吳偉翔斯文。
在寶潔就像坐在火車上
在中國語境里,“大河有水小河滿”是從正面說明組織與個人相互依托的關系,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則是從反面對這種相互關系進行詮釋,如果用“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形容,則是指事情已經到了非常不妙的地步,對組織和個人而言都是悲情時刻。
然而,寶潔這種百年老店式的組織由于其無比深厚的積淀,以上幾種說法,放到寶潔身上,便不太適當。1999年,在中國土地上已經走過10年的寶潔遭到當頭棒喝,銷售額從1998年的80億元猛然下滑到39億多元。在外人看來,當時的寶潔人,無論是市場部還是銷售部,或者是市場研究部,因為業績下滑肯定會沮喪,甚至有被炒魷魚的危機感。但是,寶潔明顯沒給予員工“企業興亡,人人有責”的訴求,這究竟是一種自信,還是一種值得商榷的疏忽?
吳建多少有些謹慎地把當年的“下滑”情景說成是“變換”,說當時他們能感覺到公司業績的“變換”肯定對個人有影響,但不知道那種“變換”對自己的將來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現在回想起來,感覺理解自然要深一些。”這種理解是,當時應該是感覺上了泰坦尼克號,只能像船上的乘客隨波逐流。
吳建同時比較了自己的三段職業經歷:“我曾經認為頭5年在寶潔,就像你坐在火車上,一直坐在同一節車廂里。這節車廂就是廣州寶潔,車里的人走來走去在流動,但車開的多快你完全沒有感覺,因為你與它相對靜止。車開往哪里,向左還是向右,什么時候停車,你根本不知道,也根本不受你控制。等從寶潔出來,進入了一家小公司,我的感覺就像是騎上了一輛三輪車,什么都得自己來,所有的家當都在車上,完全都是你自己控制。從小公司出來,再進入一家大公司,你有了在寶潔坐火車、又有自己騎車的經歷,你再控制一輛中型車,很多事情你就有或多或少的經驗,該往哪走,該怎么走,遇到交通繁忙的路口和路段要怎么辦,就會知道該怎么做。”
離開寶潔與業績相關,但未必明智
也許是業績的壓力最終導致了寶潔營銷系統的改組。1999年,原銷售部被CBD(客戶生意發展部)代替,全面負責客戶生意的發展和服務工作;接著四個銷售大區(華南、華北、華東和西部)的建制被打破,改為以渠道類別劃分組織結構,有分銷商渠道、批發渠道、主要零售渠道和大型連鎖渠道、沃爾瑪渠道。不久,批發渠道并入分銷渠道。據吳建回憶,當時他們把分銷商的很大一塊生意拉過來了,比如有一些大型零售的生意,他們自己直接供貨。300多個經銷商后來壓縮到207個。
這種大手筆的改組,寶潔的意圖是讓渠道員工集中精力研究專管渠道的運作,成為“顧問型行銷專家”。但是,在員工心里,他們未免失落。吳建說:“大的原因是公司發生了大的變化,股票下滑,業績下滑,每個人的工作也有了調整,你的前景不明朗,職責也在不斷減少。”
實際上,分銷在改組之前承擔了寶潔中國公司80%的生意,改組后也有50%。但渠道管理大家都做得很熟了,作為豪氣沖天的年輕人,每個人都會想要嘗試一些新的東西,結果被限定在一個極其狹窄的行銷范疇,郁悶在所難免。吳建直言不諱地說:“開始的時候感覺有些沮喪,批發和分銷商管理放在一起,而寶潔供貨是統一定價,因此分銷商拿到的產品不會有太大的價差。”這就影響了寶潔內部負責分銷業務人員的積極性。隨行的吳偉翔則說:“回想起來,當時離開寶潔的人,是很短視的,看不到寶潔作為一個強大的全球性公司的力量。”
在吳建看來,寶潔前期注重橫向增長,發展經銷商,增加銷量;后期主要側重縱向發展,即便砍掉了一些分銷商,大部分的地級區域寶潔也覆蓋到了,只是把人為的覆蓋轉變為自然的覆蓋。特別是這一兩年,寶潔一些主要的品牌調整了價格之后,對網絡的覆蓋能力就更強了。
寶潔的執行效率
盡管吳建不太認可一些前寶潔人形容的“寶潔有如初戀”的說法。但他告訴記者,5年的寶潔工作經歷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寶潔做事情的高效率,這一點不是體現在繁瑣的表格要填寫,而是寶潔提倡的領導層對項目的跟進。寶潔有一套方法和培訓幫助員工養成高效的行為模式,比如說備忘的填寫,比如說領導對員工每天工作的跟進,等等。“很多事情都是寶潔先動手做的,因為做的時間長,經驗就多一些,因此執行力強。”
吳建和吳偉翔對網上傳言“更改海飛絲的標簽需要55個簽名”表示不屑。吳建干脆說,他不太覺得寶潔官僚。在他看來,寶潔有兩點挺好,一是從上到下不會走彎路,因為每個人貢獻的價值不一樣。二是寶潔的復制能力,方法在一個地點成功了,馬上就會為寶潔所復制。所謂55個簽名只是因為寶潔有過很多教訓,這個數字并不說明寶潔一定反應慢。做財務的吳偉翔補充說,也許在別的企業兩個簽名需要兩個月,而寶潔就算55個簽名花的時間也很短。
事實上,無論是市場戰略還是銷售戰略部門,在吳建看來,效率都非常高,比如在降價、包裝等方面,處理的時間都非常短。而在產品更新、升級數量上,寶潔的對手都沒辦法與寶潔抗衡,一個是因為這些競爭對手的研發能力弱,另一個是它們的計劃很容易被否決,效率不高。吳建舉例說,2000年B2C很熱門的時候,寶潔內部就有人“眼紅”B2C被神化了的前景,遞交了建議書上去,很快就被否決了。吳建說:“寶潔之所以沒有盲目跟進,因為媒體深度分銷不是我們的強項,而是我們競爭對手的強項,我們的強項在分銷、渠道。”
寶潔倚重可結戰略同盟的經銷商
寶潔在營銷方面對經銷商的提攜和幫助,歷來為人稱道。吳建說:“復制成功模式不僅靠我們自己,也靠全國各地的經銷商。很多公司是經銷商一虧錢,公司就緊張。但是寶潔不會,我們只會做對整個行業、整個公司利益有益的事情。生存權是分銷商自己的,寶潔只是一個助力。”
寶潔的幫助其實一點都不神秘。譬如在寶潔叫“助銷”的,在其他公司可能是叫賣場陳列,就是一個產品出來之后,貨架上放什么位置,做怎么樣的促銷,如何使賣場陳列生動化,等等。
寶潔的與戰略客戶共贏策略才是真正重要的。譬如,寶潔常常為經銷商培訓,指導他們如何做品類管理,讓產品品牌的擺放為整個品類的效率最大化做貢獻,而不單單指向寶潔的產品。事實上寶潔常致力于對經銷商的整體培訓,把寶潔從財務到人力所有的管理知識都教授給他們。吳建感嘆道:“這是一種長遠的做法,寶潔經銷商的隊伍因此很穩定。”
盡管經銷商做寶潔的產品利潤率低,但利潤率低不等于投資回報率低。在降低經銷商成本方面寶潔還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對經銷商而言,整個投資回報率的增長就是投資的降低和利潤的增長。寶潔最早引用對終端客戶的管理,運用80/20理論,尋找戰略客戶。譬如在管理應收賬問題上,寶潔有個很極端的例子。比如一個分銷商一年的生意規模為3億元,可能它每天的庫存率只有十幾萬元,但是寶潔不會讓他斷貨,因此他一年3億元的生意,如果按3個點的毛利算,利潤也有上千萬元,而成本才幾百萬元。這樣算下來,投資回報率就非常驚人了。
當然,經銷商要賺錢,同樣也要承擔責任,譬如所有的業務代表都是跟經銷商簽合同,但是他們的附帶服務費、利潤、獎金都是由寶潔來制定并監管。在每個財政年度寶潔都會與經銷商簽這樣的合同,對經銷商的業務人員有很具體的規定,在比貨、陳列等細節方面規定得很清楚。同時,寶潔對經銷商也有合同,要求他們保障業務員的利益,比如獎金、養老保險等等。也許在開始的頭兩年雙方的磨合會很辛苦,但慢慢就好了,重要的是寶潔可以借此牢牢掌控產供之間的主動權。